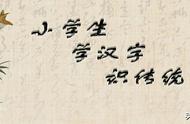张大庆
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人类是否能够征服疾病?人类从有这样一个设想到现在,哪一些疾病被征服了?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对于疾病都会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于某些个体的疾病,像是感冒、肺炎、糖尿病、痛风等,可能还会有相关经验。关于“什么是疾病”有过很多讨论,美国的科学哲学家Boorse等在一本名为《什么是疾病》(What is Disease?)的书中,讨论了40多年来人们有关疾病概念的争论,迄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结论。
当从单个的疾病认识上升到一般性的认识,其意义就不再只是描述个体病痛的经验,而延展到医疗服务标准的确立,医疗保健政策的制定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等等。所以疾病概念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而是相当具体的。讨论疾病是什么也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入手,比如从哲学的、文化的、人类学的观点来讨论。今天我们主要是从医学史的观点来讨论疾病是什么。从历史上看,我们对具体的病症有很多深刻的认识,但是变成一种抽象的概念,不仅有很多争论,也有很多版本。
讨论疾病局免不了涉及健康问题,健康和疾病常常是相互定义的。比如说什么是健康,健康就是没有疾病;什么是疾病,疾病就是人体的正常功能受到了损害,就是不健康。然而这样一种互为对立面的定义并不能使人满意,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前给出过一个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指身体、心理和社会的良好适应状态。”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这个定义提出批评,认为它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缺乏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价值。
对于疾病的定义,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具有历史性。而且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甚至是亚文化中,对于疾病的理解可能也不一致,所以其中又蕴含了文化的特性。我们后面也会再结合具体的一些案例进行分析。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人类能够征服疾病吗?”可分成三个问题来讨论,一是疾病是什么?二是历史上人类是怎么认识疾病的?三是哪一些疾病得到了人类有效的控制,甚至是根除,还有什么疾病依然是人类的严峻挑战?疾病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复杂的研究领域,人类遭遇过各种各样的疾病,要想把它讲清楚是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只是从历史的视角来向大家展示一个概貌。
疾病是什么
在中国古代,对于疾病认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比如说甲骨文里面就可以看到类似的文字,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试图描述出来,

甲骨文“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的字形,表示疾病的意思,是一个人中了箭的样子。 被称为是“疾”,一般认为描述的是一种外伤。后来人们对这个字又有一些引申,认为中箭是一个比较迅速的过程,所以又引出了一个“快”的意思。这个病出现以后,较轻、很快就消失了,于是称之为“疾”。

甲骨文“病”。
而比较重的就称为“病”字,《说文解字》解释是“病,疾加也”。字表述的是一个人躺在床上,还在出汗,可能是在发热。大家知道,疾病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就是发热。很多常见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比如说像我们很熟悉的SARS,新冠疾病等,早期的很多传染病,像天花、麻疹、伤寒、鼠疫等等都有发热的症状,所以说发热是早期人们对于疾病认识的最重要的一个症状。这样看来,如果一个人在发热、在出汗,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病。

甲骨文“龋”。
甲骨文里面还有对个别具体病症的记载,比如说像这个 “龋”字,认为大家可以看这个上面有一个小虫,有了蛀牙。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于个别的疾病和一般性的疾病概念都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古代埃及,也有对于疾病的认识,这是康氏纸草文书,古代埃及的一本医学的纸草文书,后来有古文字学家进行破译,可以看到在上面也有一些具体的疾病的描述,比如这里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墓葬的一个拐弯的形状,表示的大概是一个损伤的意思。这一组图形描述的是呼吸急促的意思。第三种图形的话,描述的是骨折或者是错位的意思。在古代的埃及的纸草文书里面,有很多疾病的记载,也都是描述的一些具体的疾病,就是告诉我们当时人们认识到了这样一类人类所遭受的外伤或者是疾病的折磨,怎么去处置?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埃及,或是在巴比伦的泥板上面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展示了。
历史上人类是怎么认识疾病的
人们对于疾病的记载,也是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一般可呈现出几种不同的认识的方式,其中一种我们称为本体论的疾病观,本体论就是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在发生作用,或者对于人的疾病产生影响。人之所以生病是有某种东西在作祟。比如说是恶魔,或者是祖先的灵魂,或者是上帝的愤怒等等。总的来讲是一种神奇的、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一种外在的力量,对人产生的一种作用。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人做了不好的事,或者是触怒了上苍,或得罪了祖先,那么人们怎么去对待这种情况?比如说有的是用祈祷的方法、或者是驱魔的方式,不同的文化传统,无论是中国还是埃及,还是古巴比伦等,都有类似的传统。
当然在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在有一些不发达的或者是还存在着的土著部落里面,人们依然还会有这样一种魔鬼致病的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疾病是一种外来的神秘力量,或者是恶魔而导致的,总之是一个外来物引起的。所以应对方法就是放走它。古埃及有一个神,叫做霍鲁斯(Horus),他的眼睛有驱魔作用(the eye of Horus),所以古埃及人祭祀他。后来把霍鲁斯之眼被抽象成为一个符号“Rx”成为处方上的一个代码。
我们看到古代埃及的医神,希腊的医神,都发挥着祛病消灾的作用,人们有了疾病,都去神庙里祈祷,希望通过神力来对抗恶魔,驱走恶魔。这是上古时期人们对于疾病的一种认识。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都修建有这样的神庙,比如古希腊修建的阿斯克雷比亚神庙。神庙一般都修建在空气清新、风景优美,还有温泉的地方,这样也有助于那些来此祈祷者的康复,有些人还可以在神庙过夜,晚上有祭司给他们祈祷,也给他们一些药物治疗。
古希腊的神灵大多数是人格化的神,所以说神也会娶妻生子,所生的孩子也具有治疗的神力,比如阿斯克雷比亚的太太Epione能够抚慰人们心灵的痛苦,他的一个女儿Hygeia是保障人们健康卫生的神灵,另一个女儿Panacea是掌管药物的神灵,“万灵药”就来自于她的名字。
前面我们讲了古代怎么去认识疾病,就是把疾病看作是一种外来的神秘物质,通过祈祷、祭祀、驱魔的方式把它赶走,人就可以恢复健康。在此之后,人们又产生出另外一种疾病观,我们称为生理学的疾病观。这种观点认为,人之所以生病,并不是某种外来的神力影响,而是人们身体内部的功能发生了紊乱。
那么人体身体的功能是怎么保持正常的呢?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医学认为有三种主要的物质的力量在主宰着人体的身体功能,一种叫做Pitta具有火的性质,另一种叫Vata,就是气。还有一种是粘液性的叫做Kapha。这三者形成了适当的比例混合,是人体的基本构成。三者保持平衡,人们的身体就是健康的,三者失衡就会导致疾病。这是印度的所谓“三原质”学说,也称为“三大”,是解释人们疾病和健康的基础理论。
古希腊医学则有“四体液”学说,也称为体液病理学说,四种体液为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体液被认为人体的基本物质组成,不同的比例混合,分布在人体体内,就可以保持身体正常功能的运行。如果说某一种体液过多,某一种体液缺乏或某一种体液变质、腐败,这样就会引起相应的疾病。
第三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的“五行学说”,在此就不赘言了。大家可以比较看看,印度是三原质,古希腊是四体液,中国是五行,无论是三、或是四、还是五,重点不在于哪种解释更全面、更精准,而是在于它们都是为医生提供了一个解释模型,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助于医生解释某人会生疾病,是因为体内某种物质的平衡发生了变化,由此利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当然这种解释模型非常宽泛,可以针对不同的病人,给出不同的说明。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主张四体液病理学说,他认为体液的变化,可导致人体内的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他强调疾病并不是一种外来的神力,他还专门批驳了所谓的“圣病”,即由神力所引起的疾病,他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身体所出现的所有的症状都是对于疾病的一种回应、一种反应,而医生最重要的功能就帮助身体来恢复它的自然治愈力(natural healing power)。
希波克拉底提出来的这个医学原则是非常睿智的。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医生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帮助病人恢复自然治愈力。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的功能是帮助,而不是主导。比如说这一次人类面对的新冠肺炎,或者新冠疾病,大家最期盼的是什么呢?最期盼的是疫苗的出现。疫苗是什么?疫苗实际上就是医生研制出来的一种帮助病人恢复“自然治愈力”的物质,将疫苗注射到人体里面,就是帮助人体产生更多的对抗这种病毒的抗体。如果没有疫苗的帮助,人体的自然治愈力激发不出来。如果注射疫苗以后,免疫力(自然治愈力)依然很弱,那还是不会起作用。所以说,希波克拉底提出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医学思想,就是注重身体自身的治愈力量。
在中国古代,类似的医学观念也是非常受到重视的。中医也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虽然,可能大家认为正气、邪气的概念很抽象,但实际上讲的问题依然还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体的免疫力。当然希波克拉底当时不知道免疫力问题,中国古代医生也不知道,中国古代讲的是正气,而希波克拉底讲到就是自然治愈力,两者异曲同工。
我们现在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往往都认为是某个药物、某种方法起的作用,往往忽视了自身的治疗可能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医生的作用实际上是帮助病人,恢复病人自身的自然治愈力。希波克拉底等诸多古代医生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即大多数的疾病是能够自然治愈的,甚至不会到医生这里来自己就康复了。有很多疾病是有自愈性的,都是个体的自然自愈力的深刻体现。
希波克拉底还提出一个所谓的不伤害原则,就是在医生没有办法治疗的时候,也不要给病人带来伤害。治疗过程中造成伤害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为了某些不恰当的目的,错误的来使用或者过量的使用药物而造成病人的伤害,这都是不应该的。
希波克拉底第三个很重要的医学思想就是,注重疾病的转归,他把疾病的进程分成几个阶段,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就是期7天。7天、14天的观念,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即古代医生观察到大多数疾病从未成熟期到成熟期的时间过程差不多有7天的时间,这个过程便称为“消化”,是采用的一种比喻的方式,促使从未成熟到成熟的动力就是身体内的能量(physis),消化后可以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化,一种就是经过一个危机期(crisis),疾病好转或恶化,另一种可能会,变成一种慢性的状态(lysis)。
这种认识对于当时医生来判断疾病的转归是非常重要的。在希伯克拉底时代,医生真正能够很好治愈的疾病是非常有限的,希波克拉底提出这种理论具有时代特征。我们这个时代,判断医生好不好,即医生能不能很准确地认识某种疾病,注重的是诊断(diagnosis)。而在希波克拉底时代,认为医生好不好,不是看他的诊断能力,而是看他的判断预后(prognosis)的能力。医生一看这个病人是可治还是不可治,如果不可治,他就会告诉这个病人,你这个病我没有办法,这是分辨医生好坏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希波克拉底对于疾病的认识、观察成为了西方医学近2000年来基本遵循的一个原则。虽然后面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基本的准则还为医生们所遵循,真正的变化差不多要到19世纪以后才会有一个明显的转向,所以一般追踪西方的医学思想,都追溯到希波克拉底那里,认为希波克拉底是医学之父。
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学说,对于当时很多疾病的解释是有价值的。比如说粘液,主要是大脑来控制,它的特性是冷和湿,占支配地位是冬季,人们可以根据经验来解释,为什么冬季人们容易患感冒,而感冒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流鼻涕,流鼻涕不停地流,希波克拉底解释说这是因为大脑里面分泌出来的这种粘液。有了这样一个解释,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治疗。
希波克拉底的思想,后来由罗马时期的医生盖伦所完善,提出了一种体质病理学说。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学说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患某种疾病,而体质病理学说所解释的是,为什么某人更容易得某种的疾病。前者是讨论一般性的问题,后者讨论了特殊性的问题,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对于很多的疾病做出一般性的解释,为医生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病人听到后也觉得有道理。所以说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学说和盖伦后来发展的体质病理学说,在西方的医学史上占据了2000多年的统治地位。
直到现在,体质病理学有时候还会被提及,比如在描述个人特性时,说某人具有某种特质,是情感丰富,还是多愁善感,是性情急躁,还是忧郁寡欢。这样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和解释很多病人的一般情况。当然疾病是复杂多样的,除了考虑人体自身的特质之外,也会观察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季节、气候等产生的影响。
希波克拉底专门写过关于水、气候、地域和疾病关系的著作。在中国古代医学,也非常重视自然原因导致的疾病,比如说有“六淫致病”学说,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等自然因素过盛,可导致疾病。伤寒学说,指的就是外感风寒引起的热病。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伤寒的论述,伤寒指的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病。另外,有些疾病不仅只是影响到个别人,而是很多人染病,这就是所谓“疫病”。疫病在甲骨文里面也可以找到。《说文解字》里有“疫”这个字,解释是“民皆疾也”。同样,在西方也认识到流行病会引起大量的人患病,甚至是死亡。
瘟疫往往有三种特性——发病很急,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这些不仅影响人群健康,也对社会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比如说雅典的瘟疫导致了古希腊文明的衰落,还有安东尼瘟疫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塌,中世纪的黑死病,也是导致了欧洲社会经济的极大衰落。
对于疫病不同文明都有记载。比如对天花的记载在中国最早,记载最早并不表示这种疾病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最早,而是认识早。葛洪对天花的记载,说是来自俘虏,故称“虏疮”,是东汉时期与交趾国交战,由俘虏传入中原的。目前所知天花早期的情况,可从古埃及的木乃伊身上找到证据,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以看到他的面部有天花留下的瘢痕。
当然除了中国的医生观察之外,西方的医生也会有观察。如意大利医生弗拉卡斯特罗,就对于传染病有了一个很细致、比较全面的观察,而且他还做了分类,一类是直接接触传染;第二类是间接接触传染,即通过衣服、被褥等传染,第三类是远距离的。在这个时期,欧洲有麻风、梅毒等传染病的流行,医生们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对于这类疾病逐渐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于传染病的原因也各种说法,早期认为是来自瘴气,由于污水积聚腐败而产生的恶臭性气体,所引起的疾病,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解释,也是来自经验观察。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瘴气致病的观点。弗拉卡斯特罗认为,瘴气的观点并不准确,疾病的传染可能是一种微小的物质性的东西,是一种肉眼还看不见的或者是感官觉察不到的东西在起作用。弗拉卡斯特罗的推测,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如显微镜的发明,染色技术的发明等,直到巴斯德、科赫之后,才证明了这类肉眼看不见的物质是引起疾病传染的原因。
中国的医生也对瘴气理论有所反思。在吴有性的《瘟疫论》里,他认为瘟疫是一种戾气,是一种特殊的东西,而“非风,非寒,非暑,非湿”的原因。这也就是说明清时期,江南一带传染病的增多,使得一些医生也开始探究瘟疫的病因,不再满意发热性的瘟疫都是外感风寒,也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物质,一种“杂气”所致。除吴有性之外,叶桂、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通过临床诊疗,都意识到温病具有不同于伤寒的特性。人们对于传染观点有了新的认识。
18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兴起,即对因病去世者的尸体解剖,发现患者生前表现出来的病症,与身体内某个器官的病变可关联在一起,于是就是提出了器官病理学说。后来研究身体内部的病变又进一步从器官细化到组织、细胞。
于是,疾病就不是希波克拉底讲的体液平衡紊乱了,而是身体里的某个部位发生了病变,比如肝脏出现了脓肿,肾脏出现了肿瘤,心脏瓣膜有缺陷,肺有空洞等等,就是这种器官本身出了病变,不是体液平衡的紊乱,体液病理学说受到质疑和挑战。本体论的疾病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
除了器官病理学说之外,另一种本体论的疾病观是细菌致病学说,即现在的病原微生物理论。病原微生物学主要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由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特·科赫等建立起来。他们观察到了很多的疾病,可能是来自于外的、肉眼所看不见的某一种微小生物所致。巴斯德证明了细菌和感染、传染病之间的关系。科赫发明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显微摄影方法,改进了培养基使得细菌的培养、菌落的增长更容易观察等。科赫还提出了判断某种细菌是否是某种致病微生物的规则,即科赫氏法则,现在基本上还在使用。
由于巴斯德和科赫等人的贡献,很多致病微生物陆续被发现。导致人类疾病的许多曾经不知道的原因陆续被找到了,如鼠疫、霍乱、伤寒、破伤风、炭疽等一系列的疾病,现在我们听起来都比较陌生了,而在当时都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引起大量死亡的疾病,病原微生物学的建立,使得这些疾病能够被我们所认识,并逐步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你。
在病原微生物学发展的同时,病理学深入到细胞层面,德国医学家魏尔啸认为细胞的病变是疾病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人们陆续了解到疾病和基因的变化有关,比如有些基因的缺失,有些基因的突变,因此我们这里可以看这张列表,人们开始关注基因疾病的问题。通过一系列研究,现在认识到有很多的疾病都与基因相关,所以现在开展疾病基因组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发现有很多基因的变化可能引起不同的疾病,因此可以采取修饰基因的方法来诊疗疾病。
以上简略回顾了一下人类对于疾病认识的两类观点,一种是本体论的观点,一种是生理学的观点。本体论的观点认为疾病是某种物质性的存在,或者某种物质作用于身体的变化。这种疾病变化,在身体上、在器官上、在组织里,在细胞中,或者在基因上都能够找到证据。另外一类是疾病的生理学解释,即身体平衡的紊乱而导致的疾病,比如三原质、四体液、五行的失衡,也可以认为是人体内分泌、神经免疫功能的紊乱等,都是属于所谓的生理性疾病观。这两种解释不是对抗的,而是互补的。可能某一种解释适合于某一类疾病,另外一类解释适合于另外一类疾病。
第三部分我们讨论一下人类是否能够战胜疾病。人们已经发现很多疾病是具有自限性和自愈性的。前面讲到希波克拉底医学,强调人体的自然自愈力,很多疾病都可以自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是可以战胜疾病的。例如,普通感冒,大多数是可以自愈的,你可以不吃任何的药,通过休息自然调整,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自愈。当然人们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加快或者促进我们治愈率的提升,或者是加快疾病的康复进程。
我们可以通过通过摄生法,通过调整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来恢复健康。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非常重视摄生法,论述过急性病和慢性病的摄生法。中世纪欧洲的第一所医学院——萨勒诺医学院,编辑出版了一本关于摄生法的口诀,教导如何管理自己的身体,要求学生去背诵。
其次就是照护,照护是人类医疗史上最重要的活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照护比治疗更重要,因为治疗方法是有限的。现在人类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人们日益认识到,对于很多老年人照护实际上比治疗更重要。
再就是对症处理,这也是一种非常基本的方法,比如说这次新冠疫情,大部分的治疗都是对症治疗,如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都可以用对症治疗。从这个角度来讲疗效问题,很多对症治疗都是有效的,治疗一种疾病,包括祛除病因、改善症状、恢复功能等多个方面,并非仅仅是消灭病毒。尤其是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针对病毒有效疫苗或者是特效药物时,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同样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多患者也康复了,这就是临床疗效。所以说对症疗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当然,若要得到满意的治疗,首先需要准确的诊断。西方早期的体液病理学说,主张通过尿液来诊断,因为体液中最容易获得的就是尿液,当时对尿有非常多的研究,当时医生的招牌就是在诊所门口挂个尿瓶,医生能够辨识尿的各种成分、颜色、气味等,由此来诊断疾病。根据体液病理学说,体液变质,如血液增多或变质,医生可以通过放血的方法来治疗。
第二可以用隔离检疫的方法来预防疾病,我想大家已很清楚,就不赘述了。
第三就是化学疗法。公元8世纪以后,阿拉伯医生对炼金术的兴趣推动了化学的发展。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倡导用化学物质,特别是矿物质来治疗疾病。在欧洲16世纪到18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物药,金、银、铜、铁、锑等都曾入药。当然这些药物的安全性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后来不再用了。直到20世纪以后,德国医学家多马克在偶氮染料里面发现了百浪多息,后来制成磺胺药,开启了化学疗法。
第四是抗生素。更为有效的治疗病原微生物疾病的是抗生素的应用,抗生素对于传染病的控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五是疫苗。我想大家对疫苗的重要性应该有大致的了解。最有代表性的疫苗就是牛痘疫苗,最早是来自人痘疫苗。人痘接种的最早记载是在中国,18世纪传到了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被公使夫人蒙塔古认识到它的价值以后,推荐给了英国的王室,王室要求皇家学会对人痘接种的有效性进行了实验,实验获得了成功,后来人痘接种在英国王室得到推广。华盛顿的军队也实施过人痘接种。18世纪末期,詹纳发现牛痘苗更为安全,所以开始推行牛痘接种。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牛痘接种在全球推广以后,成为根除天花的有效措施。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通过牛痘接种彻底根除了天花,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而根除的疾病。
在此之后,人们希望仿效天花的根除,通过不断开发疫苗来逐渐根除疾病。这张表上展示一系列的疫苗。现在最可能根除的疾病是脊髓灰质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广泛接种,能有效的控制脊髓灰质炎的流行。我们国家推行脊髓灰质炎糖丸的普遍服用,脊髓灰质炎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
虽然主要的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遗憾的是,又有新的传染病出现,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发传染病的危害更加突出,如艾滋病,埃博拉,SARS等。新发传染病可能与现代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行为方式的变化,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都是新发传染病的重要影响因素。
以往人们低估了疾病在人类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这次新冠疫情,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疾病问题。正如麦克尼尔所言,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疾病并不是配角,而是历史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我想大家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毫无疑问人类在与疾病的较量当中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的,但是新的疾病又会不断的出现,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警醒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与疾病之间的这种较量将是长期的,疾病也会与人类长期的相伴相随,我们甚至不得不接受将与疾病长期共存现实。
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许多传染病的流行,所以说依靠科学,依靠人类的聪明才智,依靠人类的团结友爱,我们还是能够从容的面对各种疾病的挑战,来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平。

张大庆
(本文为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张大庆2020年10月23日在博雅大学堂所做讲座的整理稿。)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