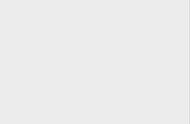20世纪60年代后期,城乡文化一片荒芜,农村更是看不上什么书,晚上又多停电,在那种情况下,一些看过古书的老学究就有了用武之地,人们秋冬季节闲时就央求这些知书人“说书”。所谓“说书”就是把书的内容通过说书人的嘴讲给人们听。
我们街上那时有三四个能说书的人,一个是我本族的爷爷,一个是叫作二掌柜的单身老汉,高度近视,我们都叫他二爷子,一个纯粹是盲人,我叫他增福伯伯。本族爷爷说的是《七侠五义》,他看过的书多,所以能一本一本地说下去,《七侠五义》是武侠小说,当时农村很流行武林故事,而且还有不少年轻人习武练功,武林群雄们飞檐走壁,来去自如,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故事,着实深深地吸引了少年时期的我们,人们每晚准时到一个小卖铺中去听。
小卖铺的主人叫马林如,开了我村唯一 一家卖杂货的小卖铺。马林如老人丧偶,有一个儿子叫马全贵,也没有家小,父子两人相依为命,人们闲来无事,便到铺子里闲坐,农闲时节,就成了说书、听书的最佳场所。每到说书时间,一间不太宽敞的屋子里便挤满了人,大人们坐在炕上,吸着烟,半大的孩子们则站在地下,尽管油灯昏暗,烟味呛人,但大家都静静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直到说书人说出“要知后事如何,咱们明晚再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小卖部回家。
后来,有人主张给说书人买几支烟抽,大家便凑点钱给说书人买了烟,好能每晚听听下回书都有些什么精彩故事。
《七侠五义》中最精彩的片段是大破铜网阵,铜网阵机关重重,暗器密布,白玉堂因骄傲独闯铜网阵,结果惨死阵中,叫人痛惜。人们都说“说书唱戏劝人心”,确实不假,白玉堂身死铜网阵的故事便给人们提了个醒,人再有本事,也不可骄傲自满。所以,听书除了享受故事,还让人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二掌柜说的是《粉妆楼》,后来才知道《粉妆楼》是罗贯中的作品,讲的是罗成后代罗灿弟兄和奸臣沈谦斗争的故事,具体情节已无详尽记忆,但罗灿、沈谦、九头狮子马耀等名字现在还记得。
二掌柜说书速度较慢,还有一句口语“咥咧咳”,虽无实际意义,但穿插在书中,就像调味品,大大丰富了书的意味,人们有时说话,也有“咥咧咳”不时从嘴里蹦出,可见人们对二掌柜说的书还是非常认可的。可惜老人家无儿无女,老年就住在生产队羊圈旁的一间土房中,离去的时候,没有多少人照看,母亲曾给他送过几回吃的,还拆洗过一次被褥和洗过几次衣服,这虽是读书以外之事,但它是一页活书,给我的教育影响很深刻,使我受益终身。
增福伯伯说的是《左连成告状》,这部书选自公案小说《刘公案》,是一种鼓词形式的小说。增福伯伯说书完全像背书,语速快,没有特别吸引人的特色,所以,一部《左连成告状》很快就说完。有一次人们恶作剧,在增福伯伯说得起劲时,一个个悄悄地从门上溜走,增福伯伯看不见,一直还在说,等说完一段,屋内仍静悄悄的,就剩下他和二掌柜两人,直让两人哭笑不得。
随着这些说书人的老去,街里的说书人就断了档。后来听说比我们低一个年级的小学同学马贵生在楼西街说《小八义》,但我们村子太大,到了别的街上就像去了外村,因此便没有去听过。
其实,村里还有一个真正会说评书的人,叫师秀山,他曾是村上业余剧团的演员,善演反面角色,在歌剧《刘胡兰》中扮演石三海,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坐山雕,在《红灯记》中扮演鸠山,演得活灵活现,但他不轻易表演评书。仅有一次看戏时,在戏场中见他表演过一段评书,之所以说是表演,是因为他说书时加有身段动作,所以更加精彩,可惜他过世后,把一身技艺带走了。他的儿子后来也能说书,曾在文水县开栅镇一带说过评书,很受人们欢迎。
后来,村上实在没人说书了,孩子们就自己学着说,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叫二元的大孩子说的一次书。
有一年冬天,街上一帮孩子们趁着月夜玩耍,不知谁提议,要让二元说书,二元欣然答应,于是孩子们便集中到当年二掌柜住过的羊圈屋听书,进到羊圈屋,发现房子顶已经塌漏出几个窟窿,明亮的月光从窟窿泄到屋里,尽管天气冷,但大家听书心切,仍旧在那个小屋听二元说书,他说的是一段神话短篇故事《石头人》。说的是一个侠义之士得了一尊石头人,这石头人有一特殊本领,每当这个义士寡不敌众时,他就一拍石头人的肩膀,石头人便跃起身来,一头撞向敌方,将敌方撞死撞伤。故事不长,倒是也吸引人,可惜二元没看过大部头侠义小说,也就再没有给大家说过其他的书。因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非常特殊,所以,一直萦怀不忘。
李世林(汾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