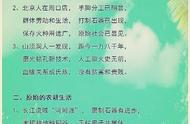格伦·古尔德 Glenn Gould (1932 - 1982),加拿大著名钢琴家,被誉为20世纪最具精神魅力的钢琴演奏家之一。他早年就蜚声国际,之后录制了诸多著名唱片,其中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等曲目已被奉为当世经典。
第一种可能,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听过一首音乐作品的演奏,只是看过这个音乐作品的谱子,然后就认为这个作品太伟大了。第二种可能,一个人特别钟爱这个作品,但特别讨厌所有演奏这个乐曲的,因为他都觉得离这个作品的本质差得太远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爱这个作品。我相信几乎是没有这两种可能,除非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所以你对一个伟大作品的认知,恰恰和你对这个作品的喜爱程度是成正比的,甚至是完全连在一起的。你可以说演奏只是作品的一种实现,但这个实现恰恰是使一首音乐作品,能成为“音乐”的最重要的一环。
新京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于大众的音乐史写作的一种误区,就是过于注重作曲家和创作者而忽略了历史上著名的演奏者和歌唱家。
张昊辰:我觉得肯定会有这种影响。在《演奏之外》的第四章,我大概提过这一段历史,虽然提得比较简略,但大致来讲,作曲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获得类似今天的地位。作曲家有些时候只是服务于特定场合。几乎可以说,创作者的地位是低于演奏者,演奏者是低于他要服务的场合。当时经常有演奏者碰到海顿和莫扎特作品,然后演奏者说,你这个太难了,我们演不好,能不能改简单?这种状况说明了当时作曲家并没有受到演奏家太严肃的对待。现在的演奏者不可能说,这个作品我演不太好,所以我就不演了,或者要改简单。这种情况到了贝多芬之后才有一定改变,因为贝多芬是真的没有把观众和演奏家太当回事。他把自己看得最重,他不妥协任何的外部的限制。

电影《莫扎特》。
当了解这段历史后,我们可以从海顿、莫扎特的历史阶段一直往前推,当大家知道古典音乐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样子,作曲家是什么地位,他肯定会重新审视当下。
新京报:我在《演奏之外》中读到了你对不同民族语言和音乐的关系的见解。我对你的论述也很有兴趣,但是只恨自己对意大利语和德语完全不懂。你在西方不同地区音乐作品中感受到的语言对音乐的影响有多可观?另外,相比语言音调、词曲牌以及音乐旋律有着很强烈相互牵动的汉语系统和中国音乐,欧洲的语言和音调对西方自发形成调性音乐和复调、和声是否也有一定的作用呢?或者说,复调音乐及和声产生的契机会是什么呢?
张昊辰:我没有对这方面有研究,尤其对中国本身的民族音乐史,所以我自认为不太有资格去大谈特谈。但作为一个学习西方音乐的人,我可以站在古典音乐的角度上,稍微做一个比较,一种音乐肯定是民族的文化,或者整个意识形态的产物。
尤其我觉得,音乐作为这么抽象并且有灵性的一个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和整个文化的连接会更深。从西方音乐来说,我知道它主要的特点还是调性。一方面我觉得文艺复兴的思想与艺术解放对复调音乐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教皇明令禁止出现复调,因为教廷认为展示上帝的声音应该是干净的,不应该有其他的声部跟它在一起;第二个是大小调体系的建立,大小调体系建设,如果之前的宗教调式是以主音作为一个调的核心,大小调体系之后,是主和弦作为一个调的核心,比如和声的存在。我说两点,第一个是,复调强化了对位,大小调体系的建立从调性上强化了和声,所以这两个是整个西方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能够形成的两个大前提。

欧洲中世纪音乐。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流行音乐、爵士乐等等深受古典音乐的影响,我们能看到整个西方音乐所发生的历史变化。这种发展当然和中国的音乐非常不一样,比方说在和声领域,我们强调主和弦,但这个主和弦,如果它代表稳定的话,代表和谐的话,一定要以一个跟它最不和谐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属七和弦——一个紧张的和弦“解决”,才能成为稳定的主和弦,所以有一个不和谐和和谐之间的对立。这个在东方文化的意识里,是不存在的,我们不需要强调这样一个逻辑。西方音乐对于冲突有一种迷恋,无论在希腊还是在基督教文化都有,必须有一种二元对立的东西,这个东西最后能够被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某种前提或者过程之后,才发生的。
所以,我记得查尔斯·罗森说过整个西方音乐,就是一个围绕着“终止”这个概念进行的一系列创作。无论是一个乐句的终止,一个段落的终止,还是小到两个音之间的一种终止关系,还是大到整个作品,最后要走向的整部作品的终止。包括怎么延迟这个终止,然后强化这个存在。怎么样设下一个终止的陷阱,怎么改变这个终止,否定这个终止,但最终又走向这个终止等等。但是这个前提就是,所谓终止,一定是通过某种跟终止对立的东西,然后达到了终止,也就是我们是回到了一个终止,从对立的那个对岸回到终止。这种二元性,在东方文化里面并不存在,我们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与整体和谐。我们避免冲突,所以说,你可以提出为什么中国音阶一直是五声调式,我们不是没有七个音,但是我们只用五个音,我们偏爱用五个音,省掉的那两个音,正好是两个不和谐音。
突破与捍卫:贝多芬与勃拉姆斯的成败
新京报:你在《演奏之外》里面也曾经提到过贝多芬的《降B大调第二十九钢琴协奏曲》(下文简称Op.106),尤其是关于调性的分析和否定的力量那里,我觉得非常精彩。我非常关心这个作品的第三乐章,很多不同的人对这里提出过不同的见解,罗曼·罗兰他好像提到过关于回归宗教的问题,克列姆廖夫曾经说过第三乐章是一个悲剧的发展及对激情的拒绝,并且含有从社会回归个人的路径选择。杨燕迪先生则判断贝多芬晚期的基调,是对苦难的和解。
再比如像贝多芬晚期的第九交响曲,他在最后的合唱乐章具有一种不断把前面乐章出现的材料进行否定的处理。比如说,第一乐章的动机出现,然后被器乐歌唱化的宣叙调打断,第二章乐章的D小调主题闪现,也被打断,然后直到第三乐章的沉思,把这些都打断以后,《欢乐颂》出现了,他的这个处理似乎也有一种突破,表达非常直白,贝多芬似乎有把交响曲形式逻辑性表达转化为偏向内容表达的意味。您对晚期贝多芬有一种怎样的判断呢?
张昊辰:你刚刚提到《欢乐颂》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欢乐颂》的动机,在前面的乐章就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贝多芬到了晚期,尤其是他的弦乐四重奏中出现了阿多诺所说的“分裂的征兆”。但是在这之前,某种“整体性概念”在他的作品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贝多芬的伟大可能在于,他能够给自己设定各种各样的阻碍,或者说分裂的征兆,最后还能够把这些分裂的动机全部回归为一个整体。把它扩展到一定的极端,再拉回某一个中心,这样形成的整体性,就有了更加强烈的凝聚力和张力。这个我在自己写贝多芬那一章的时候,也有提到。你刚提到的Op.106就是一个典型。

位于维也纳的贝多芬故居。
新京报:那么你对Op.106的第三乐章是怎么体会的呢?从一个外行人的观感,我能够认知到这个乐章巨大的处理难度,无论是体现在篇幅,还是表达上的复杂性,这个乐章对于背谱演奏应该是很有难度的吧?
张昊辰:对我来讲好像不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很难背谱演奏的作品。贝多芬的作品我觉得是容易背谱演奏的,比如Op.106,因为逻辑性特别强,只要你能抓住这个逻辑关系,整个曲子的脉络就会显得非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