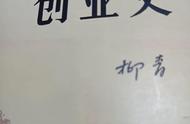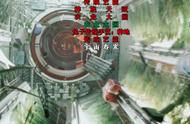人都有爱美之心,追求美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
但生宝心里有两个念头在互相矛盾。有时候他想:改霞人样俊,心性也好,他要争取和她成亲。并且,从她看他的表情和眼神判断,他是有把握的。最大的阻碍是改霞她妈的顽固。但这只要他俩两厢情愿,也不是大的问题。有时候他又想:“算了吧!人家上了三年级啦,恐怕这阵心大了,眼高了。咱庄稼人,本本分分,托人在什么村里瞅个对象,简简单单结个亲算哩。”他想:这样更实际些。自己负起了互助组搞丰产的责任,哪里还能为亲事分心呢?他这样想的近因,是那天改霞在漉河桥和他说话,不像从前那么热情;脚拨弄着路上的小石头块,心里恐怕有了其他的想法吧?脸上也有些捉摸不定的恍惚神情。再没比恋爱的青年人敏感了,对方一丝一毫的变化,都能感受出来。
但改霞白嫩的脸盘,那双扑闪扑闪会说话的大眼睛,总使生宝恋恋难忘。她的俊秀的小手,早先给他坚硬的手掌里,留下了柔软和温热的感觉,总是一再地使他回忆起他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一块的那些日子。
生宝希望给什么人,说说他这心内的矛盾,帮助他下个决心。但他给谁说呢?谁能帮助他下这个决心呢?有一回,他想对区委王*倾吐衷肠,话已经从喉咙眼涌上来了,他的嘴唇和舌头,积极准备发音了,他的具有高度意志力的理智,又把话扣压起来,退回心中去了。
“给组织说这个做啥?”他在心里嘲笑自己的无聊,觉得对个人问题的纠缠,和为大伙谋利益的活动,是多么不相调和啊!
在互助组分稻种的这天黑夜,生宝从那天傍晚郭振山劝改霞进工厂的同一条路上,往南走去。他去找冯有万。一方面,他要批评有万,在秃顶老汉要分稻种的时候,不该气愤地掼下秤杆走掉;缺乏忍耐心,终将使自己不能在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坚持到底。另一方面,他就是想把他对改霞的心事,告诉有万,看他能给他出什么主意。
再不能拖延了!买稻种的任务完成以后,他得即刻开始为互助组进山做准备了。等到过了清明节,互助组的人就在终南山里头啰。他不能让给自个儿搞对象的念头,老是分散社会事业的心思。若是拿定主意和改霞谈,他希望在他进山以前。
夜色苍茫中,还没消散尽的做晚饭的炊烟,在复种青稞的稻地上飘浮着。生宝在牛车路上走着,噙着他的一巴掌长的烟锅,吸着旱烟。带着办成功一件事的暂时的轻快感觉,生宝想着:改霞对他这回的行动,心里会怎么思量呢?当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嫩草芽!渠里的流水!稻地里复种的青稞!你们为什么不把那天郭振山对改霞说的话,让这个恋爱的小伙子知道呢?
到岔路口该拐弯的时候,生宝站住了。东面稻地塄坎的小路上,过来一个黑影子。生宝不是看出,也不是从脚步声听出,而是从这条路只通向有万家的草棚屋,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万,你到哪里去?”生宝在月光中先开口问。
“你到哪里去?”有万反问。
不需要更多的问答,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是互相寻找了。这两个小伙子是这样的关系,自从搞起水稻丰产互助组以后,两个人只要是同时都在村里,他们就连一刻也不愿分离。共同的事业常常把肉体上是两个人,变成精神上是一个人,彼此难舍难分。生宝直到如今,还没有把他对改霞的心思告诉有万,主要因为有万太任性了。生宝恐怕这个愣家伙在不适当的场合,拿这事开玩笑。
“走!生宝。到你屋里去吧!”戴黑制帽的有万,拉着包头巾的生宝的袖子,说,“光棍屋里好拍嘴嘛!昨黑间,我就要在你炕上拍一夜来,见你出门这些日子,太乏了,叫你美美睡上一夜,咱再拍嘴。今黑间,我已经给屋里打了招呼,不回去睡了。”
生宝站着不动,在月光中笑着,盯住有万的胖脸盘。
“金姐娃没问你在哪里睡觉吗?”
“她知道我在你屋里。你甭瞎拍!人家相信咱自进了她屋,一心不二。”
“你经常在我屋里睡,她能乐意吗?”
“我告诉她互助组有事,她没二话。不是在你跟前卖嘴哩!当初进她家的门,咱就同说话人敲得响明:她娘俩日后,不能干涉咱的积极性儿;要是拖咱落后,咱可不干。”
“噢呀!你立场站得那稳?”
“当然!人没立场,如比树不扎根。你看吧,咱早晚要和你一样!”
“和我一样做啥?给她娘俩轰出来,再打光棍吗?”
“瞎拍!咱也要和你一样,入党!”
“就凭今儿俺伯分稻种时,你那股邪劲吗?王*帮咱们订生产计划时,说你啥来着?要想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就得有忍耐心。你忘了吗?像你这样,到四五月生产紧忙的时光,咱能团结住大伙吗?”
“那股劲儿上来,唉,生宝,就像有鬼拨弄我一样。”有万愧悔地说,“我从你院里出来,在回家的路上,就后悔哩。心里恨自己:‘你这是做啥?一也沉不住气!看人家生宝拿得多稳!’咱想返回来,又觉着怪没脸的。咱这就是寻你检讨来了。走吧,到你屋里细拍!”
这个辕牛一般强壮的小伙子,拉着生宝的一只胳膊走了。他和生宝在蛤蟆滩来说,算庄稼行里数一数二的把式。犁、耙、锄、割、扬种、插秧,除了铁人郭庆喜,没有比得上他俩的。这是他们熬长工熬来的本领。有万比生宝更长的,是惊人的体力。从终南山往山外运木料,别人掮四根杨木椽,他掮八根。他比生宝差的,是他那火药性子,谁说话做事不合他的脾性,他好像滚油煎心般,不能忍耐;但是过了那一阵子,他自己也觉得这样急躁没意思。
生宝最了解他。他知道有万这性格,是幼年时候形成的,很难一下子从根改变。人们不是说:幼年亡父、中年丧妻和老年失子,是人生三大不幸吗?那么有万和生宝都是孤儿出身。所不同的:生宝很快随母改嫁,得到继父梁三的荫庇;而有万很快连母亲也死掉了,在他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以前,是在下堡村讨饭的一个野孩子。他本姓高,和高增福原是近族,两年前,做了一个寡妇老婆的独生女儿——金姐娃的进门女婿,才改姓了冯。在他能够懂得道理以前,他只知道恨——饥饿的时候,恨他看见正吃饭的人;寒冷的时候,恨他看见穿得暖和的人;想娘的时候,恨那些跟着妈的娃子……当到他懂事的年龄,这“恨”已经渗入他的气质,变成暴躁的性格了。他知道这样不对,但到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有时恨不得用耳光子,改变某个农民落后的一面。
虽然这样,生宝喜爱有万。因为他那苦难的童年,不仅造成他性格的缺,也给了他正义感和意志力。一个人在小时受过艰难的严格训练,比十个娇生惯养的人还有用。有万的绝对公正、嫉恶如仇、见公共事一马当先,使得生宝感到互助组有这个人,搞丰产的信心更强了。
两个知友,在生宝的草棚屋小炕上睡下了。他们吹熄了灯,就打开话匣子了。
在生宝买稻种不在家的时候,蛤蟆滩发生了几件事情。首先,上河沿李二和李三弟兄俩,为争地界边子,又干了仗。其次,前国民党军下士白占魁正月去了西安以后,他的风*女人翠娥最近开始很活跃,三天两天往黄堡街上跑,可能又和什么人乱搞。最后,有万说到高增福寻他去追富农转移粮食的事儿,说到郭振山不带头搞互助组,整个官渠岸都是涣散的、死气沉沉的,看来高增福很苦恼……牵扯到另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党里头的事情,生宝照例谨慎地不对这个直性子人表示什么。
当生宝把他对改霞的心事告诉了有万的时候,他们的谈话热烈起来了。
“啊呀!有这美事,为啥不早告诉我哩?”有万一听,使劲推了面对面睡着的生宝一把,大为不满。但是随即他又笑了,问,“你啥时候起了这意?”
生宝告诉他在改霞解除婚约以后。
“我不信!”有万断然地说,“保险你两个在土改时……”
“低声!”生宝推一推他,“俺妈和秀兰在对面草棚屋里醒着,你吵啥?”
有万压低了声音。
“保险你两个在土改的时候……你这阵坦白!”
“没!”生宝很正经地说,“接近是接近来,干干净净!旁人看见我那常病的媳妇要死不活,就那么胡猜哩,其实冤情。你看咱是那号乱七八糟的人吗?”
“那么,你们……”有万粗野地问,“搂抱来没?”
“没!”
“亲嘴来没?”
“没!这号烂脏话,你怎么说出口呢?”
“那么男人和女人怎样相好呢?”有万不在乎地笑着。
生宝第一次怀着深深的感情,娓娓动人地对人谈叙他和心爱的人中间的秘密。
改霞和他一道在县城里,参加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每天傍晚,青年代表们纷纷在县城的街巷里转游。改霞在街上向生宝提议出城去。他们出了东门,在绕城的漉河边,遛了一个圈。他承认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私交——改霞向他倾吐自己对包办婚姻的不满,要求他帮她出主意,怎样才能解除婚约;他建议她利用代表主任的威信,争取她妈的谅解。后来,改霞又对他的不美满的婚姻,表示惋惜和同情,攻击旧社会数不尽的罪恶。他从她眉眼间看出她对他满怀着柔情……
“家伙!真有福!”有万听得入了神,很羡慕。他又热心地说,“是这,赶紧下手吧!你那是前两年的事,改霞这阵手稠着哪!”
“咱不怕她手稠。”
“你甭吹!讨卦的人嘴拍多了,泥菩萨还给好卦哩,慢说一个闺女家。你知道吗?伸手的尽是知识分子啊!”
“郭世富家的永茂吗?”
“嗯!听说还有教员、区乡干部……你一个泥腿子,有把握胜过人家吗?人家穿四个兜的制服,见天洗脸、刷牙,身上一股胰子味……”
“咱不怕她手稠!”生宝坚定地重复说,“不管有多少人提亲,关口在改霞本人的思想儿哩。要是她的心变了,爱上知识分子了,咱不同人家争!她的思想儿变了,那就说:不是咱的人啦。你说对吗?咱打定主意走这互助合作的道路,她和咱不合心,她是天仙女,请她上她的天!”
“对!你说得对!”有万多么钦佩生宝这实际态度,“那么,你就和她谈上一回!要红要黑,干脆一家伙!怎样?”
“我就是这主意!……”
但生宝心下,却仍然希望改霞没变心。只有看到什么明确的现象,证明改霞确实变了心,生宝才能把改霞从他心的深处挖出去。他希望很快和她谈一次话。
他苦于缺乏不被人注意的机会。这不是冬季,农村里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很少公开接触的场合。开学以后,改霞团的关系又转在下堡小学,连开会也不在一块了。黑夜,改霞如果自己不出来,生宝又怎能撞进那柿树院去呢?那柿树院的土围墙只有一人多高,一个人从外头踮起脚尖,可以看见院里;但它对规矩的生宝却真高似青天,不可逾越。怎么办呢?
两个朋友睡在草棚屋的小炕上,低低商量着,有万帮助生宝想着约会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