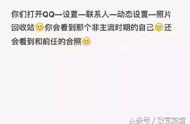黄堡镇前街是商业地区,后街净庄稼人住户。生宝现在走在比较狭窄的庄稼院街道上,他觉得比拥挤喧嚣、充满尘土的前街,舒服得多了,清爽得多了。
把所有在市集上要办的事务办完以后,摆脱了有万,个人的不畅快重新涌上梁代表心头来了。
不畅快!是不畅快!改霞思想的变化,使他心情上很不畅快。他觉得心里头怪别扭的。
生宝喜爱改霞的聪明、有志气和爱劳动。并不是他有意瞧不起一般的女青年群众,实在说,改霞坚持解除婚约的坚定性,她在农忙时节和来帮忙的姐夫们一块下地的吃苦精神,她对公众事务的热心,和她大姑娘在小学生娃们中间上学求知识的落落大方,是闺女里头少有的!正是她的这种意志、精神和上进心,合乎生宝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他觉得:他要是和改霞结亲,他俩就变成了合股绳,力量更大了。
现在,改霞既然有意思去参加祖国的工业化,生宝怎么能够那样无聊?——竟然设法去改变改霞的良好愿望,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为了祖国建设,他应该赞助她进工厂。想到这里,生宝就努力克制心中的不畅快!但每个人精神上都有几根感情的支柱——对父母的、对信仰的、对理想的、对知友和对爱情的感情支柱。无论哪一根断了,都要心痛的。在生宝对另一个女人发生兴趣以前,只要一想到这件事,他就不会畅快的。
生宝带着爱情上失意的心情,踏进挂着中共黄堡区委会和区公所招牌的街门。
噫!区公所占的前院,在有几棵正发芽的刺槐的土院子里,庄稼人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里三层外三层,挤成一大团。有的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往人群中间瞅;有的歪转包头巾的脑袋,把耳朵对准人群中间细听哩……
生宝想:“看啥热闹呢?出了啥事情呢?”
他也走到人群边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从人头上边往中间看。看不见。他也歪转包头巾的头,听人群中间说什么。听不出头绪。他只听见——
一个声音说:“你看!你看!这是伤!这!”
另一个声音说:“你就说我把你打死了来,你还在这里说话?说的不算!哎!”
生宝在人群的外圈儿,听得中刘村的庄稼人,谈论所发生的事情。
这是黄堡区东原上中刘村的哥俩——老二和老三——在闹事。老大是今早去世的,尸首还停在脚地,没装进棺材哩。两兄弟不忙着大哥的丧事,却忙着打官司,因为老大没儿子,两兄弟都争着要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亡兄。老二的理由是:按顺序,挨他的儿子、挨不到老三的儿子。老三的理由是:他三个儿子,而二哥只有两个儿子,应当讲公道,不能光讲顺序!亲戚、邻居、门中人,挤满当事人的院子,说了一早晨,没说倒,才来到区上,因为必须立刻决定谁是孝子,好办丧事。当他们在这里说理的时候,他们的婆娘们和娃子们,在家里大哭死者,尽嗓子哭,简直是嚎叫,表示他们对死者有感情。其实,他们都是对死者名下的十来亩田地有感情……
生宝听了挖心地难受。他在整党学习中,听了区委王*社会发展史的通俗报告。他现在又在痛恨一个可憎的名词——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使继父和他别扭,使这两弟兄不相亲,使有能力的郭振山没有积极性,使蛤蟆滩的土地不能尽量发挥作用。快!快!快!尽快地革掉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有人类自尊心的人,生宝要把这当做崇高的责任。
生宝不喜看这幕丑剧。这是人类的丑剧!生宝怏怏不乐地离开这个场合,他劝大伙都不要看。他说这弟兄俩太没意思了。
当生宝进到后院区委会院子里的时候,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憎恨,在他心情上控制了失恋情绪。对于正直的共产党人,不管是军人、工人、干部、庄稼人、学者……社会问题永久地抑制着个人问题!生宝不是那号没出息的家伙:成天泡在个人情绪里头,唉声叹气,怨天尤人;而对于社会问题、革命事业和党所面临的形势,倒没有强烈的反映!
“王*在家吗?”生宝站在区委会院子里,带着战斗者的情绪,精神振奋地喊叫。
听见从里头开门的声音。一只手从里头挑起了白布门帘。王*胖胖的脸带着欢迎的笑容,站在门外的砖台阶上了。区委*身量并不高大,但却敦实,离着多远就伸出胳膊,好像要把生宝拉进屋里去:
“来来来……”
生宝带着兄弟看见亲哥似的情感,急走几步,把庄稼人粗硬的大手,交到党*手里。
如像某种物质的东西一样,这位中共预备党员的精神,立刻和中共区委*的精神,融在一起去了。弟兄之间,有时有这个现象,有时并不是这样而像中刘村那两兄弟一样。就是这位外表似乎很笨,而内心雪亮的区委*,去冬在下堡乡重试办整党,给生宝平凡的庄稼人身体,注入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入党以后,生宝隐约觉得,生命似乎获得了新的意义。简直变了性质——从直接为自己间接为社会的人,变成直接为社会间接为自己的人了。他感谢他的启蒙人王*。他乐得大张着嘴巴,笑呵呵的。这时对改霞的不畅快,和对中刘村那哥俩的厌恶,已经从他精神上消退掉了。
王*拉住生宝的庄稼人硬手,笑盈盈地说:
“你来得正好!你看屋里坐个谁?”
生宝肥厚的庄稼人脊背,被王*的一只手亲切地按摩着,他脚下很轻地走进王*屋里。他喜得简直要像小孩子一样跳起来了。
“啊呀!杨*嘛,你啥时来?”
县委副*从屋子后窗前的一张木椅子里,站了起来。他带着喜出望外的笑容,大踏步走到门边,用左手握住生宝的右手,把右手搭在生宝的白小衫肩膀上,老大哥对小兄弟似的亲热地说:
“我们正商量到你们蛤蟆滩去呢。”
“那么咱们一块走嘛!”容光闪闪的生宝高兴极了。
杨*说:“你来啦,我们就不去了。县委上打电话,叫我今天回县哩。我忙着哩。……”
三十岁上下的县委副*两只炯炯的眼睛,发射着智慧的光芒,赏识地盯着这个包头巾的年轻庄稼人,直盯得生宝怪不好意思起来了。生宝从正月里在县委同陶、杨二位*谈话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一种感觉:似乎他这个莽莽撞撞的年轻庄稼汉,对党实现一个伟大的计划,有些用处。在当时,这种感觉还是模糊的,不敢肯定的;现在杨*对他的这份亲热,这份喜欢,这份信任,就使他确信他感觉对了。
当杨*左手握着他的右手,右手搭在他肩膀上的这一时间,生宝心中感到相当的不安。党是不是把他看得太高了呢?他是不是真的对党改造农民有很大的用处呢?他当然希望能实现他的豪言壮语。但愿他能兢兢业业,不要让党错宠爱了他吧!他的心情有紧张,他感到担子的重量。但是这位相当活跃的陕北老同志,却拍拍生宝的肩膀,笑眯了眼问:
“怎么着哩?小光棍汉!寻下个对象哩没?”
“还没……”生宝怪不自然,他想起了刚才和改霞的决裂。
县委副*大不称心地说:
“怎么忸忸怩怩?这么棒的小伙子,中共预备党员,寻个对象有什么难哩?又不要花钱?”杨*转向区委*问,“还要花钱吗?经过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还要花钱吗?”
区委王*带着下级的谦逊,笑说:
“不要花钱,恐怕要花些时间。”
“对!”生宝得到了启发,“着重是忙得顾不上……”
“把它当成副业嘛!不要专门谈恋爱嘛!哎哎,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刻板吧!我说可以公私兼顾,你说呢?佐民同志?”
杨*和区委王佐民*,两人笑得呵呵的。生宝紧张的心情,被县委副*这一番笑谈,一下子冲得烟消云散了。同志间政治上的关系和劳动人中间感情上的关系,竟融合得这样自然呀!生宝这个刚入党的年轻庄稼人,不禁深有感触。他觉得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而庄稼人之间的感情,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不常常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庸俗人情吗?邻居间在利害一致的时候,相好得那么俗不堪言;一旦错收了一颗鸡蛋,拌几句嘴,就该别扭多少日子了。
着杨*招待的一支纸烟以后,极端兴奋的生宝并顾不得吸。他庄稼人拿惯旱烟锅的手,笨拙地拿着冒烟的纸烟,坐在杨*旁边的一个小凳上,只顾向前倾着茁壮的身子,眼睛专注地望着穿一身灰制服的县委副*。这位杨*外表很像下堡小学的体育教员:高大、结实,留着很精神的小平头,脸上带着一种健康的粗糙,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旷野里长大的劳动人,不像是房子里长大的知识分子那么纤细、白净和文雅。生宝看着看着,动了感情。他那么亲切地问:
“杨*,你比正月里我在县上见你时,精神!”
杨*说:“是吗?也许是这么个事情。我是个贱皮,宜跑!一下乡,能吃能睡。一个月不下乡,就萎靡不振,这塔也疼,那塔也疼。……”
“这是长期做农村工作的习惯。”区委*王佐民尊敬地评论。
生宝曾经从区委*嘴里听到过这位杨*的一些身世。父亲是一九三五年安塞战役倒下去的英雄,母亲被凶恶的地主领着残酷的敌人,捉住凌迟死了。革命家的儿子靠同志们的抚育长大起来,在延安上保育小学。边区中学毕业以后,烈士的遗孤,从乡文书一直工作到担任区委*的职务。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本县的时候,他是县委宣传部长;现在,杨*分工专管互助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