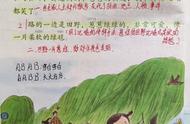在 3·21 空难现场,搜救队找到了一份《客舱乘务员岗位职责》中,第一条的第一个词是“保障安全”,在全文九条意见中,“安全”两个字就出现了六次。它原本被张贴在MU5735机舱的内部,如今成了空难遗物之一。
民航系统的安全,由一套复杂的体系在提供保障。每个人在其中各司其职,只是有些人的工作被人看见,有些不被看见。
28岁的小望属于后者。他是机场的一位地勤人员,平时的工作包括安检、开包、巡查等。
执勤的日子,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天 2000多个的蹲起运动——他要手持安检仪,不断蹲下和立起,为乘客进行从头到脚的检查,以及,不断重复提醒的,“把雨伞钥匙充电宝提前拿出来”。
在正常情况下,一名乘客从进入安检口到通过的时间,不超过半分钟,但小望每次站在固定位置的工作时间,一场要接近5个小时,期间,他不能离开,也不能携带手机。每次上岗前,他都会提前喝好水。

在“安全”这件最重要的事情面前,个体的需求,被放到了更加靠后的位置。
有一次,小望着急上厕所,但接班同事晚到了一会。他只能在每次蹲起的时候,抓住机会喘口粗气,分散注意力。此后几周,要不要喝水都成了小望上岗前要纠结的问题。
民航人围绕安全的努力,会以五花八门的形式出现。
一次飞行过程中,有乘客被项坠卡住。卡卡走到乘客面前,快速地说着在训练过程中已经说过无数次的话:“您好,我是乘务员卡卡,我将为您提供紧急帮助,可以吗?”在得到对方的点头后,她立刻站在乘客的身后,伸出双臂环绕在病人的腰部,不断用拳头多次挤压对方腹部,实施了海姆立克急救法。
当项坠被吐出后,机舱里响起了掌声。
“我会心脏复苏、懂航空安保、知道怎么紧急接生、必要的时候还能带着大家一起野外逃生。”实施海姆立克急救,对卡卡来说不算大事,她所在的航空公司,还有同事在飞机上帮助过产妇接生。

安全意识的不断强化,有时候会被上升到“奉献”的高度。
“比待遇越比心胸越窄,讲奉献越讲境界越高。”东方航空西北分公司在办公楼里贴着这样的海报,还配上了一线员工的工作图。
2021年1月,东航董事长刘绍勇曾在新年为员工撰写文章《向往的生活》。“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文章里,他引用了《庄子·天道》的内容进行,在刘绍勇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简单质朴。
东航在业内有“奉献航”之称,当然,这其中有褒赞,也有着业内人的嘲弄之意。2020年年底,行业自媒体“民航一枝花”做了一场关于国内航司员工对公司满意度的调查问卷。在这份满分为4分的答卷中,东航得分为 2.04 ,即接近“不满意”,排名落后于厦航、国航和深航。
04 离开MU5735带着中国民航最好的安全历史离开了——超1亿小时的安全飞行纪录。
傲人的安全成绩,是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发生多起飞机失事时候后才开始建立的。多次空难发生后,中国民航局不仅加强了安全监督,还与国际多个飞行安全公司展开积极合作,建起起更加完善严苛的飞行制度。
2007年,《华尔街日报》发文称,中国在航空安全方面超过了美国多数地区的水平。但或许安全本身是一场“墨菲定律”,就在《华尔街日报》激情夸奖三年后的2010年,伊春空难发生了。

自此之后,直到今年3月21日,中国民航人创造了安全飞行超过1亿小时的世界纪录。这是飞机之所以成为最安全的交通方式的重要原因:所有的事故都会被最细致地复盘和总结经验,最大程度避免悲剧重演。
如今,这个纪录已经以132条生命为代价清零。
失事飞机的两只黑匣子,目前正在北京被破译。所有人都在等待真相,因为这场事故在业内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航空专业人士形容它:在极佳的空管体系、极佳的航空公司和极佳的飞机的背景下发生的灾难。
但海恩法则也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所有的灾难总归是有原因的,只是,有些能凭人类之力找到,有些暂时还不行——比如那架消失的MH370航班。
随着 “3·21“ 现场搜寻工作进入尾声,这场灾难带给世人的悲痛,终将随着时间慢慢减弱。遇难者家属要在更漫长的岁月里,接受这场悲剧带来的后果。
“估计又有很多同行要离职了”,卡卡猜测。疫情三年,民航人的整体收入已经大打折扣,空难带来的沉痛,大概率又会加速很多人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