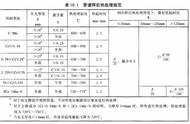散文:二十二朵玫瑰
文·傅杰
侄子三十九岁,媳妇是北京人,他们结婚时我正在部队服役。我复员以后至少有三年时间才见到他们,那是个中午,在自由市场里,他们经营着一个蔬菜摊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暂时立起来的;快到春节了,小两口从外地批发一车青菜,应节赚点鞭炮钱。
侄子是瓦工,卖菜之前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干。
我问他:“北京干好好的,怎么回来了?”
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老想家,最近有个想法,打算在县城买一处民房,然后把他我妈接来住。”
我说:“北京离咱老家也不远啊,想家就回来看看嘛。”

侄子说不行,他的理由是,老家在山里,从北京回来下车还要翻山越岭,回趟家太难了。次年春,侄子在几个姐姐的帮助下,在县城真的买了房子,没多久,就把他妈从老家接了过来。
侄子三岁就没爸爸了,他爸患食道癌,去世那年我已经记事了。
我恍惚记得,我和几个小伙伴在老哥家的当院玩,隔着玻璃,看见老嫂怀里躺着老哥的半个身子。老嫂像哄孩子睡觉似地拍打着老哥的肩膀,身子还轻微地前后摇动着。她的身边趴着一个孩子,一会爬窗台,一会爬炕沿,老嫂总在孩子危险的时候腾出手来拽一拽。那时候,大人们都说老哥长了噎食,其实就是食道癌。后来一个米粒都咽不下去了,光喝水,再后来连水都不能进,老嫂就把毛巾沾湿了给老哥润嘴。那时候医疗条件太差,老哥得了这样的病只能等死。赤脚医生一天跑八趟也不管用。老哥去世那年四十多岁,给老嫂留下俩儿子,四个女儿。这几个孩子肩挨肩降生到这个世界,一个不让一个,可是自从老哥去世以后,他们都知道疼爱小弟弟了。侄子是在哥姐的呵护与疼爱中长大的,他初中毕业后选择北京落脚,也是因为四个姐姐都在北京。后来他想把老嫂也接到北京,老嫂不去,跟侄子说:“我去了北京,你大哥咋办?”于是侄子就搬回来了,把家安在了县城里,他说他要跟他哥哥一起,尽到孝心。

侄子前年诊断出胃下垂,我给他做过一段时间的手法治疗,他说没什么感觉,就改吃中药。去年一年的时间,他的身体还算不错,从喝酒上我就能看出来。可是两个星期以前,侄媳妇突然来我家,说侄子有可能得了胃癌,县医院不敢确诊,又去市医院了。我有些不大相信,觉得充其量也就是个胃溃疡。但我说不出不相信的理由,只好等待市医院的病理切片,结果是“低分化腺癌”。侄子拿着报告单问我,这个癌长在啥地方?我说胃窦部。他又问这个癌到底是咋回事?我担心他心理负担重,一开始说得比较含糊。要知道,有相当一部分癌症患者都是吓死的。也就是说,还没跟病魔搏斗呢,精神首先崩溃了,癌细胞乘势迅速繁殖。可我又想,侄子毕竟年轻,心胸也不小,放在老人身上可以隐瞒,说些善意的谎言。侄子需要这样吗?帮他分析一下病势,就像打仗一样,做到知己知彼岂不更好!于是我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并鼓励他要敢于面对,敢于承担,要相信医生,相信科学。我始终以为,在大灾大难面前,就要想到大处和亮处。
侄子态度是乐观而坚定的,去医院手术的时候跟我说:“我妈身体还不赖,媳妇长得也不丑,关键是两个孩子还没成人,我决不能死,必须活着!”我相信侄子的豪迈,虽说他是在宠爱中长大,但他这种不屈抗争的性格,是决定他生命的关键。果然,术后第一天他就去卫生间刷牙,同时还可以下地溜达一会儿。我去看他,发现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挂着吊瓶,还跟陪床的外甥开玩笑。见了我就让我看他的刀口,说刀口很长,缝了22针!他说着就要解绷带,我没让他解,他仍那么低着头,一只手护住另只手,温情地摸索刀口处。抚摸了好长时间也不把手放下,还自言自语:二十二针,二十二针呐!那样子仿佛怀抱着二十二朵玫瑰花,憨憨傻傻的,让我眼睛湿润了。我想,那二十二针就权当是命运赐予侄子的玫瑰吧,它虽然纠葛着痛苦,也能融进对未来生命的想象和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