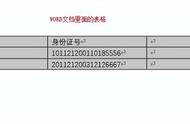午后,下起大雨。杨老先生托侄子来客栈找我,要跟我聊聊昔卜华侨的历史。我冒雨前往,他已经画好一张草图,上面标注了昔卜亲朋的住址。屋外雷电交加,屋内突然断电,光线昏暗,有些字写叠在了一起,那是他十岁时在育文学校做七七事变爱国演讲时知道的侨胞的名字。少年时代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呢。书桌上,老算盘被修补过,杨老先生和他父亲都为华人组织义务做财政。他的女儿,杨阿姨,拿出家庭相册,几十年的家庭历史在上面凝固。有一张,三十几岁的杨先生坐在汽车里,戴着墨镜,风华正茂,那时他还没有出车祸;有两张*访问缅甸时的照片,是杨老先生的朋友拍的;泛黄的那张,上面的朋友都已相继过世。

雨越下越大,屋里越来越黑。老爷子给我唱了一曲《松花江上》,因为中气不足,歌词“流浪流浪”“爹娘爹娘”被用力推送出来,加上雷电与滂沱雨声,分外催湿了我的眼睛。我一路收割人们的故事,却不能将这些故事妥当安放,时常将一段段的人生遗落在地里,最后,它们与地融为一体,我更加捡拾不回来。

昔卜偏偏又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容纳一切,甚至将我也吸收进来,仿佛我不在异乡,只是时间流转,回到从前。从前,菜市场的米店旁边,有一家理发店,店里张贴了许多油头青年的艺术照,剪发的大哥黑粗的胳膊上有大幅的纹身;从前,小镇上没有电影院,只有一个录像厅,录像厅里装了空调、沙发椅、时髦的液晶电视,看一场电影需要1600基亚,比租碟贵八倍;从前,巷口有个简陋的亭子间,只卖槟榔和烟叶,被一棵高大的缅茄树覆盖着,一伙老男人成天在那里聚会;从前,村口路边有一家杂货铺,戴着镀金耳环的小女孩儿才四五岁,每次拿可乐给我时都有些舍不得;从前,小伙子们爱骑摩托车去铁道边猜火车,或者用啤酒瓶盖、贝壳、木板雕成的十字棋盘,玩一种神秘的游戏;从前,放学路上,最爱吃一种裹着薄薄面粉的油炸蔬菜,吃完就顺道将牛赶回家;从前,家附近有个旧书摊,那里常年挂着昂山将军和昂山素季的画像,卖书的姐姐喜欢围酒红色的头巾,头巾的边缘镶着鲜红的亮片。

我常常想起昔卜,就像想起昔日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