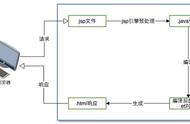(一)
我关注“死亡”这个问题有两三年了。
我开始关注的原因,是因为朋友、熟人、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地去世了。可以说许多年届不惑之年的人,都亲见了十来位身边人的死亡。
伴随着自己长大的名人去世,也会引发我们最切肤的感慨。2018年就是一个这样的年份,霍金、李敖、单田芳、臧天朔、李咏、金庸等等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在写下这几个名字的时候,觉得他们还在。2019年对我们这代中年人来说,或许也是这样一个年份,褚时健已先走一步,只留下褚橙年复一年春华秋实,周而复始。
一场亲朋葬礼就是一堂关于死亡的观摩课。一次名人去世的网上热议是一堂关于死亡的讨论课。于是,大部分中国人的死亡课是从中年开始的。

电影《寻梦环游记》展现了一种温暖的死亡观:只要还有一个爱你的人记住你,你的灵魂就不死亡。
为什么这么说呢?
性教育、死亡教育,是我们这代人从小缺少的两门课。都需要通过长大后的亲历无师自通。
性教育的缺失是个显性的问题,死亡教育的缺失是个隐性的问题,绝大部分人都没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民俗文化中有强烈的死亡禁忌,彷佛提到它就会沾上它,家长是不希望孩子谈“死”的,尤其逢年过节,只能讲吉利话。
唯物论者对死亡的处理简单粗暴:死去元知万事空。死亡可能是世界上最单调的一件事,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儒家持自然死亡观,孔夫子对死亡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生还没有搞明白,去研究死干什么?他老人家以实用主义回避了对人生终点的讨论。大多数中国人应该秉持的儒家态度。
以上就是我们怎样自小死亡教育缺失,中年爆发死亡困惑的。
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发现明末清初时代的中国人,也面临着与我们今日同样的死亡困惑。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耶稣会是晚明自欧洲来华传教的一个天主教修会,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就是这个修会的,一直延续到雍正年间,大约来了近500名会士。他们每年将在中国的传教情况等写一份总报告寄往罗马总部进行汇报,就是“年信”。

耶稣会年信的样式,图为1623年的
通过年信记载看出,“死亡”是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要处理的核心议题,从中可以窥见400年前中国第一代天主教徒是如何处理死亡问题的。
说到这里,就将“死亡”与“宗教”相关联了。宗教或许不是解释、解决死亡问题的唯一法门,但至少是很重要、很合适的门径,因为死亡是关乎另一个世界的事。
中国人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在信与不信之间(不是将信将疑,因为没有疑的成分,对不信的也不怀疑),在中国信仰者的眼中,没有异端,只有求同。我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是不认同、不否定。我是由一个坚定的唯物论者“退步”到不那么坚定了,而使我退步的原因,恰恰是科学的发展,比如量子力学,比如高维空间。
这是从认识而言的,从对待宗教的态度而言,我觉得有比没有好。在看电影《2012》世界末日降临时,有信仰的比没信仰的好受得多,没信仰的除了慌乱还是慌乱,没有归途的死亡是多么可怕呀。
但我没有半点儿劝人进教的意思。内心不受触动,劝也没用。况且像我这样内心受触动了,也还没进。
我也不奢望从耶稣会年信记载的古人的取舍中寻得答案,但至少应该有一个原则性的意见:如果不参透死亡,就过不好今世。
再回到正题上,明末清初天主教徒如何处理死亡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本身就可以引申出一篇博论,我打算分成几次讲,大体按照死亡观的转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准备死亡、临终时该如何通过圣事被接引至彼岸、什么样的尸身状态昭示灵魂得救、葬礼、墓地选址等全套流程,按时序分步骤地讲。
这次先讲死亡观的转变。
传教士观察到中国人对死亡的厌恶和困惑是很普遍的。传教士费乐德说:“中国人中对死亡的恐惧很普遍,比我们所知的其它任何民族更甚。”
中国人对与死亡沾边的事物都很忌讳。传教士伏若望在1631年年信中记载了北京有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平时甚至不能听到“死”字。1631年,南昌辞世神父的遗体和棺材停放在住院中,邻居轮流来劝他们将棺材搬走,因为停在家里这不吉利。
儒释道这三家当时在中国占比最大的信仰提供者,尤其是重视教育但死亡教育缺失的儒家,对死亡问题的处理不能满足所有人。
道家认为生死齐一,恶生乐死是种智慧;佛教相信生死轮回;儒家如前所述,遵奉孔夫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教诲,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现实生活上的事情都弄清楚了,鬼神之事的道理也就自然明白了。
无论避而不谈,还是模糊生与死的边界,死亡仍然是确知而不确定的,人们对死亡的疑惧没有得到解答,反而在沉默中加剧。一些爱思考的知识分子就去探索,在探索中遇见天主教,觉得天主教对死亡的处理方式可信,就入教了。徐光启走的就是这样的信仰之路。
教友所著《徐文定公事实》中记载了徐光启对死亡的困惑:
“徐公博学,多须参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详,诸凡玄学详学手不拜求名师,然于生死大事,无究着落。心终不安。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到南都父利子而略道其旨。”
为了“参透生死大事”,1600年还专程去南京请教利玛窦。而这一趟南京之行,在大方向上扭转了徐光启的信仰,开始转向天主教了。
学者林金水说:“利玛窦传入的基督教思想,对于处于苦思冥索、百思不解,苦闷彷徨的徐光启来说,是振聋发聩的。”
学者孙尚杨说:“天主教对人死后永福(登天堂)的许诺以及对地狱之苦的渲染确实影响了徐光启,使他将‘常念死候’视为人生最急事。”
徐光启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设想一下,在中国人对西洋人几乎无认知且自视中华文明高于一切文明的时代,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人归信了一个小众且与中国文化存在巨大冲突的教派,对于徐光启和传教士双方都意味着巨大的勇气和成功。

徐光启与利玛窦
像徐光启这样信天主教的学者官员在当时也有一定数量,最有名的还有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并称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四贤”,他们都是进士,也都为官,如杨廷筠曾任监察御史,正七品官,相当于现在副厅正处级的中纪委派往各地调查组成员。
此外,各地皈依天主教的皇亲宗室也有一些,不过,与入教的官员相比,王爷入教也不是高出一筹的大事,因为明末王爷数量实在是多,在地方上也没什么实权。
这些社会精英入天主教,多多少少都与死亡困惑有关,很多人的主要“痛点”就是死亡困惑,天主教解决了这个痛点,他们就信教了。当然,更多人的主要“痛点”不在死亡,可能是在某件事上受感召,但进教后,如何处理死亡也成为他们主要的“关注点”。
除了上层社会,死亡困难也是社会底层的痛点。年信记载了许多因天主教解决了死亡这个痛点而入教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种信仰的人。
据1637年年信,建阳有个70岁的老妇,年纪大了,希望寻得灵魂得救之道,花了大笔银子购置佛像、佛教书籍,仅一张和尚给她写的保证其死后进天国的纸,就100多两银子。她接触天主教后,逐渐认识到天主教之真,将佛像等送到教堂焚毁,领洗入教,“感谢天主使她免堕地狱,而送她去地狱的正是和尚的那张纸。”
陕西某个文人,自幼追求真理,先后信奉佛教、儒教、道教,无一令其满意。他对佛教的评价是“不真”,对儒教的不满意之处在于其只教人为善,不处理身后事,道教则不能使其内心平静。后来被任命为礼部官员,在礼部看见传教士用白石制作的日晷,上面刻着“泰西”等字,通过与传教士的交流,逐渐识得教义,领洗进教。
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都是聪明绝顶的人,许多是在欧洲已成名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中国人的死亡困惑这个痛点,针对性地制订传教策略,以吸引更多的信众。
传教士面对佛教、儒家这两个中国宗教市场中最大的竞争对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针对佛教,以批判其“毕达哥拉斯式的转世学说”为主。与佛教轮回式的再生不同,基督教观念中的生命之旅是直线的,“死”乃是从今生过渡到天国、从暂时过渡到永恒、从异土过渡到故乡的“生”——灵魂来自天主,必要归回到赐灵的天主。
针对儒家,传教士是十分客气的,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中国人不可撼动的价值观,就采取了“补儒”的策略,就是你没有的,我来给你补上。他们以灵魂论、末世说等天主教死亡观填儒家之空缺,践行其“补儒”的传教路线。
诸多宣教书籍中都有针对性地解答死亡问题,如《天主实义》主要在基督教神学框架和体系的梳理中介绍其不同于儒家的生死观念,利玛窦撰《畸人十篇》作为《天主实义》的续篇,根据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冯琦等围绕生命意义与归宿问题的对话写成,是一篇通过连续不断的对死亡的默想以应对生死的著作。此外,罗雅谷《死说》、《哀矜行诠》,阳玛诺《轻世金书》,陆安德《善生福终路》等著作都专论生死。
通过传教士的死亡教育,因信服天主教的死亡观而归信者很多,成为新教徒的一个重要来源。
尽管天主教始终未发展成中国社会中的主流宗教,但是在明末清初还是有相当存在感的,每年入教人数稳定在几千人,在1650年时,总人数已有15万之巨。
从传播学角度,我对这些传教士们是很服气的,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传播学大师。
下期,我将说说“善备死候之法”,即明末清初天主教徒们是怎样把准备死亡贯彻到日常生活中的。

徐光启墓碑前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2003年修墓时才竖起,此前,徐光启的教徒身份一直被遮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