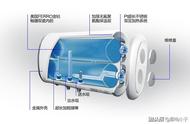文/王祥夫
研究俚语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至今不明白上海一带为什么把喜欢占女人便宜叫做“吃豆腐”,此话怎样由来,恐怕上海的朋友也说不清楚。虽然说不清楚,但我个人,至今还是喜欢吃用豆类做的豆腐。豆腐无疑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好吃、好消化,而且又极富营养。大病初愈,在饮食上这不行那不行,来块豆腐,想必连最有经验和最负责任的大夫都不会有意见。读丰子恺先生《缘缘堂随笔》,其中有一篇写他的冬日生活,说他坐在火炉子边上,在炉子上坐一个锅,把水烧开,在水里热一块豆腐,豆腐热好后蘸酱油食之,而且还给围在身边的儿女你夹一块我夹一块。丰子恺缘缘堂的日子过得真是朴素而滋味绵长,有老百姓“白菜豆腐”般的清平,豆腐是清平生活的必备之物。
我个人吃豆腐极喜欢吃豆腐的原味,比如香椿拌豆腐,这道菜之所以好是让你知道春天来了,再就是小葱拌豆腐,这两道菜无论出现在哪里,总是会受到普遍的欢迎。传统的酿豆腐我倒不太喜欢,这道菜式南北都有,做法大致差不多:豆腐切大块儿挖空,把肉馅儿塞到里边上笼蒸或者是下锅油煎。我不喜欢这道菜,是嫌其太捣腾,太捣腾的菜我都不太喜欢,比如那年在北京吃“红楼宴”其中的那一道茄鲞,一个小碟,小碟里一小撮儿菜,两口不够,一口又多,味道好不好?完全不得要领,不得要领能说好吗?小说是小说,小说里写得津津有味的东西吃起来未必就一定好。后来在扬州又吃了一次“红楼宴”,场面真是好,《红楼梦》中十二钗一一出场,陪我们坐那一桌的是宝钗,穿着古装,脸盘稍见丰肥,倒不离《红楼梦》的谱儿,但红楼宴的菜一道一道端上来,只其中那道茄子做的茄鲞,依然是不见茄子真面目。好不好?真还不敢赞一个好字。我以为,饮食之道,最最要紧的是要吃其原味,你把鱼做成了虾的味道,或把虾做成了鱼的味道,我认为都是无理取闹。豆腐就是豆腐,我们要吃的就是豆腐味!
读汪曾祺的散文,什么篇目记不清了,里边也说到豆腐,说某地的豆腐真是结实,你去买豆腐,好家伙,卖豆腐的可以把豆腐挂在秤钩上称给你!我没吃过这种豆腐,我以为豆腐还是要软嫩一些的好,大同的豆腐软硬居中,卖豆腐的一般都会把豆腐养在水里,大同人买豆腐只用一个字——“捞”。“干什么去?”“捞豆腐去。”可见这豆腐是放在水里!到河南,豆腐一般都放在屉子里,用湿布子苫着,要多大,当场给你用刀现划。豆腐中最嫩的应该是老豆腐,汉语真是不好解,往往给老外出难题,豆腐脑最嫩却偏偏叫它老豆腐!吃遍天下的豆腐,我以为日本豆腐最不好吃,嫩到像果冻,全部用塑料膜包装了,到饭店吃饭,谁点日本豆腐我反对谁!我还是喜欢吃我们中国豆腐,老浆和石膏点的都好,石膏点的有股子特殊味,大同这边的食客们好像是不太接受,但我反而喜欢。有句话是爱屋及乌,因为喜欢豆腐,我有时候突然会想到吃豆腐渣。豆腐渣可以到处要到,不必花钱,用一片圆白菜叶子托回来就是,做的时候猪油要多放,葱花儿也要多放,最好是猛火大炒,好吃不好吃,吃到嘴里粗粗拉拉却别有滋味。我母亲当年经常给我们炒这道菜,炒豆腐渣最好就着玉米面窝头吃。对我而言,炒豆腐渣就玉米面窝头,动辄让人起怀旧之情。
有一次吃饭,朋友们突然争论起来,争论先有豆腐还是先有豆腐干?这争论几近无聊,我向来不参加此种讨论。但豆腐*好吃是不用争的,我的道理是之所以说豆腐干好,是它可以佐茶,一边喝茶一边吃,所以南方才有茶干。你用一碟猪头肉佐茶可以不可以?在苏州吃豆腐*时候,我突然很想念我大同的豆腐干,在大同,最好的豆腐干好像非广灵豆腐干莫属,其结实耐嚼正好用来喝茶,而且没别的杂味,不像苏州茶干入口既甜且咸倒没了豆类的清香。广灵的豆腐干就好在满口豆香!其结实细致的程度也为其他豆腐干无法相比,一小条广灵豆腐干如碰到好刀工,可以切一百多丝。以其做扬州大煮干丝我想会更好,可以久煮,所以更能入味。
我现在所担心的一件事是,很怕韩国把豆腐的发明权也拿去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是他们祖宗的发明,韩国人好像根本就不怕别人说他们有错认祖宗之嫌。但韩国民间还好,我在韩国小酒馆坐在那里吃泡菜豆腐锅喝清酒,他们问我这泡菜豆腐锅好不好,泡菜好不好,我说好!你们的泡菜真好!可以说好到天下第一!他们马上就高兴起来,但我又对他们说,不过,你们的泡菜再好,这里边的主角儿豆腐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
其实,他们的泡菜也未必就好,说到好,四川泡菜更加丰富,口味也更加适合我,一碟四川泡菜我可以吃两碗米饭!
编辑:晓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