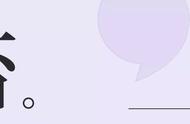《边缘人的流浪足迹》(22)回忆岁月过往,讲述故事人生。

1986年我的母亲抱着我儿子晗
我和芝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这种来之不易的“和睦”还是不经意间被打破了。
我的小妹妹去大姨家走亲戚,去了五六天。回家后,我对妹妹说:“你去了那么久也不回来,我都想你了。”
芝听到后,吃醋了。马上黑了脸,质问我:“我回娘家,不管过多久,从没听你说想过我,你妹妹离开几天,就想得不能过了?”
这都哪跟哪啊?
为此,我们又吵了一架,她回了娘家。此一回,收秋了她也没有回来。结合午季经验,我没有再去武店“请她”。中秋节,芝也没有回家。我知道,那是她娘家秋收、秋种还没有结束。
农历八月底,芝挺着大肚子回来了,其时,她娘家的秋庄稼收完了。再一个,按日子,她到了预产期。妻子*,当时也不会算日子,也不知道推算预产期,一切都在懵懂状态下随着时光流转,跟着日子前行。
娘看到芝笨拙的体态,每天都是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不要跟她发生冲突。千不说,万不说,人家在为我们老严家生儿育女呢?生下孩子,就是我们家的功臣。
我为了娘的叮嘱,忍着。
这期间,我做了许多的人生思考,尤其是到淮北走了一遭,那一遭走得如此糟糕,我不得不为自己何去何从做打算。
但是,身为一个农民,落榜回乡知青,路在脚下,前程在哪里?
没事的时候,我踏上村头去田野的乡间小路,蓝天白云,原野里碧绿的禾苗,我的眼里却没有一丝希望。
那时候,农村改革表现了巨大的成功,家家户户粮满仓,柴满垛,彻底摆脱了吃不饱的窘境。但是贫穷依然压在农民头上,像一座搬不动的大山。
城市改革的春风压根儿就吹不到我们这种偏僻落后的农村。大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一日千里,而我们家乡,微风拂面,波澜不惊。
思索再三,我认为自己的出路还是要靠写作。在八十年代时期,那条文学小路太过拥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说实话,后来从文学梦里清醒过来以后,发现走文学道路比走考学之路难上千倍万倍。
但当时,我信心倍增,痴心不改,认为只要努力,只要全力地付出,就一定会成功。
那段时间,小说,诗歌,散文,我什么题材都写,写出来就投稿。除了少部分习作被一些报刊发表出来,大多数投稿都石沉大海,或遭受退稿,或如泥牛入海。
接近临产的日子,芝哪里也不去,多数都是躺在床上,睡了吃,吃了睡。睡累了,就下床在屋里屋外走一走。嫁到我们家以后,芝很少帮着做家务,烧饭洗碗也不多见。而到了她娘家,田里、家里,所有的活计都推给她做,她做得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1985年10月30日,傍晚时分,芝对我说肚子疼。
我跑到后面的老屋告诉娘。娘说:“八成,芝要生了。”
娘来到我们房里看了芝,询问了一些疼的性状,幅度,就去我家东边找严素珍。严素珍是我们那一带有名的接生婆,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员,比我晚一辈,还要叫我叔。当时已经五十多岁,我出世就是她给接的生。在我们那里,方圆六七个村子,女人生孩子都找她接生。
不一会儿,严素珍挎一只画有“十”字的木质红漆小药箱来到我家。

她看了看床上的芝,问了一番,然后对我说:“叔,你出去一下。”
我出房间后,严素珍在我母亲陪同下,按了按芝的肚子,用手指敲了敲,又让她褪去裤子,按了按耻骨,操作一番后,对娘说:“老奶,婶婶还早呢。我回家吃过饭,晚上十点钟以后再过来。”
娘说:“你就在我家吃饭吧,安排你饭了。”
那一夜,芝肚子越来越疼,我坐在外屋,一夜没睡。严素珍跟我母亲在芝床边守着。
我睡不着觉,就在心里想:是男孩还是女孩呢?过去,我已经无数次给孩子取名字了,比如男孩叫“旭”,叫“昆”,女孩叫“嫣”,叫“苗”,也想到男女均可用的名字,比如叫“然”。
仲秋的夜,夜静如水,夜凉也如水,秋虫鸣叫都已经息了,芝的叫声一阵比一阵高。但是,严素珍依然说没到临盆的时辰。
半夜时分,娘回到后面老屋,煮了六只荷包蛋,端来给严素珍做宵夜。
村里的鸡叫了,偶尔伴随着外村的狗吠。
大概清晨四点多钟,经过了后半夜的折腾后,芝终于生了。严素珍和娘都喜悦地高喊:“是男孩,是个男孩。”
我跑进屋,严素珍在娘的配合下,正在给孩子擦身子,包裹。我看见,儿子长得很俊秀,就是鼻尖上有几个白色的点点。我当时想,以后这些白点下不下得去啊?如果下不去,儿子是不是会很丑。
结果,几天以后,儿子鼻头上的白色斑点就退尽了。
初为人父的心情激动万分,我有儿子了,从今以后,我就是父亲了。看着床上精疲力竭、满头虚汗的芝,她微微闭着眼睛,一副历经大难后的情景和安然。我心里对芝生出了浓浓的感激,也为平日里对她的仇视而感到歉疚。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她是我们家的功臣。
我难掩兴奋,来到外面。黎明正在到来,黑黢黢的东方天幕上,张开了一道亮光。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字:晗。
天将明,正是“晗”字之意。儿子出生在这个时辰,“就叫晗吧。”我脱口而出。

2006年时拍的我的老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