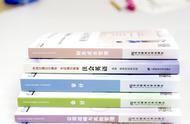加藤周一曾经在评述日本文学时精辟地指出“文学即思想”。《羊之歌》作为一部随笔作品,雅致的文字不仅体现出作者的教养学识,也凝聚了他对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思考结晶。用“文学即思想”来形容这部作品,算得上恰如其分。
**个人与时代的历史记忆
2019年,正值日本战后学者、评论家加藤周一百年诞辰。北京出版社适时推出了加藤周一的随笔集《羊之歌》(翁家慧译)。1919年为农历乙未年,加藤自述道:“以‘羊之歌’为题,一方面是因为我出生于羊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跟羊的温驯性格有不少相通之处。”
《羊之歌》是加藤周一的自传性随笔,1966年10月至1967年12月连载于《朝日期刊》。前篇从幼年记述到1945年日本战败,续篇则以战后为中心,讲述到1960年日美缔结新安保条约。对于加藤而言,1945年与1960年两个时间点意义十分重大。“1945年秋,我朝着战后的日本社会出发。”“1960年是对战后我在东京的生活得出结论的一年,同时,也是朝着以后的生活启程出发的一年。”夏目漱石在《三四郎》中借美弥子之口提出“迷羊”的概念。或许《羊之歌》便是一部“迷羊”的成长史,记录了一只离开了羊群,特立独行的羊,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前进方向。


加藤周一及其《羊之歌》
加藤周一曾将福泽谕吉与河上肇的自传誉为日本自传文学的双璧,原因在于两者均将个人的发展史与时代的发展史相重叠。《羊之歌》也是如此,它既是一部个人的小历史,又是一部跨越了大正、昭和两个时代、见微知著的大历史。
**感受体验与思想的成长史
加藤周一曾经说过,“文即人,人即思想与感觉”。《羊之歌》的前篇从《外祖父的家》开始,到《八月十五日》结束,记叙了加藤自童年至青年时期个人的成长经历、个人独特感受体验的形成、知识的储备与积累,以及二战期间思想趋近成熟的过程。开篇的《外祖父的家》让人联想起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中家庭生活的记忆。加藤的外祖父年轻时曾游学意大利,精通外语,过着西式的生活,喜欢西洋美食与意大利歌剧。童年时受外祖父影响而感受到的味觉、听觉,在加藤幼年的心中建立起独特的感官体验,让他在若干年后旅欧时感觉到“西欧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跋涉千里终于抵达的异域,而是悠长假期之后重新返回的故乡”。与外祖父家的“洋味儿”相映成趣的是,祖父家在农村,给加藤的童年记忆留下了“泥土的香味”,农村经常举办盛大的法事、婚礼,而加藤却感觉“在所有的宴会上,我认为自己永远是一个局外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渐渐从一个被动的观察者,主动成为一个观察者。这样的视觉经验也影响到加藤成年之后以冷静的目光认识西洋,并重新发现日本。
少年时代的加藤周一体弱多病,对于世人称作儿童游戏的东西,没有丝毫兴趣,而是“不求回报地、不带目的地、单纯地享受知识的乐趣”。加藤与早熟的同学无法成为知己,而听话的好学生一丝不苟的举止在加藤眼中显得滑稽透顶。读初中那年,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学校里“忠君爱国之类的东西倒是没少教,‘基本人权’之类的问题却从来不提”。回顾初中的时光,加藤直言没有一个老师在兴趣上、人格上,或者在世界观上对自己产生任何影响。
加藤的父亲是为人方正、淡泊名利的医生,家中二楼书房的书架上大多是德语的大部头医学书,文艺类书籍只有少量关于和歌的书,而且半数以上是《万叶集》的旧注释本。然而,作为“无奈之选的《万叶集》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想象世界的大门”。《万叶集》使加藤感受到一些具有音乐特性的东西,体验到诗歌类文艺作品的玄妙之处。而《万叶集》毕竟是古远的文学,无法解决现实生活对少年时代的加藤造成的困惑、沉闷、煎熬,直到遇见芥川龙之介的文学。芥川在20世纪20年代便犀利地揭示了日本近代国家的本质。其晚年作品《侏儒的话》中讽刺军人犹如小儿,对加藤启发良多。“不管是学校、家里,还是社会,一直以来所信奉的被神圣化的一切价值,竟不堪芥川龙之介的这一击,它们在我眼前瞬间坍塌。”1936年,加藤周一高中入学考试前夕,爆发了陆军将校兵变的二二六事件,加藤在现实中看清政治权力近乎荒谬的残酷,决心从此远离政治。次年,于战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的矢内原忠雄教授在演讲中洞察了日本即将踏上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作为一名听众,加藤被其自由精神深深感染。2004年,加藤周一与大江健三郎、小森阳一等作家、学者成立了维护和平宪法的“九条会”,反对“放弃战争条款”的修宪。这表明加藤的立场并非远离政治,而是拒绝独裁的坏政治,不与之同流合污。同时,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不惮于投身政治,维护和平的希望。
在东京驹场就读高中的三年里,加藤周一遇见了许多优秀的老师,如在夏目漱石名作《三四郎》中被称作“伟大的黑暗”的人物原型——哲学教授岩元祯、研究日本佛典的德国人斐措尔教授、用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论》德译本授课的片山敏彦教授……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加藤就读高中,还是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部,选修文学部的课程,在学习了三个月基础语法之后,教师便直接以外文原著作为教材授课。这一方式与现今通行的,偏重语言基础训练的外语教学不同,是通过文史哲外文原著的读解、翻译,综合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人文知识、思辨能力。这并非掌握语言的捷径,对于有志于学的学习者而言,却打通了语言与人文、思想的壁垒,是需要艰难攀爬却风光无限的历练。此外,当时尚未有“通识教育”的理念,但是从加藤周一的教育经历来看,大学提供了宽松的氛围、高质量的知识、思想传授体系,而他感兴趣的正是“包括了感觉和知识的世界整体,以及整体的结构”,因而能够打破学科的限制,成长为学识丰厚,极富洞见的学者。
加藤周一自述,大学期间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法文科副教授渡边一夫,他“生活在丑态百出的日本社会中,却从更广阔的世界和历史的角度来定位自身的存在”,渡边研究的16世纪是宗教战争的时代,而“这不仅是一个遥远国度的过去,它也是日本和日本所在的整个世界所面临的现在。”日后,渡边的学生中有一位也深受其影响,以文学反思人的存在本质,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学生便是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