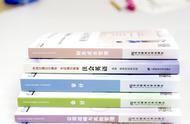永井荷风

丸山真男

夏目漱石
加藤在战争期间读完大学,留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当助手,没有上战场。而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去,不乏在战场上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其中就有加藤的友人中西。读高中时,中西便对时局抱有清醒的认识。加藤认为中西之所以战死,是因为“权力终于不能再骗到他,于是就用了物理上的力量,强行将他送往死地”。加藤在战争中活了下来,相对和平的生活环境给他提供了冷静反思的空间,并对未来抱以希望。《羊之歌》的前篇最后一章以《八月十五日》为题,文章的最后一句是“所以,希望还是有的。我们缺少的,就是粮食。不过,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
**认识西洋,发现日本
永井荷风是加藤周一偏爱的作家之一,相近的留洋经历或许是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在随笔《物与人及社会》中,加藤详细追述了永井荷风的经历与思想,认为1907年旅居法国里昂的一年对于荷风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具体而言在于“感觉教育”,即感受性的成熟。而对于加藤而言,旅欧的经历不仅使其感受性更加丰富,思想上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飞跃。
加藤自述经历了两次明显的转变,“一九四五年秋,我朝着战后的日本社会出发。一九五一年秋,我启程去看西洋。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出发”。在此之前,他与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合著的《一九四六——文学的考察》出版,为日本战后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气象。1951年秋加藤周一开始了三年多的旅欧经历,他深入理解之前在书本上接触到,而今亲身体验的欧洲文化思想。同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在与欧洲文化的比较中重新审视日本的文化及传统。
加藤周一旅居法国时,主要在巴黎大学的医学部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医院和研究室之外的世界无疑更吸引他。在《羊之歌》的续篇中,加藤主要记述了旅欧四年中所见之人、所读之书、游历之处。除了欧美人,他还结识了旅居欧洲的日本人,并对雕塑家高田博厚的观点——“所谓文化,就是‘形’,所谓‘形’,就是外化的精神;精神只有通过自身的外化,也只有通过这唯一的方法,才能实现自我”——产生了共鸣。当他游历各地,看见罗马的风景时,脑海中浮现出《古今集》之后的和歌中的景致;听到西洋音乐,不自觉地想起日本的义太夫,认为西洋的义太夫,就是法国人说的香颂;中世纪音乐则让他联想到从镰仓时代一直传承至今的横笛的旋律——加藤的这种体验并非思乡情切,而是有意识地在相似与差异中思考曾经熟悉却又变得陌生的日本文化,正如在出国之前他在《何谓日本文学》中提出的问题一样,何谓日本文化,成为一个清晰且有待解决的课题。
渡过英吉利海峡,踏上英国的土地之后,加藤惊讶地发现“以前我不曾察觉到的和英国有关联的种种习惯,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国度进口而来”。与法国青年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文学修养横向扩展,国际化却又肤浅;而对方的修养以本国历史为轴,纵向发展而且深厚。可以说,文化的差异诱发了加藤的思考。“多年以后,我写了《杂交种文化》,在文中强调了日本现状的表象之下潜在的各种可能性。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自己在大学城里的这段经历。”加藤周一的评论集原题《杂种文化》,出版于归国后翌年。中译本1991年出版,标题为《日本文化的杂种性》。此次《羊之歌》中译本为避免中文“杂种”一词的语用学贬义色彩,将其译为较为中性的“杂交种”。

《翻訳と日本の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