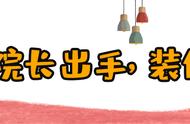傅聪
很多人把送礼看成一件投机取巧的事情,总是求人时,才想起来要送礼。送礼似乎变成了等价交换之事。
送礼不是目的,而是维护关系的方式之一。与其临时抱佛脚,不如用心经营,功夫做在平时。
比如,旅游度假时,顺手带些文创伴手礼;四时八节到了,准备一些时令鲜物等。用礼物传递情感和敬意,真正需要帮助时,一切就水到渠成。
02
送礼以“少”为贵傅雷曾经叮嘱傅聪:
西人送礼,尤其是艺术品,以少为贵。
从傅雷夫妇不断寄出去的礼品来看,他们最常选择的就是艺术品,尤其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工艺品、拓片、书画等。
这和傅聪身处欧洲音乐界的社交圈不无关系。吃穿用度方面的礼物,适合用来接济生活困顿者。而对艺术家来说,越是稀有的艺术品,越能体现送礼者的心意。
而傅雷本身就是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爱好中国传统文化,并且与黄宾虹等一批文艺名家私交甚好,自然珍藏了不少艺术品。这也为傅聪提供了他人无法企及的托举。

比如,1960年11月,寄“陈老莲《花鸟草虫册》一册,计十幅,黄宾虹墨笔山水册页五张(摄影),笺谱两套共二十张”。
其中的“陈老莲《花鸟草虫册》还是一九五八年印的,在现有木刻水印中技术最好,作品也选得最精;其中可挑六张,连同封套及打字说明,送弥拉的爸爸(傅聪岳父),表示我们的一些心意。”
傅雷同时在信中叮嘱:“因国内纸张奇紧,印数极少,得之不易,千万勿随便送人;只有真爱真懂艺术的人才可酌送一二(指笺谱)”。
这充分体现了傅雷曾经强调的“以少为贵”的原则。

傅聪在波兰
又比如,傅雷珍藏了一套《敦煌壁画选》,“三集俱全的一套,你要的话可寄你。不过那是绝版了,一九三五年的东西(木刻印数有限制,后来版子坏了,不能再印),更加名贵”。他在信中询问是否需要,如需要他可寄出去。后来傅聪与弥拉结婚时,傅雷将其作为新婚礼物赠予傅聪夫妇。
除此之外,傅雷还通过航空信等方式,寄了不少黄宾虹的画作。黄宾虹是我国中国近现代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齐白石合称“南黄北齐”。
他的作品曾参加比利时独立一百周年纪念国际博览会,获“珍品特别奖”,足见在欧洲文化界的影响。
傅雷与黄宾虹是平生知己,交谊颇厚。傅雷一生宣扬黄宾虹,也是黄宾虹艺术的重要推手。黄宾虹的作品,是傅雷寄给傅聪的礼物清单里最多的一种。
这当然得益于傅雷与黄宾虹的知己关系。对远在欧洲的傅聪而言,黄宾虹画作也是他在社交圈送礼的一个重要法宝,因其稀少且难得。
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选购礼物。除了不了解送礼对象的喜好外,对礼物的理解存在偏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送得贵,不如送得对。越投其所好,才越稀有珍贵。
03
选礼物要“未雨绸缪”很多人往往要送礼时,才开始筹划选什么礼物。
匆匆忙忙做得选择,往往很难凸显心意。
傅雷夫妇知道儿子傅聪孤身在外,精力有限,很难兼顾学习和社交。因此,他们总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各种适合作为礼物的物品。
比如,1954年12月4日,傅雷在信中告知,已寄出美术出版社印的黄宾虹册页,他选了三张并购买了三份,一份让傅聪自己留着欣赏,其余的嘱咐其分送给老师同学,作为圣诞与新年礼物。
一同寄出的还有十五年前故宫印的明信片,也预备他送人用。
1954年12月17日,傅聪在信中讲述了自己在五马路古董市场买的两幅敦煌壁画、在黄宾虹处买的十余幅清代小名家的精品等。
这些偶得的礼物,到了真正需要时,送给合适的人,往往能传达情谊,又显示了稀有和珍贵,让收到礼物的人十分喜悦。

傅雷手迹
市面上的名人家书刊行不绝,长销不衰的只有两种:《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自1981年北京三联书店初版发行以来,风行四十余年,销售千万余册。
目前市面上有两种版本。三联版,仅选傅雷一人书信的单向说教。2016年,译林出版社新版中,收录了全家往来书信。双向交流的父子对谈得以完整展现在公众视野中。
除了教育儿子如何待人接物、处理人情世故、维护社交友情等等,傅雷还对婚姻家庭、夫妇关系、亲子关系等,言传身教。
同时,还围绕音乐、文学、艺术、东方文化等与傅聪进行交流沟通。《傅雷家书》向我们完整展现了一个书香门第的教育之道。
正如金庸评价得那样:
傅雷先生的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