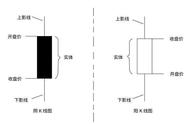我站在三号病栋锈蚀的铁门前,手电筒光束扫过门牌上暗红的污渍,腐肉与消毒水混合的气味从门缝渗出,黏稠地附着在鼻腔里,相机快门声在死寂中格外刺耳。取景框里走廊墙壁的霉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张,我后退半步后颈突然撞上潮湿的障碍物,那扇铁门不知何时已经闭合。
镜头突然剧烈闪烁,液晶屏显示的时间永远停在03:33,冷汗顺着脊梁滑进腰带。明明记得一楼有十二扇窗,此刻月光却从十三个窗口渗进来,最末端的窗户布满抓痕,内侧凝结着胶状物,像某种生物反复撞击留下的分泌物。

我的影子在墙上扭曲成佝偻的人形,耳畔响起细碎的啃噬声"啪嗒",一滴冰凉液体落在肩头,天花板的霉斑正在蠕动,墨绿色菌丝垂落下来,末端挂着浑浊的水珠,后退时踩碎的玻璃药瓶里1987年的生产标签正在褪色,而我的采访本上分明记录着本次调查发生在2023年。
逃生通道的门把手转不动了,整条走廊开始延伸,两侧病房门像闭合的牙齿般交错咬合,消防栓玻璃映出我身后有道灰影,戴着防毒面具的脑袋正以诡异角度后仰,狂奔时踢到的铁皮桶滚向黑暗深处,发出长达十秒的回响。

负一层的楼梯间消失了,墙面密密麻麻布满抓痕,指甲碎片嵌在混凝土里闪着微光,转角处的房间堆满腐烂的病号服,每件袖口都缝着"17床"的标签。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黏腻的水声,混合着生锈铁链拖过地面的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