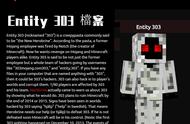去隆县拜年
冬天很快来到了。入冬以后,乌兰巴托的天气比之往年不算怎么冷,但对使馆的外交工作来讲,够得上一个真正的严冬。外交活动极少,使馆人员基本上是“蛰伏”越冬,并在“蛰伏”中迎来了1968年。
新年过后,为了试探蒙方的态度,照会蒙外交部:中国驻蒙古临时代办拟按惯例到蒙中友好合作社祝贺牧民节。原以为蒙方会借故阻挠,不料却很快获得答复,他们要中国使馆告知确切日期,以便通知蒙中友好合作社。
蒙中友好合作社坐落在乌兰巴托以西一百二十公里的隆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牧合作社。50年代,中蒙之间为了显示各界的友好关系,在彼此首都附近相互建立友好合作社。
蒙古的牧民节与中国的春节基本上是同一天,这是从中国农历新年演化而来。蒙语称这一天为“查干萨拉”(意为“白月”或“正月”),男女都要穿素色和白色绸缎衣服,以表示心地洁白善良。
1960年,蒙古政府将传统的“查干萨拉”定为农牧业合作化社员节,简称牧民节。每年在这天以前,中国使馆要派人前去祝节、赠礼,开始是大使或参赞去,后来改为使馆二秘以上外交官轮流前去。
离春节还有两天,我同小毛乘坐一部吉姆轿车前往。去隆县的路上,风雪交加,十分寒冷。好在我们乘坐的汽车暖气特别好。
公路基本上是来往车辆在草原上轧出来的,虽然不正规但行车平稳快速,相反个别低洼地段铺了石子垫高压实的硬路面,车走起来颠来颠去,不仅速度慢,人也不舒服。
风刮着碎雪,迎着车头一阵阵卷过来,车前窗玻璃上的雨刷只能刷出一个扇面形的雪洞。司机老周说,这种天气叫飞白毛雪,气温至少有零下30度,如果汽车在半路抛锚那就糟了,车要冻“死”(开不动)人要冻伤。
他说得我有些担心。小毛说不要紧,这部吉姆车较新,马力也大,不会抛锚,如果换了“伏尔加”和“华沙”就难说了;其次,这条路是乌兰巴托通西部省份的主要公路,来往车辆较多,必要时可以相互救援。
下午4时左右抵达隆县边境,农牧社的社长和*按照蒙古的古老传统,在与邻县交界的地方迎接我们,然后一起回到合作社住地。首先把我们安置在一个砖瓦房的招待所里,让我们喝热腾腾的奶茶,围着炉子取暖。这种炉子不烧煤而烧牛粪,蓝荧荧的火苗,暖和而没有什么气味。
晚上,在一个大型的蒙古包里,设全羊宴用马奶酒招待我们。一进蒙古包,迎面扑来浓烈的羊膻味,这比乌兰巴托蒙方一些单位的会客室里厉害得多。为了照顾我们不习惯席地而坐,蒙古包内设了T字形的长条桌,我和小毛在社长、*的陪同下,坐在桌子的横头,面前摆着一只制作好的全羊和其他食品,桌子的竖条两侧按惯例坐着特邀的老年人和生产能手,司机老周懂点蒙文,同他们坐在一起。
社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首先致词说,今年的牧民节同中国的春节恰好碰到同一天,这是个吉祥的日子,中国使馆的同志来与我们共同迎接这个日子,我们非常高兴。
接着他讲了一下农牧社一年来的成绩,还说了一些祝福的话。我简单讲了些友好祝福的话,就赠送礼品。礼品是一箱二锅头白酒,另加几瓶山西汾酒和陕西西凤酒,还有简装中华烟和茉莉花茶,以及杭州织锦风景画。这些礼品是他们十分喜欢的,尤其是白酒。蒙古人爱酒,度数越高越好,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苏联的伏特加度数也不够。
近两年中蒙贸易量下降,蒙古进口中国的酒较少,根本分配不到县以下。赠礼后,社长让主宾切全羊。小毛告诉我怎么切法,我就拿起刀在羊臀部片了一小块肉放到嘴里,然后把刀交给社长转与一老年人。这位老人一会儿就把全羊分解成小块,盛在碗里送与在座的每个人。招待所的女服务员把一碗碗马奶酒端到每人面前。马奶酒我过去听说过,但从没喝过,一口下去觉得味道香醇,度数不高,就接连喝了几口,没想到马上冲上脑袋,弄得晕晕乎乎。
小毛怕我喝醉,就向服务员要来一杯酸马奶让我喝。社长问我加糖还是加盐,解释说蒙古中西部喝马奶是加糖,东部喝马奶要加盐。我回答当然是加糖,为了同他们取得一致。大家喝着吃着,社里年事最高的老人唱起民歌——长调,旁边有人拉起马头琴,歌声高亢悠扬,配以忽高忽低琴声的呜咽,令人有游荡在大草原上的感觉。
长调是蒙古民间歌唱形式,多在喜庆日子演唱,歌词有的是传统继承,有的是老练歌手即景生情按调自编,之所以叫长调,不仅歌唱时间长,而且每句调之后要拖长腔,就像我国京剧末字要哼半天。欢乐气氛一直持续到夜深,蒙古包里暖洋洋的,人们忘记了外面刮的白毛雪。
回到招待所,只有司机老周不肯脱衣就寝,坐在那里默默地抽烟。我问他怎么不睡,他告诉我,招待所没有车库,我们的车只能放在露天,这种天气晚上每半小时就得把车发动一次,要不即使水箱冷冻液经得住,传动轴里的机油也会冻实。
他白天雪中行车够辛苦,晚上又尽职尽责地守夜,这样的老师傅实在令人感动。我乘车颠簸疲劳,加上喝了马奶酒,很快就入睡了,只是司机开门出去一阵冷风吹进来时,偶尔醒一下。
第二天雪霁天晴,告别农牧社的领导,踏上归途。雪下得不厚,但迎面反射的阳光十分刺眼。我说这雪下得太薄不顶用吧,小毛解释说这雪正好,下得深了把草全盖住,牲畜冬天就没吃的了;农牧社本身也矛盾,种地希望雪越厚越好,放牧则希望下雪次数多但量不要大。
司机老周问我对蒙古包里的膻味习惯吗,我告诉他来蒙古以前有思想准备,有人告诫过我,能闻膻味、能吃带血羊肉是过两关,否则在蒙古没法呆。
我小时候吃了牛羊肉就呕吐,战争期间下乡搞土改,住在一个复员军人家里,那时由于粮食饲料困难,家家户户养羊而不养猪,这位复员军人经常宰羊做羊肉汤下饭,我从开始强咽到慢慢习惯,最后离去时已喜欢上羊肉了。
小毛说要是不能吃羊肉,到蒙古来就惨了。过去使馆有位参赞,出席蒙方宴会只能吃点面包、酸黄瓜什么的,闻到浓重的羊膻味就恶心呕吐,农牧社这样的地方他根本不敢来。
讲到羊膻味,老周补充说,使馆食堂所需鸡蛋,有时蒙古外交商店供应不上,我们就到华侨家收购。华侨家的鸡蛋又大又红,据说是拣蒙古餐馆扔掉的羊内脏切碎喂鸡,鸡吃了这种饲料,冬天照样下蛋,而且零下二三十度也不进窝。
我说,无怪食堂的炒鸡蛋一股羊膻味,说得他们两人都笑起来。我问他们:为什么外交商店供应的鸡蛋个个都编号码?小毛说蒙古人不会养鸡,外交商店的鸡蛋是“中国援建的养鸡厂生产的,数量极其有限,怕工人偷吃就编了号。
我问小毛,蒙中友好社对我们的招待比之往年怎么样?小毛说没有什么变化,还像过去一样那么热情友好。我问,为什么中蒙关系恶化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小毛说,蒙古普通百姓都认为中国是真正的朋友,他们政府说的那一套,老百姓不相信。
从隆县回来的第二天,就是农历除夕,当晚在使馆礼堂举行了春节晚会,除了使馆的二十多人,还邀请了中建驻蒙古公司的留守人员和友谊医院的医护人员,上百人济济一堂。
晚会上,大家同唱革命歌曲,医院的姑娘们演出各种节目,最后敲锣鼓、扭秧歌,一直闹腾到半夜,听到收音机传来北京大钟寺的钟声才散会。欢乐情绪是有感染性的,大家忘记了背井离乡身在异域,也忘记了冷若冰霜的中蒙两国关系。
意外的一次旅行
驻蒙古使馆在“蛰伏越冬”的状态中,迎来了1968年的春天。
由于去冬少雪,气候分外干燥,蒙古辽阔的草原上露出了旱象,牧民们担心接羔以后牲畜草不够吃,希望苏联老大哥能支援一些草料。然而,苏联除了继续运兵入蒙,就是送来一场森林大火。
火是从苏联境内后贝加尔地区的山林中燃起的,随后沿着蒙古色楞格省东部以及中央省与肯特省交界的山岭,由东北向西南,断断续续一直烧到离乌兰巴托几十公里处。有时刮东北风,烟火味竟然飘进乌市来。蒙古既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没有什么技术装备来扑灭林火,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好几百年成长起来的松林烧成灰烬。好在蒙古的森林面积占其领土的15%,人均木材蓄积量约为六百立方米,烧掉一些森林,看来蒙古政府也不那么心痛。
这场森林大火送走了乌兰巴托短暂的春天。接着,是干旱而炎热的夏天。说是炎热只是与往年比较而言。在乌兰巴托,7月份平均气温18℃,最热的8月初也很少超过25℃,夜里通常在20℃以下,睡觉还需要盖薄被子。即使如此,蒙古人也还是怕热。

土拉河边有一所古建筑——夏宫,是本世纪初喇嘛皇帝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夏天避暑的地方。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当前的党和政府的高级*,在土拉河南岸、博格多汗山麓盖有豪华的别墅,他们在那里度夏。
中层干部在土拉河南岸的河滩上盖有自己的小木屋,作为全家避暑之用。一般干部和城市居民则利用夏季休假,全家到有山泉的树林边坡地上架起蒙古包,有滋有味地度过“炎夏”。
我国援蒙的建筑工人说,蒙古人很会享受。

开春以后,随着天气转暖,驻蒙古各国使团间的外交活动也逐渐多起来。开展与各国驻蒙古使馆的来往,这多少缓解了我们在中蒙外交中“坐冷板凳”的苦恼。
朝鲜使馆,由于中朝之间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加以两国军队和人民在抗美战争中,彼此的鲜血流在一起,友谊更加深厚,因而他们在蒙古,并不顾忌苏蒙当局对中国的态度如何,而主动加强与中国使馆的来往。
朝鲜驻蒙古大使原是中国东北延边地区人。其祖辈是在日本吞并朝鲜国土后,移居到延边来的,他从小在中国东北长大。
日本投降后,他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1950年秋,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他返回祖国,参加了朝鲜人民军。由于作战勇敢,逐级提升,停战后转到外交系统工作。
这位大使的经历,使得朝鲜驻蒙古使馆同中国使馆之间的亲密关系更加深了一层。两个使馆间几乎每一至两个月要互相宴请一次,或者举行联欢。席间畅饮中国茅台和朝鲜人参酒之后,大家引吭高歌《金日成将军之歌》和《东方红》,情绪非常热烈。宴后,双方往往要表演节目助兴,朝鲜大使的“卖糖葫芦”表演,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他用长柄扫把充当小贩的插满糖葫芦的稻草把子,扛在肩上一面走一面用东北腔调吆喝着,真是惟妙惟肖。
夏天到来,两家使馆则到土拉河上游幽静山谷的树林中举行联欢野餐,并邀请经常为朝鲜使馆送医送药的中国驻蒙古友谊医院的全体人员参加。大家又说又唱又表演节目,热热闹闹,轻松愉快地度过一天。
我们与朝鲜使馆互赠食品,也是加深友谊的措施之一。在蒙古几乎见不到绿色的蔬菜,尤其是冬春两季,外交商店里只有土豆和干巴巴的圆白菜。而中国使馆有国内运来的大白菜,自己厨师做的豆腐,还有驻蒙古公司几个工地室内种的西红柿和黄瓜。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朝鲜使馆,他们非常高兴,大使夫人用中国大白菜做成原汁原味的朝鲜泡菜回赠我们。

蒙古的冬天晴朗无云,日照条件特好,随意在花盆里栽上一棵西红柿或黄瓜,培上一点羊粪,放在向阳的窗台上,就能长出累累的果实。驻蒙古公司留守职工用大木盆扩大栽种,自吃有余,就给使馆送一些来,成了使馆开展友好外交的礼品。
越南驻蒙古使馆,大使之下包括司机在内只有四个馆员,也同中国使馆一样不带配偶。我们是由于“文革”的限制,而他们则是由于抗美战争经费困难。
大使曾率全馆人员到野外挖野菜,补充伙食,这很令人感动。我们也像国内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战争一样,在物质生活上帮助越南使馆,常送去各种副食和蔬菜,其中豆腐至少每两周送一次。而越南使馆有时也回赠他们自己做的炸春卷,用糯米粥表皮卷炸而成,又薄又脆又香。
越南驻蒙古大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汉文底子深厚,他可以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可以写中国古体诗,但却不知这些中国字怎么念。他下中国象棋水平较高,但越南的下法“象”是可以飞过河的。两个使馆间相互宴请,倾谈友谊,但在涉及苏联和蒙古的话题上,他们尽量回避,极力保持“中立”。
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驻蒙古大使,都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其中尤以罗马尼亚大使比较突出。这位大使进入外交界以前是一名医生,他看过俄文版的《*语录》,对*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话非常称赞。在蒙古对华关系上,他有时能及时告诉我们一些内幕消息。
波兰大使在同我们的交往中,多次提到1956年波兰与苏联矛盾激化,苏联准备出兵镇压,中共中央派*前去调解,使波兰避免了一次刀兵之灾。
波兰使馆的一秘,直爽、健谈,与我的一场关于汽车的争论,使我经久难忘。他认为中国早晚要发展私人汽车,我说不会,他说肯定会。我说我们*总理说过,要发展公共交通,不搞私人汽车。他说你们总理讲了也没用,到一定时候就会有私人汽车。这话对我有些刺伤,同他一直争得面红耳赤。若干年后,我只能检讨自己认识上的局限性。
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同中国使馆的关系比较冷淡。1968年出现“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实行一些改革,受到全国人民欢迎),该馆外交官同我们接触较主动,尤其是与刘振鲁在蒙古国立大学同过学的捷馆三秘,常来谈谈其国内情况和对苏联控制的不满。
1968年8月,苏联突然出兵布拉格,进行武力镇压,并迅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博达和党的第一*杜布切克,被裹挟到苏联“谈判”。斯沃博达总统的名字,意译为“自由”,在苏军占领之下,他和全国人民都失去了自由。
此时,捷驻蒙古使馆陷于一片混乱,捷馆三秘怕蒙古特务监视,只能夜晚偷偷来中国使馆,讲他们国内人民反抗占领的情况,以及他们大使如何摇身一变,由支持“布拉格之春”,变为忠于苏联的“国际主义斗士”,大整馆内的“反苏分子”。不久,这位三秘被调回国内。
中国使馆同东欧国家使馆的来往,本来可以放开一些,但由于顾及馆内的不同意见,有时不得不缩手缩脚。例如,匈牙利大使夫妇对中国相当友好,只是话不能说得明白。他曾设盛宴招待过我们的几个主要外交官,在他离职回国前我要宴请他,请示国内未获同意。他乘中蒙苏国际联运列车离开乌兰巴托,我到火车站送行,本来想送他一瓶他特别喜欢的茅台酒,也因馆内有人反对而作罢。在车站,只好向列车长嘱咐,途中好好照顾这两位老人。
就在春末夏初的时候,驻乌兰巴托的外交使团中,出现一位怪人——法国新任驻蒙古大使。法国在同中国建交后不久就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租住乌兰巴托饭店的房间,建立了法国使馆。其前任大使只在每年夏天蒙古国庆节前后,临时来乌兰巴托住个把月,然后退掉房间返回法国。
法国新大使贝卢希,个子高高的,瘦得干巴巴,满头白发,背有点驼,他说自己五十岁出头,但看上去有六十多。他能讲法国口音的俄语,还能讲一些中国话。他说起话来非常谦和,不像苏联和东欧某些国家的大使那么架子十足。他到任不久就主动来拜会我,交谈中间跷起二郎腿,不断地喝着青岛啤酒,说他多么喜欢中国。
一个星期以后,我去乌兰巴托饭店回拜他。他对蒙古外交部发起牢*来。说他一到任就申请租一幢楼房正式建立使馆,过去一个多月了,一点回音没有。他指着阳台上斜插着的法国国旗说:“你看,我们的国旗能老是这么挂着吗?”他还说,他的从巴黎寄来的邮件,经常被拆开检查,他对蒙方破坏外交惯例随意检查外交邮件,向蒙古外交部提出指责,讽刺地说:“你们检查以后,能否给封好一点,免得里面的东西掉出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驻蒙古外交使团举行酒会,欢迎新任法国大使。酒会在匈牙利使馆举行,匈牙利大使那个矮矮胖胖的嗜茅台酒如命的和气老者,是本年度使团活动的轮值主席。使团活动用的是俄语,匈牙利大使自己能够对付,我就趁便与他的翻译、那个蒙文很棒的三秘交谈起来。
他告诉我,他的蒙文是在布达佩斯大学东语系学的,那个系不仅教学国际现用的东方语文,为了研究东方文化,甚至还保留了满文。这使我十分意外,因为中国的北京大学满文教学早已停课。我问他,匈牙利为什么对东方语文这么重视?他笑着说,难道您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从东方来的吗?我当然知道远在两千年以前,匈奴族从亚洲北部西徙到黑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建立了东欧最古老的国家。
席间,罗马尼亚大使悄悄告诉我,法国大使是个“怪人”,朝鲜战争时,他在汉城,曾被朝鲜俘虏,在俘虏营里住过一段时间,越南战争爆发时他在西贡,今春“捷克事件”他在布拉格,现在,又来到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凉爽的夏天很快过去了,法国大使不再提租楼房建使馆的事,据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讲,这位大使嫌花钱太多,放弃了申请。冬天来临之前他回国了。我注意到这位大使同他的前任一样来去,只不过在乌兰巴托停留的时间从个把月延长到半年多。
后来,我进一步弄清他来去的特点:离蒙古时乘火车经北京飞巴黎,来蒙古时飞莫斯科乘火车到乌兰巴托;有的年份则相反,走时北线,来时南线。据小联运列车员讲,他来去北京一乌兰巴托之间,总是愿意乘小联运,在车厢里摆着一箱青岛啤酒,一面喝一面观景,看到苏军在建的军事基地和机场,就端起小型电影摄影机拍个不停。
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乌兰巴托新增了一家外国使馆——古巴驻蒙古大使馆。大使还未到任,先派一名二秘担任临时代办,办理建馆事宜。我主动先去拜会,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交谈中,他盛赞古中友谊,感谢中国对古巴的全面支持并向我详细介绍了猪仔湾事件(古巴军民打败登陆进犯的美国雇佣军)。
他让我吸古巴雪茄烟,我这个从不抽烟的人,出于好奇尝新,猛抽了半支,结果告别时晕晕乎乎地离开了古巴使馆。我不禁想起,外交部信使老刘曾告诉过我,抽古巴雪茄烟能抽醉。
突然的旅行安排
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个年头。外交战线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1967至1968年一年多时间里,与我国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有近三十个国家同我国发生外交纠纷。其中有不少是中国方面处理不当引起的。这就使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外事工作陷于困境。
对于这些极“左”错误,周总理和广大外事干部一直表示反对,并努力设法制止。*多次提出批评,要求纠正。经过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外事工作一度出现的混乱较快地得到纠正,一些不正常状态逐步消除。不久,中国就开始派出一批为参加“文革”而统统调回的驻外使节,对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双方关系的事件,主动进行修复工作。
在驻蒙古使馆,我担任临时代办半年多来,日夜提心吊胆怕出问题的紧张心情,开始得到了一些缓解。使馆主要领导成员开会,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对外工作,感到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错误:一是在对外宣传方面,没有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曾经发生不区分对象,广为散发《*语录》,实际上是强加于人的情况;另一是对待华侨敞开使馆门户,进进出出,还不时举行时事报告会,宣传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很好强调遵守驻在国的法律法令,以致引发了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小事故。
这两方面的错误,给对外关系,尤其华侨工作造成一定损失,只是由于蒙古当局追随苏联激烈反华,客观上掩盖了我们某些过火行动的后果。
在使馆内部,因为受国内“文革”的影响,经常意见不一,“惟我独革”大有人在。使馆的一位机要员,回国参加“文革”时,是使馆“战斗队”的小头头。他返馆后,工作上出差错,我批评了几句,他就寻机报复。
苏联出兵捷克后,9月初,驻蒙古使团要向乌市苏军烈士塔献花圈,约定先在匈牙利大使(使团长)馆集合,给我发来请帖。
参加不参加?请示国内,建议如国内同意,可不必复电。当天上午,国内来电指示不参加,但这位机要员要弄“边缘政策”,要待我迈出使馆楼门时通知我。而我因别事提前离馆,使馆办公室的同志不得不派车急奔,从匈牙利使馆门前把我找回。所乘汽车掉头时,正好罗马尼亚大使乘车迎面而来,他探身车窗外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感到十分尴尬,只好磕磕巴巴敷衍了几句,就急驰回馆。
这类事情在馆内时有发生,由于我们使馆主要领导坚持“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外事务大小都向国内请示报告;对内工作致力于巩固队伍,领导以身作则,加强团结,加强外交纪律;因而,二百多天的日子,算是安全度过。
我国政府在外交工作上的一些做法,特别是修复因中方原因而损害的某些国家关系,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蒙古当局继续追随苏联发表一些反华文章的同时,其外事人员在同中国使馆的日常交往中,显示出若干想改善关系的愿望和姿态。
1968年6月,中蒙之间年度贸易谈判在乌兰巴托举行。中国对外贸易部派来官员,我问他们双方的贸易额怎么样,他们告诉我:“1967年只有61万卢布(270.8万图格里克),降到空前的最低点,而1960年曾经高达3129万卢布(1.3亿图格里克),是1967年的五十倍。今年也不乐观,你看,半年都快过去了,才开始谈判。”
贸易谈判结束,双方的协定由我和蒙古外贸部一位女副部长签字。在交谈中,她说今年两国贸易额只保持了去年水平,实在太低了,过去乌兰巴托的百货商店里,到处都是中国的商品。
我说要增加贸易额必须双方共同努力。她摇了摇头,不再说什么。
1967年以来,中蒙之间的文化、体育、科技交流全部中断,只剩下外贸“半死不活”的一条细线。各自驻对方使馆的开支,按例由各自的外贸收入中冲销,现在区区的贸易额,几乎不够使馆的日常维持费。蒙方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不能不对中蒙关系的恶化感到切肤之痛。
7月,正当“炎夏”开始的时候,使馆突然接到蒙古外交部的通知,准备安排中国使馆临时代办到外地旅行。这对我来讲,当然是求之不得,比我早来使馆的外交官,都去过蒙古的不少省份,而我只在来蒙古的列车上瞥见过大片戈壁滩。
不过,为什么在中蒙关系恶化再恶化之后,蒙方要安排这次外地旅行?分析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想以主动安排,换取其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到外地旅行,观察中国的“文革”形势;二是看到苏军入蒙古之后,中苏关系会更加紧张,一旦爆发战争,蒙古必然沦为战场,想以不惹苏联注意的小动作,来缓和一下中蒙关系。
我尽快把蒙方的通知和对其意图的分析报告国内。国内同意让我接受去外地旅行的安排。
办公室的小刘去蒙古外交部礼宾司谈旅行的具体安排。我本想向南走,以到前杭爱省疗养胜地哈尔和林,参观成吉思汗行宫古迹为借口,绕行南部三个戈壁省份,沿铁路回到乌兰巴托。
小刘回来说,蒙古礼宾司副司长图门说,天气热,戈壁省份温度高,不适宜旅行;准备让临时代办到北部的布尔干省和库苏古尔省去,那里树多水多,风景好,气候宜人。我说,她讲得那么体贴关照,使人不好讨价还价。其实是怕我们去追索苏军的足迹,否则为什么不安排去色楞格省?那里的自然风景是全蒙古的精华,而大批苏联人也住在那个省里。当然,既然国内已同意成行,客随主便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