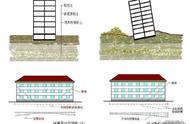鲁迅先生的《铸剑》,描述了一位名叫眉间尺的铸剑师后裔,为父报仇的故事。

其实,这篇小说并非鲁迅先生的“原创”,而是一个传统故事的新编。这个故事最早出自汉朝刘向编撰的《列士传》和《孝子传》,而流传范围最广的则是甘宝所著《搜神记》中的版本。所不同的是,在《列士传》和《孝子传》是以《干将莫邪》为题目,而《搜神记》则是以《三王墓》为题。而且,三部作品中的主人翁都是铸剑师干将和莫邪的儿子,所不同的是主人公的名字分别是赤鼻和赤。而鲁迅先生,因为赤的长相是“眉间广尺”,所以将他命名为眉间尺。
不论故事的名字叫《干将莫邪》也好,叫《铸剑》也罢,主人翁的名字是赤鼻亦或者眉间尺,其实都不重要。这几部作品,都是在宣扬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毕竟,年仅16岁的眉间尺,为了给父亲报仇,就敢背着一把宝剑独闯强大的楚国。最终,为了能够成功刺*楚王,选择信任“黑色人”,将自己的人头和宝剑交给他,并由他完成了对楚王的致命一击。但是,如果认真阅读《铸剑》和《干将莫邪》,你会发现鲁迅先生的文章与先前的文章有着莫大的不同。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铸剑》中,对于“黑色人”得着墨比《干将莫邪》要多。而这为在另外三部作品中只是被称之为“客”的“黑色人”,与其说是一位游侠,到不如说是一位“刺客”。而正是对这位刺客的描写,能够让我们从这篇“披着侠义外壳”的小说中,读出鲁迅先生内心那丝不易察觉的无奈与彷徨。
所谓刺客,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怀挟武器进行暗*的人”。而且,与行侠仗义的侠客相比,刺客是“为获得报酬而*人”。但是,在司马迁看来,刺客尤其是先秦的刺客,不仅属于游侠,而且他们都是随时可以为了知遇之恩而抛弃自己生命的人。所以,与后世为了蝇头小利而*人的刺客不同,先秦的刺客怀揣着侠义精神,而且他们的行动更有他们的理想和抱负隐藏在其中。

所以,司马迁在其所著的《史记》中,不仅专门为刺客列传,而且对描述的五位刺客,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在司马迁看来,这五位刺客,或者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比如曹沫、专诸、聂政;或者功败垂成,比如豫让、荆轲。但是,无论成功与否,他们都展示了侠客的勇气,检验了侠客的信义,更对当时的局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同样,在《铸剑》中的“黑色人”也没有愧对先秦刺客的身份。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眉间尺的托付,也证明了刺客的“勇敢”、和“信义”。
这里所说的“勇”,并不是说“黑色人”敢于拿着宝剑去找楚王拼命。因为,这种敢于“血溅五步”的决绝不过是“匹夫之勇”。因为楚王不仅残暴,而且生性多疑,所以仅凭借一份“血勇”之心,不仅会搭上自己的性命,更无法完成眉间尺的重托。所以,黑衣人在面对楚王时,要隐藏自己的“*气”,更要想办法排除楚王对自己的疑虑。当“黑色人”顺利完成自己的计划,砍下楚王的头颅之后,他发现眉间尺无法控制住楚王,所以义无反顾地砍下了自己人头,在沸腾的“鼎”中,与眉间尺相互协助,终于彻底将楚王置于死地。然后,“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向天,沉到水底里去了”。所以,“黑色人”的勇,是蕴藏着大智慧的“勇”!
当然,“黑色人”不仅证明了刺客的“勇”,更将“信义”二字展现得淋漓尽致。要知道,“黑色人”并非名满天下的豪侠,所以不必为所谓的盛名所累。面对戒备森严的楚国王宫,黑色人没有必要为了仅有一面之缘的眉间尺,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何况黑色人,看上去不过是一个“黑瘦的,乞丐似的男子”,生活明显常拮据。当时他已经得到了眉间尺的人头和宝剑,完全可以拿着这些去向楚王换取高官厚禄。但是,黑色人因为“信义”,拒绝了所有的诱惑,也排除了各种恐惧,完成了对楚王的致命一击。

“黑色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眉间尺的托付,也证明了刺客的“勇敢”、和“信义”。但是,与先秦时代刺客可以改变朝局或影响局势发展相比,“黑色人”和眉间尺的牺牲,对当时暮气沉沉的楚国没有造成任何实质上的触动,甚至连一点涟漪都未曾泛起。也正因如此,才会有了《铸剑》的第四部分。而也是这一部分,或许才是鲁迅先生内心真正的写照——无奈与彷徨。
在《铸剑》的第四部分中,王后,王妃,武士,老臣,侏儒,太监等人粉墨登场。当楚王、黑色人和眉间尺三人的头颅都落入沸腾的金鼎之后,他们争先恐后地拥了上去,然后只是进行观望,而“挤在后面的(人),只能从人脖子的空隙间向里面窥探”。这种状态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直到“第六个妃子忽然发狂似的哭嚷起来”,人们似乎才意识到“大王的头还在里面哪”。而且足足等了“煮熟三锅小米的工夫”,才想起到大厨房拿笊篱去捞楚王的人头。
楚王的头颅虽然捞起来了,但是已经与眉间尺和黑色人的头颅混淆在要一起,根本无法分开。所以,楚国上下决定,只能将三颗头颅一起埋葬。而当藏着“藏着三个头和一个身体”[6]的灵车行进在楚国都城之时,到处都是看热闹的百姓,其中除了“几个义民很忠愤”之外,大多数人关注的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甚至连“装着哀戚的颜色”的“大臣,大监,侏儒等辈”都不屑一顾。因为,在百姓看来死一个国王对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同样,对于王后也好,王妃也罢,还有其他达官显贵,依然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铸剑》中描述的楚国,与鲁迅先生所处时代的中国是何等相似。要知道,这篇小说写于1926年,发表于1927年4、5月(《莽原》杂志第八期和第九期)。当时的中国,虽然经历了武昌起义的洗礼,也推翻了腐朽的清廷。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以北洋军阀为首的武人集团所窃取。曾经抛出了各种救国的理念,比如实业救国,比如教育救国……但是,这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理念,很快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被无情地摧毁了。于是,民族资产阶级选择了向着两股势力屈服,虽然没有同流合污,但是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激情澎湃。
民族资产阶级的屈服,直接摧垮了那些激情澎湃的文人。他们曾经为革命欢呼鼓噪,期盼能够实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抱负。结果,现实就像一盆凉水,无情地扑灭了文人们心中的火焰。那些在辛亥革命中,一直没有被唤醒的民众,甚至比之前清廷统治时期更为麻木不仁。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的压迫,更要面对战火的荼毒。

而这一切,都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所谓的武人集团造成的。这些穿着军装,操持着枪炮的军阀,早已将先秦游侠的侠义风骨抛到了九霄云外。且不说,他们是否胸怀国家民族这样的大义”,就是武人本应拥有的“勇武”和“诚信”都已经荡然无存。
当时的中国多灾多难,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列强环司伺。如果真正的武人,当登高一呼,内平定割据之军阀,外对抗侵扰之列强。为民众争取安定的生活环境,让国家和民族能够拥有独立之姿态。但是,当时的军阀,除了在军阀混战中争雄之外,面对列强只有奴颜婢膝。尤其是1926年之时,为了安抚列强,军阀甚至不惜将枪口瞄向了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出离愤怒的鲁迅先生,除了将自己的笔化为匕首和投枪,写出《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似乎也无能为力。
毕竟,当时的军阀集团不仅丧失了武人的“勇气”,更缺乏做人应有的“诚信”。从1916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分裂之后,中国民众看得最多的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且,不同派系的军阀之间,都是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又会因为分赃不均而反目成仇。所以,当时军阀之间的混战司空见惯,而且不是奉系和直系联合起来打皖系,就是奉系和皖系合起伙来对付直系。相互之间的盟约也好,协议也罢,不过是无人遵守的废纸。“信义”二字,已经从他们的身上被彻底告别了。

民众的麻木不仁,让曾经追求“精英治国”理念的中国文人,理想已经趋向幻灭。而武人集团的彻底沦丧,则成为压垮他们内心理念的最后一根稻草。毕竟,他们曾经对于还称之为“新军”的武人集团满怀期待,将他们视为革命的主力。可是短短10余年之后,中国的武人集团就已经彻底蜕变,不仅没有了应有的“侠义精神”,更是连武人的基本道德都被抛弃。
所以,中国文人在对武人集团失望之余,其内心更是充满无限的彷徨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