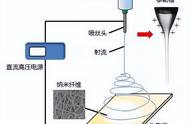我从看台上站起来,和小说家握了手,走下了看台。那群乌鸦落在烟囱上面,站在烟囱的沿上,把那沿都站满了。它们怎么知道烟囱不冒烟了呢?它们在看着谁呢?
我向着自己的方向一直走过去,不管烟囱上的乌鸦是不是在看我。
这是双雪涛在小说版《刺*小说家》中写下的话。
在原著中,刺客(即“我”)是用异常平静的方式,与小说家分的手。他不像电影版中的关宁(雷佳音饰),有掷物必中的“超能力”,而小说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也远没有电影中那么夸张。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篇3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是《干将与莫邪》的仿写,体现了后现代人的迷惘与困惑。从文本看,原著带有鲜明的后现代风格,几乎无法用影视语言呈现。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版《刺*小说家》会让人感到如此惊艳、如此震惊。不论它与原著的主题偏离有多远,仍可称是中国奇幻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这个复仇的故事,中国人讲了两千多年
《干将与莫邪》的故事最早出自出汉朝刘向的《列士传》和《孝子传》,后经晋人干宝改写,收入《搜神记》。此后该故事传承不衰,当代文学中最著名的改写本,应是鲁迅先生的《铸剑》。
故事传承的背后,隐藏着民族精神的变迁史。
在刘向眼中,这是一个关于孝的故事,而孝是世间基本大法,只有通过行孝,个体才拥有了生存的合法性。刘向对复仇者赤的刻画极简,因其性格如何,对结局无直接影响。
在干宝笔下,复仇者赤的形象突然变得生动起来,特别是加入刺客“已然诺”的慷慨,以及赤的身后哀荣,体现出晋人对个人意志、自我成长的关注。
到鲁迅时,赤(改名为眉间尺)更接近现代人,拥有独立人格,他的性格、勇气、自我牺牲等,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鲁迅试图呈现出被长期遮蔽的民族精神——血性、尚勇、豪迈、信任……以为时代寻找解药。
可这一切,到双雪涛手中,突然成了陌生之物。
双雪涛写过很多艳粉街故事,那是衰落的老工业区化身。随着城市拆迁改造的步伐,童年、熟悉的环境、父辈的传说等纷纷消散,短短20年,伴随个体成长,世界突然变成他者。曾经因熟悉而笃信的一切,已经烟消云散,让人怀疑:它们真的存在过吗?我真的存在过吗?
作为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子民,我们连邻居是谁都不太清楚,那么,我们又如何相信《干将与莫邪》是真实的呢?当它日渐消退为一个网络故事,且远不如其他网络故事那么刺激与传奇时,我们又如何从中获得养分?
故事的生命来自讲述,讲述的空间消失了,故事的生命也将终结。如果历史与个体成长无关,它就不再被承认为历史。
“报*父之仇”为何变成父爱神话
于是,在小说版《刺*小说家》中,双雪涛采取了一个非常村上春树的进入方式——为了凑钱去北极,看北极熊,作为昔日的银行职员的“我”去应聘特殊情况处理师(其实就是*手),在被接待的律师尊为“前台金融家”(就是银行柜员)后,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任务。
双雪涛用那么长的篇幅去写那个无聊的应聘过程,是在反讽现代人故作理性的无聊,他用这种方式,将读者带入极具真实感的荒诞氛围中。毕竟,大多数现代人都经历过这种无聊的过程——上学时,老师说好好学习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工作后,部门领导说努力就能多赚钱,成为成功者;终于负责一个部门了,老板说只要业绩好,可以给股份……从结果看,大多数人渡过的依然是普通人生,但人人都觉得自己算“中等偏上”。
在小说中,“*小说家”与“复仇”是两个平行故事,都不以真实取胜。双雪涛的真实目的,是在用小说来探索一种可能:重建《干将与莫邪》与当代人的关联。
作为被分笼饲养的新人类,我们是否还有被《干将与莫邪》打动的可能?我们是否还能从自己的文化根脉中,获得滋养?
于是,“报*父之仇”的母题被淡化了,双雪涛将它改写成父爱神话。红衣人消灭赤发鬼,是为寻找失去的女儿小橘子,至于久藏(相当于《铸剑》中的眉间尺)的心中,其实对赤发鬼并无太多仇恨,只因发着恶臭的、濒死的母亲的嘱托,使他不得不去复仇。这个“红衣人”并不陌生,在鲁迅的《铸剑》中是以“黑衣人”的身份出场,隐喻着时代精神。
这是一部很难影视化的小说
早就听说《刺*小说家》将影视化,却一直不太相信这是事实。毕竟,这种对世界运转底层逻辑的深入思考,该如何用影视语言来表达呢?
首先,影视语言需要故事,而故事本身就有反真实的一面。绝大多数人生不是故事,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尾,生活由细节构成,很少是情节。人类试图“概括”与“拔高”生活,很可能是一种狂妄——用一套虚假的、无法实证的逻辑,将集体幻觉合法化。可问题是,影视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产物,不用故事这种歪曲生活的常用手段,它又能怎样去娱乐观众呢?
其次,奇幻的场景不易给观众以真实感。在原著中,有较多奇幻描写,但小说的画面感是为主题服务的,与影视的画面感有巨大隔阂,《爵迹》《九层妖塔》等奇幻电影的特效也很精心,却给观众留下“为奇幻而奇幻”之感。毕竟奇幻与现实之间有隔阂,只靠画面,说服力不足,影响了观众代入感。
其三,原著的目的不是讲故事,而是用故事来表达作者对后现代的认识,其内核非文字难以传达,而图像可传达的故事部分,在原著中不仅不完整,且缺乏逻辑性。在小说中,双雪涛采取了“小径分岔的花园”式写法,并不是依照“情节”的需要来结构,而是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人物行为、事件流向如此不确定,这种非典型、多元叙述恰好违反了戏剧所强调的统一性。
种种原因,已构成影视创作的难题。
电影精彩,但原著更养精神
从结果看,电影版的处理堪称可圈可点。
首先,简化了主题。忽略了原著中后现代批判的内核,将主题篡改为赞美父爱,以此把“虚”(魔界的争斗)和“实”(刺*小说家)结合了起来,并为“刺*小说家”建立了一个新的叙事逻辑——小说家路空文(董子健饰)是老板李沐(于和伟饰)当年合作伙伴的儿子,*掉他可以斩草除根。
其次,增加了故事量,故事逻辑也变得更完整。在电影版中,强化了小说与现实的关联,即小说走向可能决定老板李沐的生死,这既增加了神秘感,又在“虚”和“实”之间形成中间地带,将原本分裂的故事线绑定在一起。
电影人物设置与小说略有不同,比如在小说中,小橘子只是同名,“我”和红衣人无关,在电影中,结合成一个人,由此创出关宁替路空文写完小说的情节设计。这种设计是否高明可另议,但随着故事量的丰富,整部影片的节奏确实明显加快。
其三,在视觉呈现上,突破了原著框架。在原著中,赤发鬼、红衣人更具符号意义,不够具象。没读过鲁迅先生的《铸剑》,就很难明白“红衣人”与“黑衣人”的互文,但电影观众更倾向于视觉记忆,而非深层文化记忆。
电影版创造出赤发鬼攻城、赤发鬼与红衣人决斗、屠城、主角被追*等场面,这些设置可能会引起争议,但这些熟悉的细节消除了“为奇幻而奇幻”之感,还为强化视觉刺激提供了更多空间。
其四,融入时代议题。比如对高科技的批判、控诉信息时代中个体隐私被掌控、反思现代人格等,虽不深入,但议题多元化契合读者的真实感受。
奇幻电影难就难在“真实”,在不同背景下,人性的基本设定、情节的基本逻辑都会发生扭曲,何况《刺*小说家》中还包含了古代内容。把不同时代的故事揉和在一起,不让观众觉得突兀,验证着创作者的功力。对于探索中的中国奇幻电影,《刺*小说家》作为阶段性的成功案例,颇有借鉴价值。
在电影版《刺*小说家》中,有一个细节处理比小说更精彩,即结尾时红衣人手持加特林机枪追*赤发鬼,这个颇具漫威风格的场面是典型的后现代手法,既戏谑,又过瘾,而且深层合理。
当然,电影版《刺*小说家》在思想深度、艺术震撼力等方面,与小说不可同日而语,当许多观众还用庸俗象征的角度去理解它,把片中人物生搬硬套为某个社会群体的写照时,实在忍不住要说:还是读点好小说,更能滋养精神。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