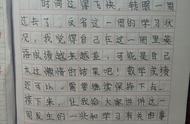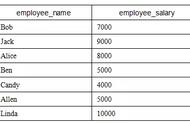主张经世致用,写下《劝学篇》:清末儒臣张之洞活得太纠结
以“中体西用”而闻名的一代儒臣张之洞,将转变大时代中的所有尴尬和冲突,都在他的人格心态中浓缩地展示出来。
同治光绪年间的官场,位少人多,因镇压太平军而崛起的湘淮军人,以军功占据了封疆大吏大半;朝廷缺钱,又让一批杂佐以银子铺路,以捐纳挤入官场。于是鸠占鹊巢,仕途拥挤,本来等着外放的翰林们就前途无望了。
他们牢*满腹,怀才不遇,同味相投,于是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形成了一个清流党。李军机于张之洞是他河北的同乡前辈,清流的风格又很对自己的口味,张之洞毫不犹豫入了伙,成为与张佩纶齐名的清流党大将。清流个个正途出身,满腹经纶,看不起当时炙手可热的“浊流”——洋务派封疆大吏。慈禧太后也乐见借助清流的势力,牵制如日中天的恭亲王和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员。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最大的敌人是李鸿章。在张之洞他们看来,李中堂是“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张之洞要乖巧得多,他懂人情世故,只是正面提出建言,即使有批评,也是对事不对人,很少有纠弹官员之举。他的上疏得到各方赏识,更为慈禧所另眼看待。

慈禧太后像
假如张之洞没有机会外放,大概他终身会成为清流的死忠党。偏偏不久机会来了,朝廷命他出任山西巡抚。在这之前,虽然做过两任钦差学政,他并没有主管行政的州县地方官的经历。因为有慈禧的眷顾和同乡李鸿藻的关照,竟然越级提拔,获得“特擢”,成为封疆大吏。这是张之洞人生的最大转折点。在翰林院任职言官,尽管放言高论,应该如何如何,不必为结果担责。一旦主掌地方,就不得不表现,以政绩证明自己。张之洞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明白,世道已经变了,假如不懂洋务,便实现不了富强,而在一个竞争的世界,富强正是生存之本。
从山西巡抚开始,到后来的两广总督、湖广总督,20多年的封疆大吏生涯,让他从一个高谈阔论的清流党,变为一个注重富强的洋务派。特别在他督鄂的18年里,视武汉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大力施展湖北新政,后来居上,将原本落后的武汉打造成仅次于上海的洋务重镇。最出名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其质量与数量都在上海、天津之上。武汉这个华中通衢之都,有今日之地位,首先要感谢的是张之洞在清末的首功。
但不要以为张之洞真的摇身一变为完全的洋务派,毋宁说他是以清流为本,洋务为用。清流与洋务构成了他一生的内心紧张,后来他在《劝学篇》中,以“中体西用”的模式加以安顿。事实上,办洋务,并非违背圣人义理。洋务事业,从经世致用而来。儒家之义,本来就有两面:一面是修身,注重道德修养;另一面是经世,落实于社会政治治理。经世而不修身,那是法家的吏道;修身而不经世,则与道家、佛教无异。儒家与法家、佛老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有修身的超越层面,又有经世的世俗性格,在不同的朝代和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办洋务,本身就是儒学内部一场静悄悄的自我变革,它继经世而来,是经世之术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在西风吹拂之下经世的新阶段、再发展,未必违背圣人之学。从曾国藩到张之洞,皆可作如是观。
张之洞最欣赏的是“通经致用”,早在担任四川学政的时候,他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提出治学、读书、习史的根底在于“通经”,熟读儒家经典。但是,通经不是目的,最终乃是要“归于有用”。他说“读书趋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张之洞以饱学之士闻名,其读书之多之杂,在同治年间无时人可比。他给尊经书院的门生开列了2000余种书目,后来作为《书目答问》一书传布全国,成为当时士人们首选的读书指南,其中大部分是经史子集的传统经典,也有几册翻译的西学著作,比如《新译西洋兵书五种》《新译几何原本》《代数术》《数学启蒙》《瀛环志略》《海国图志》《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等。清末的启蒙巨擘梁启超少年时代埋头于科举,不知天地间除了辅导科考的帖括之外还有另外的学问。待他读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顿开茅塞,始知天下还有学问二字!直到七年以后经过上海,才看到了张之洞所开列的这些西书。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读到《书目答问》中西书的时间,也不比张之洞更早。

梁启超像
1898年光绪帝宣布变法,重用维新派文人士大夫,慈禧太后针锋相对,迫令帝党领袖翁同龢免职归兮,部署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执掌京城兵权。帝党、后党冲突一触即发。张之洞形象开明,为帝党所倚重;又死忠太后,为后党所信任,国内外都将调和帝后冲突的目光放在张之洞身上,在变法进入生死存亡的时刻,精明的张之洞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劝学篇》,洋洋数万言,描绘了官僚士大夫的变革路线图,也成为晚清知识分子“中体西用”的纲领性文件。他开宗明义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即使孔孟再世,也不会非议变法。因为可变者,是器械、工艺和法律政制,这是用;不可变者,乃儒家之圣道、三纲之伦理、修身养性之心术,这是体。简而言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用的层面,可以引入西学西法;但在体的层面,坚守圣人之学绝不动摇。整部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讲的是不变的圣人之道;《外篇》务通,以开风气,逐条论述变法的途径。

《劝学篇》
戊戌之后,张之洞与康梁彻底交恶。流亡海外的康梁之言行,让张之洞厌恶,他多次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指责康梁办的《清议报》“诋毁中国朝政,诬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是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1900年八国联军入北京之际,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汉口密谋起义,救光绪复辟归政。张之洞毫不手软,将这个昔日的学生抓捕入狱,亲自堂审,张问:你文才甚优,为何谋乱?唐反唇相讥:你读书而不明理,附和太后,忘了与光绪帝的君臣之义!被捕者中有多位他创办的两湖书院和武备学堂的门生,为了摆脱干系,张之洞不经奏报,第一时间将唐才常等20位起义者*害。自古以来,诛*读书人在史书上一向无好名声,张之洞深知这一点,在政治厉害面前,他断然选择自保。血光之下,他的内心是惶惶不安的。康有为一语道破了他的忐忑心态:“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俯仰无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悯,其用心抑亦苦矣!”
比较起同代人李鸿章,张之洞的确要复杂得多,他不仅是一个能吏,而且还是一个儒臣,他的种种矛盾行为,固然有厉害的算计,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思想上的自觉。这个秘密要到《劝学篇》里面去破译。张之洞说,晚清的求变,有三种路向:一曰保国家,二曰保圣教,三曰保华种。所谓国家,乃是大清王朝也;所谓圣教,指的是儒家纲常伦理;所谓华种,意思是种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清廷推行新政,当然是为大清江山,小江山的存亡高于国家的安危;康有为变制,是为了捍卫儒家圣教;而梁启超鼓吹维新,最关心的是世界竞争大势下民族的生存。
在晚清最后20年,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个亦新亦旧、跨越新旧的人物,旧派嫌他太新,新派又嫌他太旧。新传统主义者的复杂面相就在于此。在用的层面,他是与时俱进的。1901年,他与刘坤一联名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要求清廷在法律、官制、科举、练兵、游学、工商等领域推出全面的新政,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变法三折”成为晚清新政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湖北的新政,几乎都走在全国的前面。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立宪国日本打败了专制国俄国,筹备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张之洞一反之前的谨慎态度,觉得若不尽快立宪,“排满”风潮永不止息,大清江山也将难保。
到了晚年,他眼见新学猖狂,颇有悔意。在他看来,文以载道,人人趋新,用新名词,文体变坏,士风人心也会随之变坏。但新学新政又是他一手提倡引入,为了富强之故又不能重新逐出国门,张之洞因此常常感到痛苦,嗟叹不已。在洋务与新政时代他将书院改为学堂,如今他最想办的竟然又是书院,试图在汹涌的西学大潮面前,保留中国文化的国粹,守护摇摇欲坠的圣人之道。
晚年的张之洞,是孤独的。1907年,他奉旨离开经营了18年的湖北,回到京城以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军机大臣。这年他70岁。回首四顾,这个本来他很熟悉的京城士大夫圈,似乎变得很陌生了,老的一辈已经凋零,过去的风雅成为绝唱。守旧者依然守旧,固陋闭塞,言新者又多是浮躁浅薄的年轻一辈。张之洞与两边都气质有隔,可谈论者几乎绝迹,只能常常独自一人去西山游览,与自然默然相对,口中吟出的诗流露出内心的无限悲凉:“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
张之洞入军机处一年以后,大事发生,光绪、太后几乎同时死去,小皇帝年幼,由光绪的弟弟载沣任摄政王,掌握朝廷大权。
牢记“不可重用汉人”祖训的摄政王载沣,表面上给足了张之洞的面子,实际上并没有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当回事,甚至还不如太后执政的时候。载沣只相信自家人皇族国亲,不给汉人大臣以实权,张之洞屡屡上书,苦谏说:“若舆论不服,必激发革命。”载沣竟然自信满满地回答:“怕什么,有兵在!”这个年龄不到30岁的摄政王其实是一个完全没有主意的无能之人,他只记住一条:掌握兵权,那是他当年出使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二世密授他的统治秘诀。但他不知道,比兵权更要紧的,是人心。
张之洞听到载沣这话,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不意闻亡国之言也!”自此一病不起。临终之际,摄政王前来探望,张之洞有满腹的忠言诤语要倾吐,但载沣只是虚与委蛇,要他不必多想,好好保养。待载沣离开,张之洞长叹一声:“国运尽矣!”几天之后,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