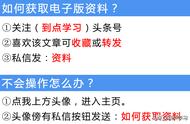有人认为,今人作旧体诗,重要的是能表达出“现代的感觉”,不过更多人是试图找寻现代生活中的古典诗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既教授古典文学,又亲身实践,他的心得是作旧体诗须讲求“法度”——强调技术门槛——在他看来,这是造成诗美的必要条件。他六年来吟咏国内国外事象,得古、近体诗1402首,新近结集成《巢云楼诗钞》(团结出版社,2023)出版。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旧体诗是否过时了呢?又是否,唯有旧体诗方能张扬汉语之美?近日,汪涌豪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谈谈他“守旧的理由”。

“勒马回缰”与“游子返辔”
文汇报:六年得诗千余首,可谓高产。是什么动力让您坚持每天都写,又有何心得?
汪涌豪:说来也是因为喜欢,从不觉苦。加以一直教古典文学,治传统诗学,对古诗比较了解。再往前说,则小学时抄旧版《辞海》,中学时背唐宋诗词,许多积累无处打发,以后写入论文,又常被指为冷僻生造,只有交付于诗了。之所以将六年来的诗结集出版,除纪念一段岁月,私心还想为古诗和汉语争一下当下的地位。这个是我特别想说的。
我认为既作旧体,须讲法度,尤其作律诗,整(句字齐整)、俪(对偶工稳)、叶(奇偶相对)、韵(押平声韵)、谐(平仄合格)、度(篇字划一)的合体合格是必须的。这些看似简单,但要运用自如,大不易。就拿对偶来说,远非同质字词对列就成。它意义上有互文,句法上有交股,如只是“青山”对“绿水”,正如朱熹所说,“一日作百首也得”,就没意思了。所以自己在这方面较用心,带连着对字词和意象也多有讲究。
文汇报:现在作旧体诗的很多,爱好者就更多,以致有人认为旧体诗已“全面复兴”,对此您怎么看?
汪涌豪:确实不少。上有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号召,下有各地学会、诗社推动,参与者早过两百万,且年龄、职业分布广泛。近年来,随国学升温和网络普及,其势更见炽盛。《光明日报》曾作过调查,有89%的受访者直承是旧体诗爱好者,超过新诗的33%,《中华诗词》的发行量也已盖过《诗刊》。至于网络上,先是天涯社区,后来是各微信公众号和知乎、抖音,年轻的作者纷纷涌起,如曾峥的“兽体”、段晓松的“实验体”和曾少立的“李子体”各竞所长,赚足了人气,以致有“当代诗词在网络”一说。
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就现代旧体诗能否入史展开讨论,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旧体诗设置了专章,巴蜀书社推出了《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北大出版社《大学新语文》选入了一组当代学人旧体诗,鲁迅文学奖也开始向旧体诗开放。故相较“五四”时反旧文学蔚成风潮,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指其“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的国民性互为因果”“腐败极矣”,柳亚子《旧诗革命宣言》更断言“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五十年以内的事”,说现在是旧体诗创作的最好时期并不为过,但要说“全面复兴”则须谨慎。
文汇报:请您再展开讲讲?
汪涌豪:就个人而言,之所以持谨慎态度,是基于如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是尽管“五四”提倡新诗、反对旧诗的声势很大,但正如刘师培所说,“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许多人认识到这一点,故即使与胡适立场相同的陈独秀也常为之。新文化运动中人,如闻一多所说,“勒马回缰作旧诗”的就更多了。鲁迅、郁达夫自不必说,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合计竟有1500首。学者如黄侃、马一浮、俞平伯、吴宓等人都是会家,陈寅恪、钱锺书的旧体诗近些年更传诵人口。
故准确地说,旧体诗虽一度蒙尘却从未退场,传统的诗艺虽隐没不彰却从未中绝。它述情深至,用语渊雅,不仅较“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样的白话诗更见含蓄,即使较再后起的各种新体诗也一点不差。龚鹏程甚至认为,新诗虽与“五四”有血缘关系,并接受了西方影响,总的来说还“是中国古诗或中国人意识影响下的产物”。他进而还将从余光中到西川等新诗人致敬古诗的现象称为现代诗的“游子返辔”,这正与闻一多的“勒马回缰”说构成对照,很可以说明旧体诗是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核心体式。
联想到“九叶派”老诗人郑敏晚年接受采访,直承后悔他们那代人当初只知提倡新诗,以致造成旧体诗式微。当然,旧体诗终究没有式微,一直到新时期,如《王蒙文存》就收入了155首。至于普通人每遇深彻的感动,常会不由自主地将其印入眉间心底,或由其代自己传达曲曲心事,更说明了这一点。
诗乃有声之文,生色之体
文汇报:您刚提到作旧体的“法度”,恐怕是横亘在现代人面前最大的困难了。
汪涌豪:确实,这就涉及我要说的第二个事实。当今诗坛作者作品虽多,大赛论坛虽繁,或许还包括提倡“新旧体运动”与“当代诗词学”的呼声虽高,但创作实绩有限,作者对诗歌本体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此题说来话长,这里仅就着“声”“色”两字稍作展开。
前者是说诗乃“声体”,即有声之文,须尊体守律,平仄押韵,违弃格律,断不成诗;后者是说诗为“生色之体”,从来重藻饰,并与声偕行。不尚修辞,断非好诗。但遗憾的是,许多人觉得这两方面的规定有碍表达。他们的理由是,时代变了,人的情感、生活与审美也随之改变,故韵不必求工,声可以从意,体则可以从己。有些人甚至认为可以由不讲长短篇幅、不重粘对规则、不拘泥押平水韵,只须畅口顺耳的“新格诗”代替。
举网上一首《丙申仲春气候感怀》诗为例:“天意无端戏弄人,忽逢尧舜忽逢秦。轻纱初展玲珑态,转觉长裘格外亲。簌簌残红伤老大,萋萋新绿忆王孙。晴明时节从来少,珍重心头日一轮”。作者勤于创作,许多诗写得不错,但认为旧体诗发展至今,必须创新,所以提出“要永不松懈地与写诗习性和惯性作斗争”这样的主张。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这首诗不押平水韵。不押平水韵也行,问题是用新颁的中华新韵与中华通韵检核,也有好几处破绽。这让人想起前辈叶恭绰说的话:“第文艺之有声调节拍者,恒能通乎天籁而持人之情性”。它固然对作者有所约限,却是造成诗美的必要条件;它或许拦住了一些人莽撞的进入,却从未成为诗人真正的负担。
文汇报:感觉这首诗的用语十分现代。想知道用旧体诗表现当代生活,在这方面应注意什么?
汪涌豪:这就关涉前及第二个字“色”了。“色”又称“辞色”,指文法修辞,从来为古人所切讲。唯此,东西方汉学家常用“修辞性”来标别以诗歌为中心文型的中国文学的特质,如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就说:“尊重理智的修辞决定了成为中国文学中心的与其说是所歌咏之事,所叙述之事,倒不如说是如何歌咏、如何叙述。换言之,往往常识性地理解素材,却依靠语言来深切感人,这可说是中国文学的理想。”
作旧体诗,情感固须得诸己,辞色却必须有出处,见本源。以此标准看上面这首诗,用语不免太现代了。古诗有说“格外”的,但很少说“格外亲”,为其指常情常礼之外,非特别、更加之意,如杨万里《兰花五言》之“花中不儿女,格外更幽芬”,张侃《寄曾兄》之“年来格外添新句,夜静灯前理旧书”。一味以今人用法混入,就有失典雅。另外诗中对偶也不工稳,颔联勉强算流水对,但较前人之“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孟浩然)、“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杜甫),用语俗近,且缺乏必要的对应;颈联中“老大”是形容词,可对“少壮”却不能对“王孙”。再加上平仄有瑕疵,修辞上的努力基本没有,诗的品质难免受到影响。
因此个人常强调写旧体诗须留心字词及其特殊的组合方式,类似重意合不重形合,重人治不重法治;常有意突破语法规制,通过省略人称、时态和虚词,造成一种“间阻”效果,以增加诗的“陌生感”等等,它们能增诗之“色”,需细加体味。海德格尔说:“诗的本质必得通过语言的本质去理解”,此理通于中西一切诗。故排除西式语法的干扰对作旧体诗来说很重要,主谓宾一个不缺,定状补太过常规,又不知比兴,鲜有寄托,不但会挤占原本就不大的作品篇幅,还会收窄亟待淬炼的诗美空间,是很难写成好诗的。
说到这里,想再引一位前辈的话。张中行在《诗词读写丛话》一书中,就此说过自己有一个“来自实际”的“守旧的理由”,即诗境虽人人向往,但找到它非得与现实保持距离不可,方法之一是“用旧词语”,“金钏诗意多,瑞士手表诗意少;油壁香车诗意多,丰田汽车诗意少”。当然现代语也可用,但须乞援于暗示和朦胧,不然“迷离渺远”化为“明晰切近”,诗意就差了。他的话可谓内行。

旧体诗与汉语的“忒修斯之船”
■汪涌豪
世纪之交,“百年中文,内忧外患”成为热门话题,因为汉语外受西语影响,大大欧化;内则自信不足,迭遭修葺,与传统几度发生断裂。聚焦于诗,症状尤其明显。这里有文化自信问题,更有认识不足问题。
其实,从索绪尔、芬诺洛萨、罗兰·巴特到刘若愚、叶维廉、程抱一,东西方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都肯定汉语的诗性功能,即使孙大雨、卞之琳和梁宗岱这样的新诗人,也提倡依托汉语特性组织诗体。直到今天,“重新发现汉语诗性”的呼吁依然不绝于耳。这足证汉语固有之美,但也反映了维护和彰显这种美的艰难。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极致,集中体现了这种艰难,故尤需人用心呵护,以防止其再度断裂。
为了汉语之粹美能发扬光大,进而旧体诗创作能有更广远的发展,个人认为尊体重法非常重要。只有体式上守正,才能浚发本原;再继以辞意上开新,才能回应时代。中华诗词学会提出“知古倡今,求正容变”,“倡今”“容变”必须建立在“知古”“求正”基础上,而“知古”“求正”又绝不应被视为骸骨迷恋。基于此,不要轻言汉语已不足用。相反,要相信它有足够的弹性容纳变化了的生活。想到网上读到的一首《癸未仲春自京还乡》:“十年孤旅偶还家,童子窥帘母递茶。却睹棠红心自怃,事亲不及一庭花”。作者异地打拼回家,乍见看顾弱子的母亲,为不能尽孝而自责,这样的事不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还有一首《吾妻》:“嫁个郎君爱写诗,家贫百事自操持。忙中哪得临妆镜,瘦到梅花总不知”。用情更含蓄,可称闺情诗的当代版,也可证传统体式并无碍今人的表达。
此外,向传统学习,提高修养也很重要。这与尊体重法互为表里。当年,朱自清向黄节求教作旧体诗,黄节告以须从汉魏六朝开始“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以后他将所作编成《敝帚集》,有“獭祭陈编劳简阅,肠枯片语费矜持”之叹。对照王力说“作古诗文,非熟读几十篇佳作,并涵咏其中莫办”,晚年胡适对学生唐德刚说“作诗词非得有几十年的功夫”,可见对程式化意味浓重的中国诗——其实也包括一切中国艺术而言,向传统学习是必不可少的。有此基础,才谈得到融合古今,汇通中西。而这种融合汇通的目的仍然是为张大汉语的传统,彰显诗歌的“汉语性”,这是个人认为要写出具有民族气派和传统韵味的好诗的前提。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有理由乐观地瞩望旧体诗未来的命运,并相信对每个人而言格律和修辞不是妨碍,它们能让你与别人不同,进而让现在的你与过去不同。
最后,想引一则“忒修斯之船”的隐喻。说的是忒修斯人自克里特岛凯旋,所搭乘的船被雅典人保留了下来,用做纪念。以后时间流逝,船体朽腐,雅典人只得不断用新木头替换朽坏的旧木头,最后所有木头都替换过了,古希腊哲学家就此发问:“这还是原来那艘船吗?”假定事物的构成要素被置换,那还是原来那个事物吗?愿轻忽汉语和旧体诗本位的人能想想这个问题。
编辑:李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