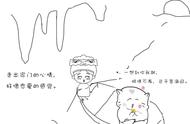严监生,大多数人听到这名字想到的是那"两盏灯草",想到的是那两只枯瘦的手指,想到的是那可笑又可悲的人生。一直以来,在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中,严监生的故事最为人们所熟知,从某种程度上说,"严监生"这个人物塑造的颇为成功。然而,不知是因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过于放大,还是因为人们自动忽略了其人性的多面性, "严监生"便渐渐和"吝啬鬼"划上等号,成为一个公众认同的代名词。

其实,如果抛去对严监生的标签化,我们不难发现,他绝不仅仅有吝啬至极的一面,甚至可以说他的吝啬有让人憎恶的一面,也有让人同情的一面。如同他的一生,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以至于到了自贱自虐的地步,还浑然不知,愈陷愈深。这种畸形的人格,呈现出了太多可知与不可知的人性的晦暗,暴露了太多可说与不可说的灵魂的怯懦。要想全面认识严监生这个人物,的确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不只是对于这个人物,也是对于我们自己。

1、挥金如土的自甘
严监生的原配妻子王氏,重病在床。严监生每日小心照顾,时时慰问,在治病吃药上更是不曾怠慢。"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严监生从未有吝啬之意。而后不久,王氏终究还是撒手人寰。对于王氏的丧礼,书中这样描述到:"自此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闹了半年"。既没有细致入微的场面铺陈,也没有浩浩荡荡的送葬仪式,但只这一句话,已经足够展示出严监生复杂人性中的一面——挥金如土。当然,在封建社会,婚丧嫁娶之事对于稍有名望的家族来说,都是要按照规定的礼法制度来办理的,但严监生在丧礼这件事情上显示的心甘情愿的慷慨确实不容忽视。联系严监生的种种表现,种种行为,我们似乎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追问:严监生真的吝啬吗?吴敬梓先生这样的人物塑造,不仅赋予人物极大的人性张力与艺术魅力,而且使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有生长、发展与突破的空间,这种自觉自知的创作意识将读者引入一个超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理性至境。

2、仁夫慈父的自白
虽说原配王氏已经过世,严监生也将侧室赵氏扶为正方,但他终究有许多"不放心"。每日在账房中盘点账目,茶饭不思,精神恍惚;或对着儿子暗自落泪,只恐家产散尽,儿子无所依靠;或时而念及王氏,怎奈物是人非,斯人已矣……此时的严监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仁夫慈父,他是一家之主,也是千千万万个平凡人中的一个。这样的严监生,我们很难将他与吝啬联系起来,这样的他让我们想到自己,又或是自己熟悉的某一个人。也许严监生这个人物之所以深深烙印在无数读者心中,正是由于他性格中的这一隐晦而又微弱的光亮。这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总能让我们找到活生生的生活原型。毕竟,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拒斥无病*,呼唤人性纯真。
3、潦草收尾的自警

对于严监生的结局,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片段,也是最能凸显他性格特征的一幕,但这样潦草收尾的结局与前面呈现给读者的复杂多样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同我们在观看一场烟火表演,经历了一个预热、绚丽,终于又归于安宁的生命周期。所不同的是,烟火留下的是一颗颗燃过的、焦黑的砂砾,而严监生留下的是一个个深沉而有力的警示,一声声悠长而哀怨的唏嘘。我想,大概没有人能说清严监生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智人还是愚人,是仁人还是恶人,但是如果仅用"吝啬"一词来概括他的生命轮回,这不仅是对人物非艺术化的歪曲,也是对吴敬梓先生呕心沥血之作的误读。"撮口山"的设计使人物回归简单甚至平庸,仿佛回到最初的原点,原始、本能的*与人格从一开始就在觉醒,无论中途多么跌宕起伏或是平淡如水,在死亡来临的时刻,都将仓促而过,潦草收尾。这一点正是吴敬梓先生的高明之处,以无胜有,以少胜多,所有的情难断,所有的意难平,都消释在千百年的漫漫追忆里。

与其说吴敬梓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跨越千年而不朽的典型人物,不如说是为我们书写了一个亦真亦假、亦幻亦实的"心中人"。至于其中的是非因果,在后人的纷纭评说中,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对于文学作品,我们在意的,是其灵魂的深度与生命的魅力,而永远不只是善恶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