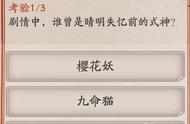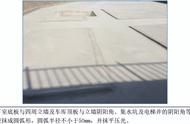一
这是一个奇男子的故事。
打个比方说,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像夜空中随风飘动的云朵般的男子。在昏暗中飘动的云朵,看不出它在一瞬之间形状有何改变,但若一直注视着它,会发现不知不觉中形状改变了。本是同一片云,形状却无从把握。
就是这样一个男子的故事。
他的姓名为安倍晴明,是一位阴阳师,生于延喜二十一年,应在醍醐天皇之世。但这个人物的生辰死忌,却与本故事没有直接关系。也许不弄清这类数字,反倒能增添故事的妙趣。
不必在意这些问题吧。那不妨信笔写来好了。这种写法说不定正适合安倍晴明这个人物。
平安时代仍然是民智未开的时代,有好几成人仍对妖魔鬼怪的存在深信不疑。在这样的时代,人也好鬼怪也好,都屏息共居于京城的暗处,甚至在同一屋檐下。妖魔鬼怪并没有藏身于边远的深山老林。
阴阳师,说白了,叫占卜师也不妨。称为幻术师、神汉似乎也可以,但都不够准确。
阴阳师观星相、人相。既测方位,也占卜。既能念咒,也使用幻术。
他们拥有呼唤鬼怪的技术,那种力量肉眼无法看见,与命运、灵魂、鬼怪之类的东西进行沟通也不难。朝中甚至也设有此种职位,朝廷设有阴阳寮。
晴明被朝廷授予“从四位下”的官阶。一位是太政大臣。二位是左、右大臣和内大臣。三位是大纳言、中纳言。朝中议事,晴明有相当的发言权。
在《今昔物语集》里面,记载着这位安倍晴明的好几件趣事。
据书上说,晴明自幼师从阴阳师贺茂忠行修行。自那时起,晴明便显示了某些阴阳师独具的特殊才能,可归入天才之列。
《今昔物语集》记载,晴明年纪尚小,某个夜晚随师父忠行外出,到下京一带。
下京位于京城南面。从大内穿过朱雀门,沿朱雀大路走到尽头,差不多在京城南端的罗城门附近。大内到罗城门之间约八里有余。
晴明一行乘车外出。
《今昔物语集》没有载明是何种车。应该是牛车吧。何故连夜前往下京,书中也同样没有写清楚。不妨假设是偷偷摸摸去那里会相好的女人。
忠行自己乘车,随行人员徒步。随行者包括晴明在内仅二三人。除了牵牛引路和提灯照明的,余下的一人就是晴明。他这时的年龄,书中没有提及。试着推测的话,应该只有十岁出头。
其他随行人员都穿一身精*直垂,晴明却穿着显旧的窄袖便服配裙裤,赤脚。他穿的应该是别人的旧衣服。
按常理来说,他身上的旧衣服难掩才华,脸上该透着凛然之气才是。其实不然。他那端正的脸庞,肯定是这个年龄常见的娃娃脸。
在某个重大关头,却表现出颇为老成的言行——他应是这种类型的少年。
可能在老师忠行眼里,年轻的晴明瞳仁深处,时时闪现着他人没有的才华的火花。但也仅此而已。
因为忠行察觉晴明内蕴的灵气,其实是始于这个晚上发生的事。
还是言归正传。
牛车平稳地走着,来到京城边上。忠行在车里睡得很踏实。走在车旁的晴明,无意中往前方一望,发现有种怪异的东西。
从对面走来的,不正是青面獠牙的“恶鬼”吗?
随行的其他人似乎丝毫没有察觉。
晴明马上打开车窗。
“忠行大人……”
他唤醒睡梦中的忠行,急急报告所见的情况。
忠行醒来,把头探出车窗外,往前望去,果然看见一群鬼魅远远走来。
“停车。”忠行对随行人员下令,“躲到牛车的阴影里,屏息不动。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忠行运用方术,让鬼魅看不见牛车和这些人,便走了过去。
自此以后,忠行常让晴明跟在身边。据说他将自己平生所学悉数传授给了晴明。
《今昔物语集》有云:“如灌水入瓮。”意谓贺茂忠行将自己的瓮中之水——阴阳之法,毫无保留地倒入安倍晴明这瓮里。
忠行死后,据说晴明的住宅位于土御门大路以北、西洞院大路以东的方位。若从处于大内中心的紫宸殿来看,则为东北面,即艮(丑寅)的方位,也就是鬼门。
平安京的东北方有比叡山延历寺,而大内的东北方位又设置阴阳师安倍晴明的住处,这样的双重安排并非偶然。
平安京这座都城的形状和结构如此设计,是因为发生藤原种继被暗*的事件之后,要保护桓武天皇免受废太子早良亲王的怨灵侵害,所以仅十年就放弃了长冈京,转而建都平安京。
不过,这些都是晴明出生之前的事。与这里要讲的故事没有直接关...
且说晴明住在鬼门方位的宅邸里,有一天,一位老法师前来拜会。老法师身后跟着两个十来岁的童子。
“法师因何事来访?”晴明问道。
“我居住在播磨国。”法师答道。
报上自己的名号智德之后,老法师旋即说明来意。
自己一直想修习阴阳道,就听到的传闻而言,最精于此道的阴阳师就是您。请无论如何也要教我阴阳之法,一点点也好……
智德老法师将这番意思告诉了晴明。
听了老法师的话,晴明心想,这位法师正是精于此道的人,这番安排正为试探我。
晴明察觉到了老法师真正的目的:他阴阳之道颇高,一定是来试探自己的。带来的两个童子也许是式神。
唔,也好。晴明心中暗笑。
所谓式神,也可写成识神,就是一种平时肉眼看不见的精灵。
它不算上等的灵,是杂灵。阴阳师用方术将杂灵作为式神,用以驱使。但根据阴阳师的功力,所操纵的杂灵的档次或为上等,或为下等。
“原来如此。”
晴明边点头边在心里赞叹:并非等闲之辈啊。因为自称智德的老法师所用的式神,是半吊子水平的人难以控制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可是,今天还有些推不掉的重要事情……”
晴明对老法师解释,请他暂且回去,稍后择过吉日,再烦请移步见教,是否可以?
说着,晴明把双手伸到袖内,悄悄结了印,默念一咒。
“那就等择过吉日……”老法师搓搓手,用手抵住额头,回去了。
可是晴明没有动。他抱着胳膊站在那里,仰望天空。
不久,他估计老法师已走出一两个街区,却见老法师穿过敞开的大门返回,边走边四下张望,不放过可能藏人的地方,诸如门口、上下车处。
老法师再次来到晴明跟前,说道:“本该跟在我身边的两个童子,忽然不见了。是否可请赐还?”
“还给您?”晴明佯作不解地对老法师说,“我没干什么呀。您刚才也在场,很清楚的。我就站在这里,怎么能把两位童子藏匿起来呢?”
听了这话,老法师向晴明低头致歉:“对不起。其实那不是童子,而是我使用的式神。今天我是来试探您的功力的,可实在望尘莫及。请原谅我吧。”
老法师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您要试探我不妨,但草草行事可骗不了我。”
晴明说话的腔调为之一变,得意地笑了。
一种不算粗俗也不那么高雅的笑容,浮现在他的唇边。那唇悄然解除了咒文。
很快就有两名童子从外面跑进来,手中各自托着酒肴。
“让他们在外面买的。难得让我高兴,这些酒菜你们就带回去吧。”
如果此时晴明真的调侃一句,倒是适时而有趣的事,但《今昔物语集》上并没有记载,只写了两名童子飞跑进来。
老法师心悦诚服,说道:“自古驱使式神并非难事,但将他人操纵的式神收藏起来,可不是一般阴阳师做得到的啊。”
老法师激动得脸都涨红了,定要拜晴明为师,并写下自己的名签交给晴明。
一般说来,亲手写下自己的名签交给对方,在练方术的人中间是绝少有的事。这样一来,就等于把性命交到对方手上。
《今昔物语集》的记载还有这样一段。
有一天,安倍晴明前去居住在广泽的宽朝僧正的住处。年轻的贵公子和僧人都挤过来要跟他说话。大家都听过关于晴明的传闻,要说的话自然集中在方术上面。
“你是惯使式神的,那么,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人吗?”有人直截了当地问。
“这行当里的秘事,也好这样贸然打听吗?”
说不准晴明就是以一种骇人的眼神,直视这名提问的贵公子。
等这位贵公子露出胆怯的神色,晴明才掠过一丝自得的微笑,说道:“哪能轻而易举就*人呢。”
他让贵公子们放心,也许还加上了一句:
“哈,不过方法可是太多啦。”
“那*死小虫子之类的,肯定轻而易举吧?”又有一位贵公子问。
“哦,没错。”
晴明应答之时,庭院里恰好有五六只青蛙跳过。
“你能*死其中一只吗?”这位贵公子继续追问。
“可以。不过……”
“有什么妨碍吗?”
“*未尝不可,但*了之后却无法让它复生。无益的*生是罪过。”
“试一下身手吧。”
“我很想见识一下。”
“我也是。”
“我也是。”
贵公子和僧人们都聚拢过来。
对于晴明的方术,大家早有耳闻,都想亲眼见识那番光景。这番好奇心让众人眼睛发亮。
从这种情势来看,若此时晴明借辞推托、不当场出手,就会成为众人的话题,被说成“这家伙也不过如此,有名无实”。
晴明瞥一眼众人,说:“你们真要让我做罪过之事吗?”
他随即念念有词,伸出右手,用白皙的手指从垂落屋檐的柳条上随手摘取一片嫩叶,将叶子往空中一抛,念咒。
叶片飞舞在空中,轻轻落在一只青蛙上面。就在一刹那间,青蛙被压烂了,当场死掉。恐怕是蛙肉与内脏涂地。
僧等见此,皆大惊失色。
《今昔物语集》如是说。
晴明似乎还在家中无人时使用式神。家中明明没有人在,板窗却能自动打开、关闭;即使没有人去开门关门,房门也能自行开关。
种种不可思议的事,发生在晴明周围。
翻翻其他资料,看样子这位安倍晴明偶尔好使方术吓人,从智德法师和*青蛙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晴明好像颇以此为乐。一方面正正经经,给人一丝不苟的印象,其实也有孩子气的一面。
以下只是我的想象:安倍晴明这家伙,恐怕在为朝廷服务的同时,也有不少与凡人相同的地方,尤其对人情物理了如指掌。
他是一位身材修长、肤色白净、目光如水的飘逸美男子。
当衣着典雅的他漫步走过,宫中的女人们目睹其风采,一定会窃窃私语。想必也收到过一些血统高贵的女人送出的、写有含情脉脉的和歌的书信。
晴明凭借自己的聪明,处世几乎万无一失,但似乎也有无意中出言莽撞的时候,例如一不留神就对天皇脱口而出:“哎,哎!”
浮现出典雅微笑的双唇,有时也会浮现出卑劣的笑。
由于阴阳师这一职业的性质,他既须通晓人性的黑暗面,在宫中又须具备相当高的修养。汉诗要熟记于心,吟咏和歌的能力要有,乐器方面也须有一两种拿得出手,比如琵琶、笛子之类。
我想,平安时代是个风流典雅却又黑暗的时代。
此时,我就要讲述这位男子的故事。他像风中浮云一样,飘然隐身于多姿多彩、风流文雅却阴森可怖的黑暗之中。
二
朝臣源博雅登门拜访安倍晴明,是在水无月之初。
水无月即阴历六月,以现在的阳历而言,大约是刚过七月十日。这期间,梅雨尚未结束。
连续下了好几天雨,这天难得地放晴了,但也不算阳光明媚,天空像蒙了一层薄纸般白茫茫的。
时值清晨。树叶和草叶湿漉漉的,空气清凉。
源博雅边走边望着晴明宅邸的围墙。这是大唐建筑式样的围墙,齐胸以上的高度有雕饰,顶上覆以山檐式装饰瓦顶,令人联想到寺庙。
博雅身披水干,足蹬鹿皮靴。
空气中悬浮着无数比雾还细小的水滴。在这样的空气中步行,水*布料就会吸附这种小水滴,变得沉重起来。
朝臣源博雅是一名武士,左边腰际挂着长刀。看样子年过三十五,但没到四十。走路的样子和言谈间透着习武之人的阳刚气质,相貌倒显得平和,神色中有一种较真的劲儿。
此刻,他一副劲头不足的样子,看来心中有事牵挂。
博雅站在门口。院门大开,往里面探望,看得见院子里的情景。满院的草经昨夜雨水滋润,青翠欲滴。
这岂非一座破庙?
这样的表情浮现在博雅脸上。
虽说还不至于到荒野的程度,院子也的确未加修整。
正在此时,芬芳的花香钻进了博雅的鼻腔。原因一望而知。草丛中长着一棵经年的大紫藤,枝节上仍有一簇盛开的紫藤花。
“他真的已经回家了?”博雅嘴里咕哝。
早就知道晴明是个喜欢任由草木随意生长的人,但眼前所见似乎又太过分了。就在他叹气的时候,正屋那边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虽说是女子,却身着狩衣(狩衣:平安时代由狩猎服演变而来的男式便服;直贯,公卿贵族日常穿的束脚肥腿裙裤)和直贯。
女子走到博雅跟前,微微躬一躬身,说道:“恭候多时了。”
这是个年方二十、瓜子脸的美丽女子。
“在等我?”
“主人说,博雅大人马上就到了,他要我出迎。”
博雅跟在女子身后,心里琢磨为何晴明知道他要来。
女子带他来到屋里。木板地上放着榻榻米,晴明盘腿坐在上面,两眼盯着博雅看。“来啦……”
“你知道我要来嘛。”
博雅说着在同一张榻榻米上坐下来。
“我派去买酒的人告诉我,你正向这边走来。”
“酒?”
“我出门有一段时间了,太想念京城的酒啦!你是怎么知道我已经回来的?”
“有人告诉我,昨夜晴明家的灯亮了……”
“原来如此。”
“这个把月你到底去哪儿了?”
“高野。”
“怎么忽然就……”
“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就是说,忽然想到了某件事,所以去找高野的和尚谈谈。”
“什么事?”
“这个嘛……”晴明挠挠头,望着博雅。
这两个人的年龄都不易猜。从外表看,晴明显得年轻,相貌也更端正,鼻梁挺直,双唇如薄施粉黛般红润。
“是什么事呢?”
“你是个好人,不过对这方面的事可能没多少兴趣吧。”
“你得先说是什么事呀。”
“咒。”晴明说道。
“咒?!”
“就是去谈了一些有关咒的事情。”
“谈了些什么?”
“比如,到底何谓‘咒’之类的问题。”
“‘咒’难道不就是‘咒’吗?”
“这倒也是。只是关于咒究竟为何,我忽然想到了一种答案。”
“你想到了什么?”博雅追问。
“这个嘛,比如所谓咒,可能就是名。”
“什么名?”
“哎,别逗啦,博雅。一起喝上一杯重逢的酒好啦。”晴明微笑着说。
“虽然不是为酒而来,酒却是来者不拒。”
“好,上酒!”晴明拍拍手掌。
廊下随即传来裙裾窸窣声,一位女子手托食案出现了。食案上是装酒的细口瓶和杯子。她先将食案放在博雅面前,退下,又送来一个食案摆在晴明面前,然后往博雅的杯子里斟满酒。
博雅举杯让她斟酒,眼睛则一直盯着她看。
同是狩衣加直贯的打扮,却不是刚才那名女子。同样年约二十,嘴唇丰满,脖颈白净,有一种诱人的风情。
“怎么啦?”晴明问注视着女子的博雅。
“她不是刚才那个女人。”
那女子微笑着行了个礼,又给晴明的杯子斟满酒。
“是人吗?”博雅直率地问道。
他是问,这女人是不是晴明驱使的式神或其他东西。
“要试一下?”晴明说道。
“试?”
“今天晚上你就金屋藏娇吧……”
“别取笑我啦,无聊!”博雅回道。
“那就喝酒吧。”
“喝!”
两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女子再往空杯里斟酒。
博雅望着她,喃喃自语:“永远都弄不清楚。”又叹了一口气。
“什么事弄不清楚?”
“我还在琢磨你屋里究竟有几个真正的人。每次来看见的都是新面孔。”
“咳,你算了吧。”
晴明边答话边向碟子里的烤鱼伸出筷子。
“是香鱼吗?”
“早上有人来卖的时候买的。是鸭川的香鱼。”
香鱼长得很好,个头颇大。用筷子夹取鼓起的鱼身,扯开的鱼身中间升腾起一股热气。
侧面的门开着,看得见院子。
女子退出。仿佛专等此刻似的,博雅重拾旧话。
“继续刚才的话题吧。关于咒的问题。”
“你是说……”晴明边喝酒边说话。
“你就直截了当说好啦。”
“这么说吧,你认为世上最短的咒是怎样的?”
“最短的咒?”博雅略一思索,说道,“别让我想来想去的了,告诉我吧。”
“哦,世上最短的咒,就是‘名’。”
“名?”
“对。”晴明点点头。
“就像你是晴明、我是博雅这类的‘名’?”
“正是。像山、海、树、草、虫子等,这样的名字也是咒的一种。”
“我不明白。”
“所谓咒,简而言之,就是束缚。”
“……”
“你知道,名字正是一种束缚事物根本形貌的东西。”
“……”
“假设世上有无法命名的东西,那它就什么也不是。不妨说是不存在吧。”
“你的话很难懂。”
“以你老兄的名字‘博雅’为例来说吧,你和我虽然同样是人,可你是受了‘博雅’这咒束缚的人,我则是受‘晴明’这咒束缚的人……”
博雅还是一副不明白的样子。
“如果我没有了名字,就是我这个人不在世上了吗?”
“不,你还存在。只是博雅消失了。”
“可博雅就是我啊。如果博雅消失了,岂不是我也消失了?”
晴明轻轻摇摇头,不置可否。
“有些东西肉眼看不见。但即便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也可用名字来束缚。”
“噢?”
“比方说,男人觉得女人可爱,女人也觉得男人可爱。给这种心情取个名字,下咒的话,就叫作‘相恋’……”
“哦。”
博雅点点头,但依然是一脸困惑的神色。
“可是,即使没有‘相恋’这个名字,男人还是觉得女人可爱,女人还是觉得男人可爱吧……”
博雅又加了一句:“本来就是这样嘛。”
晴明随即答道:“二者又有所不同。”又呷一口酒。
“还是不明白。”
“那就换个说法吧。请看院子。”晴明指指侧门外长着紫藤的庭院,“有棵紫藤对吧?”
“没错。”
“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蜜虫’。”
“取名字?”
“就是给它下了咒。”
“下了咒又怎样?”
“它就痴痴地等待我回来。”
“你说什么?”
“所以它还有一串迟开的花在等着。”
“这家伙说话莫名其妙。”
博雅仍是无法理解。
“看来还非得用男人女人来说明不可了。”
晴明说着,看看博雅。
“你给我说清楚一点!”
博雅有点急了。
“假定有女人迷恋上你,你通过咒,连天上的月亮都可以给她。”
“怎么给她?”
“你只需手指着月亮说:‘可爱的姑娘,我把月亮送给你。’”
“什么?!”
“如果那姑娘答‘好’,那么月亮就是她的了。”
“那就是咒吗?”
“是咒最根本的东西。”
“一点也不明白。”
“你不必弄明白。高野的和尚认为,就当有那么一句真言,把这世上的一切都下了咒……”
博雅一副绝望地放弃的样子。
“哎,晴明,你在高野整整一个月,就跟和尚谈这些?”
“哦,是的。实际上也就二十天吧。”
“我是弄不懂咒的了。”
博雅举杯欲饮。
“对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吗?”晴明问道。
“算不上是趣事——忠见在十天前去世了。”
“那个咏‘恋情’的壬生忠见?”
“正是。他是气息衰竭而死的。”
“还是不吃不喝?”
“可以算是饿死的。”博雅叹息。
“是今年的三月?”
“嗯。”
两人连连点头叹惋不止的,是三月在大内清凉殿举行宫内歌会的事。
歌人们分列左右,定题目后吟咏和歌,左右两组各出一首,然后放在一起评比优劣,就是这样一种宫内歌会。
晴明所说的“恋情”,是当时壬生忠见所作和歌的起首句。
恋情未露人已知,本欲独自暗相思。
这是忠见所作的和歌。
当时,平兼盛欲与忠见一较高下。以下是兼盛所作的和歌。
深情隐现眉宇间,他人已知我相思。
担任裁判的藤原实赖认为两首和歌难分高下,一时难住。见此情景,村上天皇口中也喃喃有词,回味着诗句,他低吟的是“深情”句。
就在藤原实赖宣布兼盛胜的一刻,忠见低低喊叫一声“惨也”,脸色变得煞白。此事宫中议论了好一阵子。
从那一天起,忠见没有了食欲,回家后一直躺在自己的房间里。
“据说最后是咬断舌头而死的。”
似乎无论多么想吃东西,食物也无从入口。
“看上去温文尔雅的,骨子里却是极执着的家伙。”晴明嘟哝道。
“真是难以置信。赛诗输了,竟然食不下咽。”
博雅由衷地叹息,喝了一口酒。
此刻,两人都是自斟自饮了。
博雅往自己的空杯里倒酒的同时,看着晴明说:
“哎,据说出来了。”
“出来?”
“忠见的怨灵跑到清凉殿上去了!”
“噢。”晴明的嘴角露出笑意。
“说是已有好几个值夜的人看见了。脸色煞白的忠见嘴里念着‘恋情’,在织丝般的夜雨中,哀哀欲绝地由清凉殿踱回紫宸殿方向……”
“很有意思呀。”
“你就别当有趣了,晴明。这事有十来天了。如果传到圣上耳朵里,他一害怕,可能就要宣布迁居。”
晴明也少有地严肃起来,频频点头,嘴里连连说“对呀对呀”。
“好,你说吧。博雅……”晴明忽然说了这样一句。
“说什么?”
“你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也该说出来了吧。”
“你知道了?”
“写在你脸上啦。因为你是个好人。”晴明带几分取笑,说道。
博雅却认真起来了。
“是这样,晴明——”他的腔调为之一变,“五天前的晚上,圣上心爱的玄象失窃了……”
“呵呵。”晴明手持酒杯,身子向前探出。
所谓玄象,是一把琵琶的名字。
虽说是乐器,但若是名贵的宝物,就会为它取一个固定的名字。
玄象原是醍醐天皇的秘藏,是从大唐传来的。《胡琴教录下》有记载:“紫檀直甲,琴腹以盐地三合。”
“到底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如何偷走的,一点眉目都没有。”
“的确伤脑筋。”
晴明嘴上是这么说,却看不出有什么为难的表示。
博雅似乎有些线索。
“前天晚上,我听到了那玄象弹奏的声音。”
三
听见玄象声音的晚上,博雅正在清凉殿值班。
此时的情况,《今昔物语集》有记载。
其人深通管弦,常为玄象失窃之事叹息。当日万籁俱寂,博雅于清凉殿上,遥听南面方位传来玄象之音。
警醒后再倾听,发现的确是玄象那熟悉的声音。
起初,博雅心想,难道是壬生忠见的怨灵因宫内歌会的事,怨恨村上天皇,于是偷走玄象,在南边的朱雀门一带弹奏?
又想,这是否幻听?再侧耳倾听,果然是琵琶的声音,绝对是玄象。他深通管弦,没有理由听错。
博雅深感诧异,没有告诉其他人,只带着一个小童,身穿直衣,套上沓靴就往外走。从卫门府的武士值班室出来,循着琴声向南面走,来到朱雀门。
但琵琶声听来仍在前方。于是,博雅从朱雀大路往南走。
如果不是朱雀门,该是前面的物见楼一带?
看样子不是忠见的怨灵,而是盗窃玄象的人爬上了物见楼,在那里弹奏琵琶。
可是,当抵达物见楼时,琵琶声依旧从南方传来,声音和在清凉殿上听见的一样大小,实在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是世间之人在弹奏。童子脸色变得煞白。
然后往南、再往南,一直走下去,不知不觉中,博雅来到了罗城门前。
这是日本最大的一座门。有九间七尺高,在昏暗的天色下,黑沉沉地巍然耸立。
不知何时起,四周飘起纷纷如雾的细雨。
琵琶声从城门上传来。上面昏暗不可辨。
站在城门下仰望,童子手中的灯光隐隐约约映出城门的轮廓。自二层起,昏暗吞没了一切,什么都看不见。
就在这昏暗之中,琵琶声不绝如缕。
“回去吧。”童子恳求道。
但博雅却是个耿直的汉子,既然已来到此地,就没有扭头逃走的道理。而且,那琵琶声多么美妙啊。
是迄今没有听过的曲子,它的旋律深深打动了博雅。
铮铮——
琵琶悄吟。
铮铮——铮铮——
哀艳的音色,如泣如诉。
“世上真的有隐没未闻的秘曲……”
博雅心中深深感动。
去年八月,博雅亲耳听到了琵琶秘曲《流泉》、《啄木》。
他是听一位名叫蝉丸、年事已高的盲法师弹奏的。与蝉丸交往三年,才终于听到曲子。
那时,在逢坂关上,有一位失明的老法师建庵居住。老者原是式部卿宫的杂役。
这位老法师就是蝉丸。据说他是演奏琵琶的高人,连如今已无人能演奏的秘曲《流泉》、《啄木》都通晓。
在吹笛子弹琵琶方面,博雅被公认为无所不晓。听了这种说法,博雅按捺不住地想听这位法师弹奏琵琶。
博雅甚至派人到逢坂关,对蝉丸说:
“此处如此不堪,莫如进京。”
意思就是说:这种地方怎么好住人呢?上京城来住如何?然而,蝉丸幽幽地弹起琵琶,以吟唱代答。
世上走一遭,宫蒿何须分
“这世上好歹是能够活下去的,美丽的宫殿、简陋的茅屋又有什么区别?最终不都得消失无踪吗?”
法师随着琵琶声吟哦的,大体就是这样的意思。
听了这些,博雅更加不能自拔。
“真是位风雅之人啊。”
他热切盼望听蝉丸弹奏琵琶。
老法师并非长生不老之人,连自己也不知哪天就要死去。若老法师一死,秘曲《流泉》与《啄木》恐怕从此湮没无闻了。太想听这两首曲子了。无论如何都要听。想尽办法也要听。
博雅走火入魔了。
可是,如果去见蝉丸,直接要求他“请弹给我听”,会令人不快。纵使弹奏了,也难说用了几分心思。
可能的话,最好能听到老法师自然而然、真心实意的弹奏。
这个耿直的人拿定主意,从那天晚上起,每晚都往老法师那边跑。躲在蝉丸的草庵附近,每个晚上都充满期待地等:今晚会弹吗?今晚会弹吗?
一等就是三年。
宫中值班之时脱不开身,除此之外,博雅的热情在三年里丝毫未减。
如此美丽动人的月夜该弹了吧?虫鸣之夜不正适合弹奏《流泉》吗?这样的夜晚总令人遐想,充满期待。
第三年的八月十五之夜,一个月色朦胧、微风吹拂的夜晚。
袅袅的琴声终于传来了,是隐隐约约的、只听过片段的《流泉》。
这回真是听了个够。
朦朦胧胧的昏暗之中,老法师兴之所至,边弹边唱:
逢坂关上风势急,长夜漫漫莫奈何
博雅闻之泪下,哀思绵绵——《今昔物语集》这样记载。
过了一会儿,老法师自言自语道:
“唉,今晚实在好兴致。莫非这世上已无知情识趣之人?今夜若有略懂琵琶之道者来访就好了。正可以聊个通宵达旦……”
听了这话,博雅不由得迈步上前。
“这样的人正在这里啊。”
这位耿直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一定是被欢喜和紧张弄得脸颊发红,但仍然彬彬有礼。
“您是哪一位?”
“您可能不记得了。我曾让人来请您去京城,名叫源博雅。”
“哦,是那时候的……”
蝉丸还记得博雅。
“刚才您弹的是《流泉》吧?”博雅问道。
“您很懂音乐啊。”
听见蝉丸既惊且喜的声音,博雅简直是心花怒放。
之后,老法师应博雅所愿,在他面前毫无保留地弹奏了秘曲《啄木》……
听着罗城门上传来的琵琶声,博雅回想起那个晚上的事。
此刻听见的,是更胜于《流泉》和《啄木》的妙曲。那奇妙的旋律令人哀戚已极。
博雅不禁心神恍惚。他久久地倾听着头顶的昏暗中传来的琵琶声。过了好一会儿,开口道:
“请问在罗城门上弹琵琶的是哪一位?琵琶的音色分明来自前天晚上宫中失窃的玄象。我今天晚上在清凉殿上听见这声音,为它吸引,来到这里。这琵琶是皇上的心爱之物……”
刚说到这里,琵琶声戛然中止,周遭一片死寂。
童子手中的灯火忽然熄灭了。
四
“于是,只好回去了。”博雅对晴明说道。
童子吓得直哭,浑身发抖,加上没有灯火,可想而知主仆二人都够狼狈的。
“那是前天晚上的事?”
“嗯。”
“昨晚呢?”
“说实话,昨晚也听见了琵琶声。”
“去了吗?”
“去了。这回是一个人去的。”
“罗城门?”
“嗯,自己去的。听了好一阵子琵琶,能弹到那种境界,已非人力所能为。我一说话,琵琶声又停了,灯火也灭了。但是这次我有所准备,马上点燃灯火,登上城门……”
“你上去了?上罗城门?”
“对啦。”
好一个勇往直前的家伙。
城门上不是一般的昏暗,完全是漆黑一团。假定对方是人,在你拾级而上时,忽然从上面给你一刀,那可受不了。
“结果,我还是放弃了。”博雅又说道。
“没上楼?”
“对。上到一半的时候,楼上忽然传来人语声。”
“人的声音?”
“类似人的声音。像人或者动物的哭声,很恐怖。”博雅接着说道,“我仰头望着黑暗的上方向上走,忽然有样东西从上面掉到我脸上。”
“什么东西?”
“下楼之后仔细看看,才知道是人的眼珠,已经腐烂了。大概是从哪个墓地弄来的。”
博雅说,于是没有心思再上去了。
“勉强上楼,导致玄象被毁就没有意义了……”
“那么,你要求我干什么呢?”晴明饶有兴趣地问道。
酒已喝光,香鱼也吃光了。
“今天晚上陪着我。”
“还去?”
“去。”
“圣上知道吗?”
“不知道。这一切目前都闷在我肚子里,还嘱咐童子绝不能向外说。”
“噢。”
“罗城门上的,应该不是人吧。”
“不是人的话,会是什么?”
“不知道。大概是鬼。总之,如果不是人,就是你的事了。”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虽然目的是取回玄象,但我实在很想再次听到那琵琶演奏啊。”
“我陪你去。”
“好。”
“得有一个条件,不知你……”
“是什么?”
“带上酒去。”
“带酒?”
“我想一边喝酒,一边听那琵琶演奏。”
晴明这么一说,博雅略一沉吟,看着晴明喃喃道:“行吧。”
“走吧!”
“走。”
五
这天晚上,有三个人聚齐了。
地点是紫宸殿前,樱树之下。
晴明是稍迟才现身的。他一身白色狩衣,足蹬黑色短靴,轻松自在,左手提一个系着带子的大酒瓶。右手提着灯,但看样子一路走来都没有点燃。
博雅已经站在樱树下面。他一副要投入战斗的打扮:正式的朝服,头戴有卷缨的朝冠。左腰挂着长刀,右手握弓,身后背着箭矢。
“哎。”
晴明打个招呼,博雅应了一声:“嗯。”
博雅身边站着一位法师打扮的小个子男人,背上绑了一把琵琶。
“这位是蝉丸法师。”
博雅将法师介绍给晴明。蝉丸略一屈膝,行了个礼。
“是晴明大人吗?”
“在下正是阴阳寮的安倍晴明。”
晴明语气恭谨,举止稳重。
“有关蝉丸法师您的种种,已经从博雅那里听说过了。”
他的言辞比和博雅在一起时要高雅得多。
“有关晴明大人的事,我也听博雅大人说过。”
小个子法师躬身致意。他的脖颈显得瘦削,像是鹤颈。
“我跟蝉丸法师说起半夜听见琵琶声的事,结果他也说一定要听听。”博雅向晴明解释。
晴明仔细看了看博雅,问他:“你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打扮出门的吗?”
“哪里哪里。今晚是因为有客人在场。要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哪至于这么郑重。”
博雅说到这里,从清凉殿那边传来低低的男声:
“恋情未露……”
一个苦恼的低语声渐近,夜色下,一个灰白的身影绕过紫宸殿的西角,朦朦胧胧出现了。
寒冷的夜风之中,比丝线还细的雨像雾水般弥漫一片。那人影似乎由飘浮在空中、没有落地的雨滴凝结而成。
“人已知……”
人影从橘树下款款而来。
他脸色苍白,对一切视而不见。身上穿着白色的文官服,头戴有髻套的冠,腰挂仪仗用的宝刀,衣裾拖在地上。
“是忠见大人吗?”晴明低声问。
“晴明!”博雅望着晴明说道,“他这么出现在这里是有原因的。不要拦他吧……”
晴明并没有打算用阴阳之法做些什么。
“本欲独自……暗相思……”
白色的影子消失在紫宸殿前,仿佛慢慢溶入大气般,和那吟哦之声一起消失了。
“好凄凉的声音啊。”蝉丸悄声自语。
“那也算是一种鬼啦。”晴明说道。
不久,有琵琶声传来。
啪!晴明轻轻击一下掌。
这时候,从昏暗的对面,静静地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
那位美丽的女子身穿层叠的丽裳,即所谓的十二单衣。她拖曳着轻柔的紫藤色华服,走进了博雅手中提灯的光线之内。
女子站在晴明跟前,白皙娇小的眼帘低垂着。
“请这位蜜虫带我们走吧。”
女子白净的手接过晴明的灯。灯火噗地点亮了。
“蜜虫?”博雅不解。
“怎么……你不是给经年的紫藤取了这个名字吗?”
博雅想起今天早上在晴明的庭院里所见的唯一一串紫藤花,盛开的鲜花散发出诱人的芳香。不,不仅是想起。那种芳香的确是从眼前的女子身上散入夜色之中,飘到了博雅的鼻腔里。
“是式神吗?”
博雅这么一问,晴明微微一笑,悄声道:“是咒。”
“真是不可思议的人啊。”
博雅边说边叹气。他看看把灯交给女子的晴明,又看看自己手中的灯。
蝉丸没有带灯,三人之中,手里提灯的只有博雅。
“就我一个需要灯吗?”
“我是盲人,所以白天黑夜是一样的。”蝉丸轻声说道。
蜜虫转过穿着紫藤色华衣的身体,在如雾的细雨中静静迈步。
铮铮——铮铮——
琵琶声响起。
“走吧。”晴明说道。
六
晴明提着瓶子,走在迷蒙的夜色、清冷的夜气中。
他不时将瓶子送到唇边,饮几口酒,似乎很享受这样的夜晚,还有幽幽的琵琶声。
“你也喝吗?”晴明问博雅。
“不要。”
博雅最初一口拒绝,但被晴明取笑他是否“怕喝醉了,箭射不中目标”之后,也开始喝起来。
琵琶声婉转凄切。蝉丸一边出神地倾听着琵琶,一边默默地走路。
“我头一次听到这曲子,好凄凉的调子啊。”蝉丸小声说。
“胸口好憋闷!”博雅把弓背上肩,说道。
“应该是来自异国的旋律。”晴明边说边把酒瓶往嘴边送。
夜幕下的树木很安详,绿叶的芬芳溶在夜色之中。
晴明一行人抵达罗城门下。
铮铮的琴声果然是从罗城门上面传下来的。三人无言地静听了好一会儿。
曲子不时变换。奏其中的某一支曲时,蝉丸低声自语道:
“这支曲子倒是有些印象……”
“什么?!”博雅望着蝉丸。
“已故的式部卿宫生前某天,弹奏过一支说是不知其名的曲子。我觉得就是这支。”
蝉丸从肩头卸下琵琶,抱在怀中。
铮铮——
蝉丸和着罗城门上传来的旋律,弹起了琵琶。
铮铮——
铮铮——
两把琵琶的旋律开始交织。
蝉丸的琵琶声开始时略显迟疑,但也许是传到了对方耳中,从罗城门上传来的琵琶声同样弹奏起那支乐曲。反复几次,蝉丸的琵琶声不再犹疑,几番来回,几乎已与城门上传来的琵琶声浑然一体。
绝妙的音乐。
两把琵琶的声音水乳交融,回荡在夜色中。铮铮,美得令人战栗。
蝉丸心荡神驰般闭上了失明的双目,在琵琶上奏出串串声音,仿佛正追寻着内心升腾起的某种东西。欢喜之情在他的脸上流露无遗。
“我真是太幸福了,晴明……”博雅眼含泪花,喃喃说道,“身为一个凡人,竟然能耳闻如此琵琶仙乐……”
铮铮——
铮铮——
琵琶之音升上昏暗的天幕。
有人说话了。
野兽似的低沉声音,一开始低低地混杂在琵琶声里,慢慢变大。
声音从罗城门上传来。原来是弹琵琶者边弹奏边哭泣。
不知何时起,两把琵琶都已静止,只有那个声音在号哭。
仿佛追寻着大气中残留的琵琶余韵,蝉丸将失明的双目仰向天空,脸上浮现出无比幸福的表情。
哭声中开始夹杂着说话声,是外国的语言。
“这不是大唐的语言。”晴明说道。
侧耳倾听了好一会儿,晴明忽道:“是天竺的语言……”
天竺即印度。
“你听得懂吗?”博雅问道。
“一点点吧。”
晴明又补充说,因为认识不少和尚嘛。
“说的是什么?”
晴明又细听一听,对博雅说:“是在说‘好惨呀’,还说‘真高兴’,似乎又在喊某个女人的名字……”
天竺语即古印度的梵语。佛教经典原是用这种语言写成,中国翻译的佛典多是用汉字对原典进行音译。
在平安时代,也有几个人能说梵语,当时日本也有天竺人。
“那女人的名字是什么?”
“说是悉尼亚。”
“悉尼亚?”
“或者西尼雅,也可能是丝丽亚。”
晴明若无其事地抬头望望罗城门。
灯光可及之处极其有限,稍高一点的地方已是漆黑一团。
上到城门的第二层,晴明轻声打招呼。他用的是一种异国的语言。
哭泣声戛然而止。
“你说了什么?”
“我说:‘琵琶弹得真好。’”
不一会儿,一个低低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
“你们弹奏我的国家的音乐,说我的国家的语言,你们是什么人?”
虽然略带口音,但毫无疑问是日语。
“我们是侍奉宫廷的在朝人。”博雅答道。
“姓名呢?”那声音又问。
“源博雅。”博雅说道。
“源博雅,是你连续两晚来这里吧?”那声音问道。
“正是。”博雅答道。
“我是蝉丸。”蝉丸说道。
“蝉丸……刚才是你在弹琵琶吗?”
当那声音问时,蝉丸拨动琴弦,“铮——”的一声代替了回答。
“我是正成。”
晴明这么说时,博雅一脸困惑地望向他。为何不用真实姓名呢?
晴明满不在乎地仰望着罗城门。
“还有一位……”那声音欲言又止,似是喃喃自语,“……似乎不是人吧?”
“没错。”晴明说道。
“是精灵吗?”那声音低低地问道。
晴明点点头。看来楼上是俯视着城门下面。
“请教阁下尊姓大名?”晴明问道。
“汉多太——”回答的声音很小。
“是外国名字吗?”
“是的。我出生在你们称为天竺的地方。”
“应该不是今世的人吧?”
“对。”汉多太答道。
“你的身份是什么?”
“我是游方的乐师。原是小国国王的庶子,因国家亡于战争,便远走他乡。自幼喜爱音乐多于武艺,十岁时便通晓乐器,最擅长演奏五弦月琴……”
声音里含着无限的怀旧之情。
“我抱着一把月琴浪迹天涯,到达大唐,在那里度过生前在一地停留最久的一段日子。我来到你们的国家,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我是搭乘空海和尚的船,来到贵国……”
“噢。”
“我死于一百二十八年前。我原在平城京法华寺附近制作琵琶等乐器,有一天晚上来了盗贼,我被那贼砍掉头颅而死……”
“那为什么你又会像现在这样?”
“我原想在有生之年再看看故乡。也许是久别故国,客死他乡的悲哀,使我死不瞑目吧。”
“的确如此。”晴明点头称是,又开口说道,“不过,汉多太啊……”
“请讲。”那声音回答。
“你为什么要偷走那把玄象?”
“其实,这把玄象是我在大唐时制作的。”
声调低沉而平静。
晴明长叹一声:“原来如此。”
“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吧。正成先生……”
那声音说道,叫的是刚才晴明所报的假名字。但是,晴明没有回答。
“正成先生……”那声音又说话了。
博雅看着晴明。晴明朱唇含笑,仰望着昏暗的城门。
忽然,博雅想起一件事来。他瞪着上方说道:
“那把玄象也许从前是你的东西,但现在已是我们的东西了。你能否把它还给我们呢?”
“归还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那声音很小,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不过,你们能否答应我一项请求?”
“什么事?”
“说来惭愧,我潜入宫中时,对一名女官心生倾慕。”
“竟有这种事?”
“我十六岁上娶妻,这名女官与我那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
“说来我是为那女官夜夜潜入宫中,因此才看见了那把玄象……”
“……”
“当然,我可以凭借鬼神之力将女官据为己有,可我却不忍心。于是退而求其次,拿走玄象,以怀念往者,怀念妻子悉尼亚,弹奏着琵琶抚慰自己的心灵。”
“那么……”
“请向那女子道此隐衷,请她过来一次。仅一个晚上即可。请她给我一夜情缘吧。若能遂我心愿,第二天早上她就可以回宫,我则悄然离开这里……”
言毕,声音似哀哀地哭泣起来。
“明白了。”博雅答道,“我回去将事情奏明圣上,若蒙圣上允准,明晚同一时刻,我会带那女子前来……”
“在下不胜感激。”
“那位女子有何特征?”
“是一名肤色白净、额上有黑痣的女官,名叫玉草。”
“若圣上准了,明天白天我将此箭射过来。若圣上不准,则射的是涂黑的箭……”
“有劳大人代奏。”那声音答道。
“对了。你——”
忽然向城门上搭话的人,是刚才一直没有作声的晴明。
“刚才的琵琶,可以再弹一次给我们听吗?”
“弹琵琶?”
“对。”
“在下求之不得。本应下楼演奏才是,但因容貌已是不堪,就在楼上演奏。”那声音这样说着。
铮铮——
琵琶声响起,不绝如缕,仿佛大气中有无数的蛛丝。比之前的演奏更佳,更令人如痴如醉。
一直伫立在旁的蜜虫轻轻一弯腰,把灯放在地上,又轻盈站起。微风荡漾的夜色之中,蜜虫白净的手臂轻轻抬起,和着琵琶的旋律翩然起舞。
博雅不禁发出惊叹。
曼舞和琴声结束。上面传来了说话声。
“真是美妙的舞姿啊!今晚请到此为止。为防万一,我还是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吧。”
“万一?”
“为了你们明天不会干出傻事。”
话音刚落,从罗城门二楼扫过一道绿光,照在蜜虫身上。
蜜虫被那道光罩住的瞬间,脸上现出苦闷的表情,双唇开启。就在要露齿的瞬间,光和蜜虫的身影都消失了。
地上的灯映照出一个飘动的东西,缓缓掉在地上。晴明上前拾起一看,是紫藤花。
“拜托诸位了。”
头顶上留下这么一句话,没有声音了。
之后,只有如丝的雾雨飘在万籁俱寂的夜空之中。
晴明右手白皙的指头捏着紫藤花,轻轻按在自己的红唇上,唇边浮现出宁静的微笑。
七
第二天晚上。
罗城门下站着四个人。
细密如针的雨从柔和昏暗的天幕落下。
晴明、博雅和另外一男一女站在细雨中。
男子是名叫鹿岛贵次的武士。他腰挂大刀,左手持弓,右手握着几支箭。他本领高强,大约两年前,曾用这把弓射*了宫中出现的猫怪。
女子就是玉草,年约十八九岁。大大的瞳仁,鼻梁高挺,堪称美人。
晴明打扮如昨。只是没有再带酒来。博雅的装束也没有改变,只是没有带弓箭。
琴声在四人的头顶上悠扬地奏响。四人默默地倾听。
不一会儿,琵琶声止住了。
“已恭候多时了。”说话声从头顶上传下来。
是昨天的那个声音,只是其中透出掩饰不住的喜悦。
“我们如约前来。”博雅对城门上说道。
“换了一个男人嘛。”
“蝉丸没有来。我们是守约的,但不知您是否守约,所以请了另一位同来。”
“是这样吗?”
“那么,女子可以给你,你可以交出琵琶了吗?”
“女子先过来。”那声音说着,从上面晃晃悠悠地垂下一条带子,“让女子抓住带子。我拉她上来,确认没错之后,就把琵琶放下来。”
“好。”
博雅和女子站到前面,让女子抓住带子。
女子刚抓住,带子便摇摇晃晃地往上升,转眼已升上了罗城门。她的身影消失了。
不久,“啊——”的一声传来。
“悉尼亚啊!”欢喜若狂的颤音,“就是她!”
不一会儿,带子绑着一件黑乎乎的东西再度从上面垂下。
“是玄象!”
博雅解开带子,拿着紫檀琵琶回到两人身边,将玄象给晴明看。
就在此时——
罗城门上响起一声可怕的喊叫,是那种咬牙切齿、充满痛苦的野兽的吼声。
“你们骗我啊!”
隐约听见一声钝响。紧接着,是女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
叫声忽然中断,从地上传来一股血腥味。
“玉草!”
晴明、博雅和贵次一起大叫起来,向城门下跑去。
只见地上有一片黑色的渍液。移灯细看,原来是鲜红的血迹。
咯吱,咯吱……
令人汗毛倒竖的声音自头顶传来。
咚的一声重重的钝响,有东西掉落地面——是一只连着手腕的女人小臂。
“糟糕!”贵次大声叫道。
“怎么了?”博雅扳过贵次的肩膀。
“玉草失败了!”
“什么失败了?!”
“我让她用带有比叡山和尚灵气的短刀,去割取妖怪的首级。她失败了。”
贵次边说边弯弓搭箭。
“玉草是我妹妹啊。我觉得,如果我的妹妹在明知对方是妖怪的情况下,还投怀送抱,是家门洗刷不掉的奇耻大辱……”
“是这样!”
博雅说话的时候,一道幽幽的绿光自罗城门射向昏暗的空中。
贵次用力拉弓,瞄准绿光中心射出箭。
“嗷!”随着一声类似犬吠的喊声,绿光落在地上。
只见一名全身赤裸、面貌怪异的男子站在那里。
那人肤色浅黑,鼻梁高挺。瘦高个子,精瘦的胸脯上肋骨清晰可见。额上生出两个尖突,像角一样,闪烁的眼睛睨视着三人。他嘴角向两边开裂,牙齿暴露,自己的血和女人的血把嘴巴周围染成猩红。身体自腰以下长着兽毛,下身是兽腿。
确实是一只鬼。
鲜血和着泪水,在鬼的脸上流淌。那充满憎恶和哀怨的双眼望着三人。
贵次射出一箭,箭头插入鬼的额头。
“不要这样!”
当晴明大叫时,鬼猛冲上前。它扑在正要再次射箭的贵次身上,利齿咬入贵次的咽喉。
贵次仰面而倒,箭矢射向昏暗的夜空。
鬼哀怨的眼神看着其余两人。博雅拔出腰间的长刀。
“不要动,博雅!”鬼大叫。
“不要动,正成!”鬼又对晴明说道。
博雅保持着拔刀的姿势,没有动。
“太伤心了。”鬼沙哑的声音喃喃道。呼的一下,幽幽的绿焰自鬼的口中飘出。
“伤心啊,伤心……”
每次说话,鬼的口中都有幽幽的绿焰荡到黑夜里。博雅的额头渗出冷汗。他右手持刀,左手抱着玄象,似乎想动也动不了。
“啖汝等之肉,与我玄象同归……”
在鬼这样说的时候,晴明开口了:“我的肉可不能给你啊。”
晴明的脸上浮现出恬淡的微笑。他迈步上前,从博雅手中夺过长刀。
“你这是欺骗我,正成!”鬼又惊又怒地说道。
晴明笑而不答。
即使被喊的是假冒的姓名也不行,只要对方喊出名字,而你答应了,就被下了咒。
昨晚博雅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而且被叫到名字时又答应了,所以被下了咒。晴明说的是假名字。
鬼顿时毛发倒竖。
“不要动,汉多太!”晴明说道。
毛发倒竖的鬼——汉多太定住了。
晴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长刀捅入汉多太腹部,鲜血涌出。他从汉多太腹中取出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是个活着的狗头。
狗头龇牙咧嘴地要咬晴明。
“原来是狗啊。”晴明自言自语,“这是鬼的真身。汉多太的鬼魂不知在何处找到一只濒死的狗,便附在它上面了。”
话音刚落,汉多太僵立不动的肉身开始发生变化。
脸孔变形,全身长出长毛。原先是脸面的地方成了狗屁股。屁股上插着两支箭。
忽然,博雅的身体可以自由行动了。
“晴明!”他发出一声高叫,声音在颤抖。
一只干巴巴、不成样子的无头狗倒在刚才汉多太站的地方。只有晴明手中带血的狗头还在动。
“把玄象……”
晴明一开口,博雅马上抱着琵琶过来了。
“就让它附体在这把没有生命的琵琶上好了。”
晴明右手抱持狗头,左手伸到狗头前面。狗头咬住了他的手,牙齿发出声响。就在那一瞬间,他松开右手,蒙住狗的两只眼睛。但是,啃咬着左手的狗头没有掉下来。
“把玄象放在地上。”晴明对博雅说道。
博雅依言把玄象放在了地上。晴明蹲下身子,把咬住自己左手的狗头放在玄象上面。被咬着的手冒出鲜血。他自上而下仔细打量那狗头。
“哎,听我说……”晴明和颜悦色地对狗头说道,“那琵琶的声音可好听了。”
他蒙住狗眼的手轻轻移开,狗的眼睛已经闭上了。
晴明从狗嘴里抽回手,血还在流。
“晴明——”博雅呼唤。
“汉多太在玄象上面附体了。”
“你施咒了?”
“嗯。”晴明低声回答。
“就是用刚才那句话吗?”
“知道吗,博雅?温柔的话,才是最有效的咒。如果对方是女人,会更加有效……”晴明说着,唇边浮着一丝笑意。
博雅仔细端详着晴明,喃喃地叹息:
“你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
玄象上的狗头,不知不觉间已变成白骨,是一具残旧发黄的狗的头骨。
此玄象如同有生命者。技巧差者弹之,怒而不鸣;若蒙尘垢,久未弹奏,亦怒而不鸣。其胆色如是。某次遇火灾,人不及取出,玄象竟自出于庭院之中。此等奇事,不胜枚举。众说纷纭,相传至今。
《今昔物语集》第二十四卷
《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 第二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