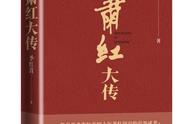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流行小说还是茅盾和巴金的作品的天下,萧红的出现给当时的场面带来了新鲜的空气。处在东北沦陷区的萧红所写就的《生死场》在抗战背景下振奋了民众的信心,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书籍再版达到15次之多。

图为萧红与萧军
《生死场》的成功不得不归咎于萧红自身独特的苦难经历,这是仅凭借概念创作所达不到的,这也是萧红创作的独特之处与难以超越之处。
在萧红的创作中,实感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于其文本之中可见一斑,萧红出生于1911年的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34年6月离开黑龙江前往青岛,而《生死场》便是在1934年写就的。
萧红自出生以来,在东北生活了二十三年,可以说她人生中的青葱年华都是在东北度过的,她把这种在东北生活的体验投射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比如说东北一大特点便是四季分明,而萧红的写作也常以季节为线索展开,这种规律和有着城市经验的张爱玲喜好以街道等场景展开故事类似。又如创作生死场的时候萧红已经有过了相对痛苦的妊娠体验,也对于女性在时代背景下某种程度上的集体性悲剧命运有了一番体悟与解读,她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这种生产体验投射进了自己的创作当中,在《刑罚的日子》一节中文本涉及到的麻面婆与金枝的生产过程的痛苦才能表达的淋漓尽致。萧红本人即是苦难的承担者,但她也是天赋的拥有者,这就如怀佩在身,是礼物,但也是惩罚,这让她不得不用笔于不止息的绵绵书写里,一再一再镌深伤口,鞭挞丑恶——她是注定要写出如此的杰作的。

虽然如此,但我们还可以发现,正如李欧梵曾在著述中提及过的,“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大多数的作家已经放弃了个人主义,他们写作的重心,特别是小说和戏剧,已逐渐地由对作者本身狭窄的个人经验转移到一个更宽广的社会现实上去(例如茅盾《子夜》中的整个上海,或是老舍、沈从文或萧红的乡村和地方)。”
其实在萧红的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注意到,萧红在《生死场》创作中也是有一个明显地从个人主义到社会现实的转变的,在《生死场》的前大部分都是在叙述萧红基于自身苦难来表达的乡村人民的生死挣扎,而后边风格陡然一变,从这种个人化的叙事转变为对时代大背景下中国东北人民抗战的叙述与表达,从而跳脱出来变成了一个较大的叙述格局,然而这其中或许有几分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的因素在。

《生死场》作为萧红个人体验下书写的生动作品,一方面吻合了当时民众的抗日心情,一方面表现出了人民的坚强与对于生存的强烈意志。在书中生命的血腥与野蛮、命运的无常反而激发出人们的生存意志,这也都激励到了当时的人们,可以说它是一部与读者相互成就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