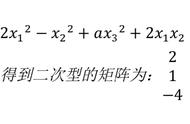金耀基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目前是该大学的社会学讲座教授。他长期专注于中国社会现代转向的研究领域,涉及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话题备受关注。看看金教授是如何理解转型期社会的“过渡型”人格
文 金耀基
“现在是过去之幼儿,也是未来之父母。”
要了解转型期社会,我们必须了解转型期社会的人,人是一切的根本。现在,让我们对转型期社会的人物做一分析。
转型期社会的人,社会学者冷纳称之为“过渡人”,他在“传统者”与“现代人”之间,设定了“过渡人”这个概念。“过渡人”是我们了解转型期社会的一把锁钥。所要说明的是,“过渡人”是指一种典型,一种概念构造,它只帮助我们了解转型社会中人的性格,但却不必是经验的描述。
“过渡人”的性格
过渡人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的人。一方面,他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不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另一方面,他既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由于转型期社会的“新”与“旧”的混合物,在这里,新旧两个“价值系统”同时存在。他一只脚踩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另一只脚还踩在旧的价值世界里。他不是静态的“传统者”,他是“行动中的人”。冷纳对“过渡人”曾有如此的描写:
“过渡人与传统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倾向’与‘态度’的‘潜在的结构’之别。他的‘倾向’是‘移情作用’——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他生活在传统者无法分享的幻想的世界里。他的‘态度’是一种‘*’——他真正想看到他‘心灵的眼睛’所看到的,真正想生活在他一直幻构着的世界里。”
冷纳说,假如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成为“过渡人”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了。
我们为了更使“过渡人”的画像清晰一点,我们可以借用理斯曼的大著《寂寞的群众》(The Lonely Crowd)中的三个“动机模式”作为分析的基础,这三个“动机模式”是人众的性格与社会之间的环扣,而此一环扣则由三种心理机构所型塑:“传统导向”“他人导向”与“内我导向”,理斯曼暗示社会的历史的发展程序是从“传统导向”到“内我导向”,再到“他人导向”的。
在理斯曼的分析中,“传统导向”的人的行为是以“习俗”“传统”为标准的。“他人导向”的人的行为则以他的“同侪团体”的规范作为标准的。而“内我导向”的人,则一方面,已经从传统的习俗中逐渐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对于他接触的团体的规范,他又没有“见贤思齐”之逼迫的需要。
理斯曼所说的“内我导向”,正是“过渡人”的特性。他一眼向“过去”回顾,一眼向“未来”瞻望;一脚刚从“传统”拔出,一脚刚踏上“现代”。由于他生活在“双重价值系统”中,所以常会遭遇到“价值的困窘”,在心理上,积极的,他对“新”的与“旧”的有一种移情感;消极的,他对“新”的与“旧”的也都有一种迎拒之情,这种价值困窘与情感上的冲突,造成了“过渡人”内心的沮丧与抑郁,所以,“过渡人”是痛苦的人。有的“过渡人”则由于对新旧价值失去信仰,而成为“无所遵循”的人,因此过渡社会常出现伪君子与真小人。
中国的“过渡人”之分析
中国的“过渡人”之出现是传统解体、新思潮涌现以后的事。
中国的传统经过西方文化猛烈的冲击,逐渐地暴露了她的弱点与缺点,儒家的价值系统在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中,一步步地丧失了她的吸引力。人众对以儒家思想为本的中国传统,由怀疑而动摇而开始绝情的扬弃。胡适之先生在1922年这样写道:
“反抗的呼声处处可闻,传统被抛弃一旁。权威已经动摇,古老的信仰遭到了损害……廉价的反偶像主义与盲目的崇新主义大量出现。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
李维亦有如下的观察:“若说古老的信仰已完全地清除是不然的。但是对整个古老信仰的动摇与松弛则异常明显。整个地说被摇撼了的旧信仰并没有被任何‘系统化的取向’所取代,知识分子间的一般倾向的崇拜之情虽已逐渐升高,但是并不普遍,也非深入。人们的一般趋向仍不清楚。古老的信仰,固然已松散,但仍看不到积极的信仰的涌现。”
的确,中国传统的“信仰系统”虽被西方的文化冲垮,但西方的“信仰系统”仍没有在中国人的心里生根,中国人已开始欣赏西方的价值,但是古老的传统的价值对他仍然有若*吸引力。作为一个“过渡人”,如前面所说,会遇到“价值的困窘”;作为一个中国的“过渡人”,则这种“价值的困窘”益形复杂,何以故?因为中国“过渡人”所面临的“价值的困窘”不只是“新”与“旧”的冲突,而且是“中”与“西”的冲突。一个人扬弃“旧”的价值而接受“新”的价值,固然需要冷纳所说的“移情能力”和一种“心灵的流动”,一个人要扬弃中国的价值而接受西方的价值,则还需要能解消一种“种族中心的困局”。
中国的“过渡人”一直在“新、旧、中、西”中摇摆不定。一方面,他要扬弃传统的价值,因为它是落伍的;另一方面,他却又极不愿接受西方的价值,因为它是外国的。他强烈地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像西方的现代的工业国家,同时,他又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他对“西方”与“传统”的价值系统都有相当的“移情之感”,但同时,他对这二者却又是矛盾犹豫、取舍不决的。这种情形,使中国的“过渡人”陷于一种“交集的压力”下,而扮演“冲突的角色”。有的成为深思熟虑“完善的自我”的追求者,有的则成为“唯利是图”而不受中西两种价值约束的妄人。
诚然,中国“过渡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认同”的问题,他们的“自我形象”是不稳定的,也不清楚的;他们的“自我认同”则困交于新、旧、中、西之间,这是两个文化发生“濡化过程”中的常有现象。中国“过渡人”所感到最焦烦的是找不到“真我”,最迷惑的是寻不到“认同”的对象;他们最大的努力是追求一种“综合”,即企图把中国的与西方的两个价值系统中最好的成分,融化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在某个意义上说,中国“过渡人”目前追求的“现代化”运动的工作就是这种心理上的要求。
从上面的分析里,我已陈示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冲击的影响,也已描绘了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画像。然而,中国的转型期社会虽然已经过渡了一百年,可是我们仍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转型期的现象即可过去。
事实上,进步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转型期社会(或过渡社会)也不必命定地可以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所以,约瑟夫·拉帕罗姆巴位认为“过渡”或转型期这个词语是有问题的,他说:“‘过渡’一词意指政治(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的达尔文的型模’,这个词语暗示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种变迁是朝着可认同的时期前进的。同时,演化的后期又必然地较之前复杂,而且优越。”里格斯就是因为“过渡”一词含有“目的论的意义”,故舍而不用,而另创“棱柱”一词。
的确,过渡社会是可以一直过渡下去的,转型期的现象是可以长留永驻的。但是,我个人仍然相信,只要工业化的速度能够加快,“过渡人”的“移情能力”能够加强,而“种族中心”的迷惘能够渐渐冲破,则中国的“过渡人”是可以变成现代人,而创造一个现代的社会的。
我喜欢,并相信下面这句话:“现在是过去之幼儿,也是未来之父母。”
(本文摘自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法律出版社)
稿件编审:吕斌 编辑:新媒体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