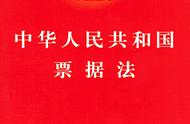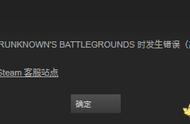图2
如果李四实在等不了3个月,他想立刻拿到钱,怎么办!很简单,应收账款本身也是一项“资产”,当然可以转让,李四可将这笔“应收账款”转让给王五。在李四和王五的转让行为中,标的物为“债权”,其实这跟买卖冰箱、彩电、汽车等物的性质类似,但最大的不同是,张三到期,到底向谁清偿?答案是向王五清偿。张三如何知道债权人从李四换成了王五?根据《合同法》规定,“李四”转让债权时,必须履行“通知”义务,即,将债权转让的消息告诉张三,让他到期直接还款给王五,至此,该债权转让行为才对张三发生法律效力。
债权转让是天大的好事,可帮助李四解一时燃眉之急,但这也带来一个麻烦的程序,就是李四需要履行通知张三的义务。但更大的麻烦在后面……

图3
这个大麻烦可能会发生在王五身上。假设李四违约没有向张三发货,张三便可以拒绝向李四付款,这个拒绝付款的权利在法律上称为“抗辩权”。但债权此时已让与至王五,张三是否能以“李四未发货”为理由,拒绝向王五支付价款?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答案是可以!张三对李四的抗辩权,不会因债权转让而消灭,还会甩锅至王五,即李四不发货这件事,张三可向王五行使抗辩权,拒绝支付到期款项。
下面问题来了,如果你是王五,你敢不敢要这债权?
王五是否敢要,取决于“人与人的信任”。假设我们站在王五的视角,首先,我们应信任张三与李四之间的贸易往来是真实的,不是两个人以虚假合同来诈骗;二是我们信任李四会向张三发货;三是信任张三会到期付款给我们,不会拒付。
以上三个信任同时满足,王五才敢要这笔债权。那如果不信任怎么办?这笔交易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你根本就观察不到,亦或是王五拿到一笔满意的风险折扣,比如支付给李四90万元,换回100万元的应收账款,差价10万元权当风险补偿。
我们可以把这笔债权继续流转下去,如图:

图4
王五将该债权转让给赵六,依然要履行通知义务,同时张三对李四的“抗辩权”依然剪不断理还乱,张三仍可以将其溯及至赵六。由于李四与赵六“相隔甚远”,赵六对最初的合同履行情况更无法知晓,他或许可以勉强接受,但一定会索要一个更大的折扣,这笔债权在他眼中,其实是不值钱的。
基于“人与人信任关系”的债权流通,一定会在很小的范围内停下来,无法再继续下去,因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来越高,最终导致基础债权是否真实的审查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没人敢要这烫手山芋。
在“债”的法律关系中,为了利益均衡,债权流转严格受到“抗辩权”和“通知”两项制约,这必然限制其流转的效率。如果没有信任,就不可能存在贸易活动,但是要相信陌生人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就算是大批互相不认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讨论一件事,一定要有一个“共识基础”,比如一个人考CPA,另一个人考CTA,双方就税法和财务会计部分,就有一个共识的地基,能够愉快的讨论;但是,如果一个人考CPA,另一个人考ACCA,虽然都是财务类考试,但双方共识就很少了,毕竟考试语言都不通;再进一步,如果一个人考CPA,另一个人从小到大没考过试,双方的共同点,可能就是如何多生孩子多挣钱。这里我们讲的道理,是成百上千万自私利己的人聚在一起,却能把一件事情的规模做到极致、做到最大化,那么必然存在一个基础基础再基础,“最最基础的共识”。
我们要把“债权转让”这种商事活动做到极致,那最底层的Lv0是什么?
“信贷资产证券化、应收账款票据化”
为此,我们可以完全跳出债法的体系,重新设计另外一套“世界观”、重新编造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把“认人”转化为“认故事”。人类商品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正是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大家都“认钱”的共识造就的。在无数的商人、金融家与法学家的努力之下,票据与票据法也就应运而生了。大家拍手称快!千古难题就此解决。世界贸易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不就是这么来的么!
单就法律来讲,票据法解决的主要问题便是债权流转效率的“技术性”问题,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票据法建立在传统债法之上,基础民事权利为“骨”,票据权利则为“肉”。

图5
若把上面张三与李四的例子,从“债”转化为“票据”,画风立刻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