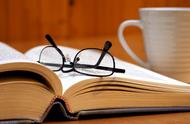作者 | 唐小林
摘 要
虚构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能力。迄今为止关于虚构本质的讨论,大致超不出实在论、制度论和传播论这三个论述方向及其复杂关系。实在论是在虚构对象或虚构叙述中,找出其区别于真实对象或纪实叙述的实在属性,并将其作为虚构的本质。制度论却把虚构的本质归因于社会文化规约。基于传播论的双层区隔原则,由于透彻地揭示了虚构的本质及虚构世界的构成,在解决虚构本质问题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所引发的争论,实质是传播论视域下实在论与制度论的冲突。因此,如何处理好实在论、制度论、传播论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实现三者的融通,是推进虚构本质讨论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虚构的本质; 实在论; 制度论; 传播论;双层区隔原则;
一、虚构无解?
笔者认为,虚构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人类是使用“符号的动物”这一理论设定。[1]语言符号使人类能够谈论未曾亲见的事物,比如过去、现在和将来;也使其能够想象那些“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事物”,比如灵魂、魔鬼和梦想。[2]“讨论虚构的事物”的符号本性,[3]往往以虚构叙述的方式表现出来。虚构叙述不仅将分散的个人连接为“类”,使人类虽“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4]立于地球食物链顶端,还将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比如自然—生物、社会—文化、思维—实践等各个层面连接起来,形成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5]在此意义上,虚构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认识虚构乃是认识人类的重要途径。
虚构虽然日常,可一旦进入理论领域,追问其本质,却变得相当困难。所谓本质乃是事物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你是什么,就你的本性而言,乃是你的本质。”[6]就此而言,虚构的本质,就是使虚构成其所是之物。如果把虚构对象看作典型的非存在物,西方对虚构的讨论大致始于柏拉图的《智者篇》,而真正形成热潮则是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情。笔者就现有的文献来看,迄今为止关于虚构本质的讨论,大致超不出三个方向:实在论、制度论和传播论,而且其创新和问题都逃不出这三者及其复杂关系。
实在论有两种主要论述方式。第一种论述方式是在虚构对象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展开,它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像福尔摩斯、贾宝玉、阿Q这样的虚构对象,“属于我们现实世界”,[7]2他们都是真实的、现实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具体的,“但却是非存在的”。[7]53比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主题为“神奇的生物:龙、独角兽和美人鱼”的大型展览,其展品都是自然界中并非实际存在的生物,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展览大厅,它们不过是“非存在的存在”。“非存在的存在”这一表述之所以看似自相矛盾,只是因为我们是在“一种极为常见的意义”上使用“存在”这个词。[8]在此实在论视域下,“非存在的存在”即虚构的本质。
实在论的第二种论述方式,致力于在虚构对象或虚构叙述中找出其区别于真实对象或纪实叙述的实在属性,并将此实在属性作为虚构的本质。这种实在论,将虚构/真实、虚构叙述/纪实叙述作为对立与对举的概念,相信实际存在于虚构对象或虚构叙述中的属性要素,是区分虚构与纪实的标准。如果第一种实在论是在虚构世界与实在世界这两个不同世界的“垂直”关系中去寻找虚构的属性要素,那么这种实在论却只在同一个世界即虚构世界中去辨识仅属于虚构的独特标识。笔者将这种实在论大致分为“字面实在论”和“文本实在论”两类。
字面实在论,在这里还包括指称论,把虚构的本质限定在语境中为真以及有意义的空名的范围内。字面实在论认为,[7]31像阿Q“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这样的句子在字面意义上是真的,它之所以为真,是因其“故事所说的内容为真”,[7]2这种真不是“绝对的真”,而是“预设的真”。指称论虽依据名称语义学,却走着相反的路,认为像“阿Q”这样的虚构名称,是一个有意义的空名,即“无指称物的指称”,[7]46即如古德曼(Nelson Goodman)所说的“零指谓”。比如,匹克威克(Pickwick)或独角兽的图像以及凡·高的《邮递员》,虽然“没有再现任何东西”,却是有所指谓的。[9]
文本实在论,是在比较虚构叙述与纪实叙述的文本构成方式中指认虚构的实在属性要素。其主要工作是“指出叙事文的虚构特征或‘纪实’特征可能对其时态变化、观察距离和视点之选择或叙述‘声音’之选择,还有……叙述者和作者两个言语机制在叙事文中的关系,产生的可预见的结果”,[10]83以建立所谓虚构的“本质论诗学”,确定某些叙述文本“本质上”“实质上”永远属于虚构而非纪实文本。小说是公认的虚构体裁,因此,小说叙述学所揭示的其在叙述主体、层次、时间、方位、情节等方面的种种特征,即是其虚构的各种实在属性要素。比如:“构成叙事的‘原始之我’的人物都是想象和虚构出来的”;[10]135作者与叙述者分离;小说作为虚构文本,“绝不引导到文本外的任何真实”,具有“不及物性”;[10]106其“陈述句以论断形式出现,却不具备论断形式的条件,是强装之论断”;[10]113“元故事叙事的出现是虚构性的一个比较可靠的标志”;[10]138“叙述事件的行为、描述人物的行为和参照地点的行为是虚构的”;[10]140等等。而纪实叙述,诸如历史、日记、新闻、通讯、法庭证词等,则不具备这些实在属性要素。
与实在论总是在虚构对象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在字面、指称以及文本构成方式的实在属性要素中寻求虚构的本质不同,制度论却把虚构的本质归因于社会文化规约。制度论是朴异汶(Yeemun Park)受丹托(Arthur C. Danto)“艺术界”理论和迪基(George Dickie)“艺术惯例论”的启发而提出的。它基于这样的预设:“对于任何事物现象未必都能给出实在的定义。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其现象的存在论结构而无法从时空的维度或者从实在的功能这一层面上得到理解……它们只有依据制度的属性这一非可视性属性要素才得以规定和界定。”[11]51比如,一个人已婚未婚并不能从生理层面得到说明,而是看其是否满足了制度性要求。作家纪德(Andre Gide)婚后从未与妻子同居,妻子在生理上仍然是处女,却不能因此认定为未婚者。相反,萨特与波伏娃同居五十多年,比夫妻还要亲密,但他们依旧属于“制度”上的未婚者。就虚构的本质而言,实在论侧重于“虚构之所是”的物质、物理或可感知层面;制度论则侧重于“虚构之所是”的观念、文化或非感知层面。这里的制度“可以解释为逻辑条件的含义”。[11]63
制度论可以说是对实在论的否定,认为其不能解决虚构的本质。不过,这种否定首先来自普遍的“反实在论”。“关于虚构的反实在论者宣称:不存在实在的虚构对象;或者,至少我们没必要为了解释虚构而假设存在实在的虚构对象。”[7]135罗素(Bertrand Russell)主张“哲学不能仅仅关注存在的事物”,[7]52也曾对持实在论的“迈农主义”给予理解,认为它“会对哲学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结果”,[7]61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反实在论者,并以“违反矛盾律”拒斥了迈农的理论。[7]62即便在实在论内部,也在不断地质疑、解构和重构已有的理论。比如徐敏立足于“形上学”(Metaphysics)的两个基本问题,[12]7所提出的“合取创造主义”,虽然被认为是“当代华人世界哲学家第一次对虚构对象所提出的哲学理论”,[12]序1-3却不敢“断言该理论是正确的或者唯一正确的理论”,因为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理论”。[12]296
文本实在论同样遭到致命的否定,文本特征不被认为是辨别虚构的标准。塞尔(John R. Searle)指出:“不论是从句法还是从语义的角度来说,都没有哪个文本特征能够明确说明某个文本是不是虚构作品。”[13]87热奈特(Gérard Genette)除极少保留外,也逐一否定了叙述文本的时序、速度、频率等是区分虚构与纪实的实在属性要素。他认为,“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在使用时序错乱以及表示这些错乱的方式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10]133在叙述速度、频率上,这“两种类型之间没有任何先验性的差异可言”;[10]134时态和人称也没有什么“先天性的区别”;只是在叙述层次上,“纪实叙事背弃大量使用二级叙述的做法”。[10]138即便是热奈特强调叙述语式原则上“确能揭示叙事的纪实特征或虚构特征,是区别两种叙述类型的显示剂”,[10]137在笔者看来也还有辩论的余地。按照热奈特的论述逻辑,如果主观化的“内聚焦”、客观化的“外聚焦”和排除主客观的“零聚焦”这三种叙述语式,都只适合虚构型叙述,那么纪实型叙述就根本不可能。
既然虚构的本质不在虚构对象或虚构文本中,那么它就不是一种客观实在,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契约,毋宁说它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塞尔认为,“虚构之所以被大家接受,是因为有一系列语言学之外的非语义常规”,打破了话语规则“所建立的词与客观现实的关联”,“应当将虚构性话语常规视为一系列横向常规,而这些横向常规打破了由纵向常规建立起来的关联”。[13]87-88对于“横向常规”是什么,塞尔语焉不详,却指出了明确的路标:“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讲故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单独的语言游戏;要玩这种语言游戏就必须有一套独立的常规,但这些常规并不是语言规则方面的常规”,[13]88而是在这个游戏场域内自己约定俗成的规则。热奈特也发现几乎相同的情况:“虚构的所有‘标志’并非都属于叙述学范畴,首先因为它们并非都属于文本范畴:更常见、也许愈来愈常见的情况是,一部虚构文本以副文本方面的特征为标志,它们可以使读者避免任何误解,扉页或封面上的体裁标志‘小说’即是众多副文本标志之一例。”[10]147热奈特把判定虚构与否的标准交给文本以外的“副文本”,交给出版商印在“扉页或封面上的体裁标志”,实际上就是交给了广义上的丹托之“艺术界”和迪基之“艺术圈”,交给了卡勒所谓的“约定俗成的自然”,即如那些以“体裁程式”出现的“文学惯例”,[14]一种制度性的因素。
制度论可靠吗? 赵毅衡认为不可靠,在他看来,“热奈特的话,实际上是宣判虚构标准问题无解,因为许多作品并不注明‘虚构’,中国出版界至今封面不加‘小说’两字”。[15]68赵毅衡不仅否定了制度论,也从“风格形态”“指称性”等方面部分地否定了实在论。[16]也就是说,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实在论和近半个世纪的制度论都不能解决虚构的本质问题,倘若不另辟新路,虚构无解。
二、双层区隔:一个重大突破?
为创立广义叙述学,赵毅衡引进传播论,试图融通实在论和制度论的合理因素,他提出的“双层区隔”原则,是解决虚构本质的重大理论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留下了可供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传播乃是“人们通过普通的符号系统交换彼此的意图”。[17]一个传播活动的最简图式由发送者、文本和接收者三个环节构成,落实到叙述行为,比如小说,则是由作者、作品和读者构成。所谓传播论,即是从这三个环节入手考察虚构本质的一种论述方式。当然并不是每个传播论者都能完整地照顾到这三个环节,有的因其具体论域或语境所限,只着重其中的一个环节。塞尔的《虚构性语篇的逻辑状态》即是依据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侧重于作者意图的考察。他从不同于“言内行为”“言后行为”的“言外行为”分析虚构性语篇的本质,而言外行为“基本上属于词语交际”,[18]可看成是广义的传播论。塞尔不同意“柏拉图认为虚构由各种谎言构成”的观点,[13]82认为虚构是作者的虚构意图所为,是作者的假装断言,即“虚构作品的作者假装实施一系列言外行为,这些言外行为通常是断言”,它是“一种非欺骗性假表演行为”。[13]86具体地说,“作者通过假装指称某人并叙述与他们有关的事件,创造出虚构人物和虚构事件”。[13]95塞尔的“作者假装断言”说及其所运用的言语行为理论,对后世探寻虚构的本质影响深远。2014年出版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指出,言语行为理论“能够最深入地阐明文学虚构问题”,[19]4对塞尔等人的学说“换一种说法”,即“可以对文学虚构做出较为明晰的界定”:“文学虚构是话语施为意义上构建虚构世界,而非表述意义上的虚构。”[19]247话语只对接收者施为,文学虚构就只能在接收者那里达成,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传播论的论述方式。
笔者认为,传播论已经超出叙述学的范围。无论如何,经典叙述学是将叙述文本外的实际作者和实际读者排除在外,而代之以叙述者、受述者或与之相应的其他名称。所以热奈特在论及叙述语态时才遇到了“一向棘手的叙述者与作者之关系问题”,因为他“不能自信还停留在叙述学的范畴内”。[10]138热奈特一向的警醒是有道理的,但换一种思考或许更有意义:如果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比如传播论的方式,把叙述文本的实际发送者和接收者引入叙述学中,势必会带来叙述学的革命,突破其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赵毅衡就是这方面卓有成效的开拓者。
赵毅衡关于叙述的“底线定义”就是在传播论的框架中做出的。叙述即是“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15]7这个底线定义字数不多,却包含了传播的三个基本要素:发送者、文本和接收者,也包括了一个有效传播必备的两次叙述。一次叙述发生在文本的构成过程中,是发送者主体在文本内部对“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的叙述。二次叙述则是发生在文本的接收过程中,是接收者主体在文本外部对“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的叙述文本的再次叙述。两次叙述不仅完成了一次传播过程所应有的编码和解码的全部活动,而且还以“叙述”为中心将发送者与接收者、叙述文本的内部和外部沟通起来。这个叙述定义完全不同于此前经典叙述学的有关定义,比如不同于只在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打转的普林斯(Gerald Prince)的定义,[20]也不同于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只在故事与话语的二维结构中展开的叙述定义。[21]叙述定义在传播论视域下的突破,为赵毅衡创立广义叙述学找到了新的基础,也为其在叙述学领域探索虚构的本质找到了新的路径,同时还立竿见影地破解了一些叙述学难题。比如其中的二次叙述,就巧妙地回答了单幅图像能否叙述的问题,也顺手解决了各种复杂文本的意义重建问题,以及不可靠叙述的可靠性是如何获得的等悖论性问题。
正是在传播论视域下,赵毅衡提出了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原则。他认为:“纪实叙述体裁的本质特点,不在文本形式,也不在指称性的强弱,而在于接收方式的社会文化的规定性:读者可以要求纪实叙述的作者提供‘事实’证据……虚构型与纪实型叙述的区别,在于文本如何让读者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体裁。”[15]72假如读者明白了体裁,也就明白了这个叙述文本是虚构还是纪实:如果是戏剧、电影、小说、绘画、音乐等,那就是虚构;如果是日记、历史、回忆录、法庭证词、纪录片、写真等,那就是纪实。而读者之所以明白,其所遵循的就是双层区隔原则。
所谓双层区隔原则,就是“用双层框架区隔切出一个内层,在区隔的边界内建立一个只具有‘内部真实’的叙述世界”。[15]73“一度区隔是再现框架,把符号再现与经验世界区隔开来”,[15]74“其中的符号文本是‘纪实型’的,直接指向‘经验事实’”。[15]75“二度区隔”是“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是“在符号再现的基础上再设置第二层区隔”,“这个框架区隔里的再现,不再是一度媒介再现,而是二度媒介化,与经验世界就隔开了双层距离”,[15]76其中的符号文本就只能是虚构叙述了。在抽象的意义上,“一度区隔的再现是‘指称透明’的”,[15]77可以在经验世界中求证;二度区隔是“不透明”的,“已经不能按框架外的‘经验实在’标准来衡量”,[15]79而只能依据塞尔之文本内部的“横向惯例”即“横向真实性”而自成“真实性”了。[15]82赵毅衡举了霍尔(Stuart Hall)《表征》中的“杯子”的例子来说明双层区隔:“我看到某人摔了一个杯子,这是经验。我转过头去,心里想起这个情景,是心像再现;我画下来,写下来,是用再现构成纪实叙述文本;当我把这个情景画进连环画,把这段情景写进诗歌小说,把这段录像剪辑成电影,就可以是虚构叙述的一部分,它可以不再纪实,不再与原先握在手中的那个杯子对应。”[15]76这样,杯子就经历了双层区隔,从经验到纪实再到虚构。而其中的区隔框架,只“是一个形态方式,是一种作者与读者都遵循的表意—解释模式,也是随着文化变迁而变化的体裁规范模式”,[15]74它是作者与读者所达成的契约:一种社会文化的约定俗成。比如一场球赛用哨声来区隔,一台演出用舞台或幕布来隔开,一部电影用演职员表来隔断,等等。赵毅衡确信:“没有无区隔的再现文本,也没有无二度区隔的虚构文本。”[15]78
纵观学术史,笔者认为,赵毅衡双层区隔原则在解决虚构本质问题上具有三个方面的重大理论贡献,其一:借助双层区隔的理论想象,明确回答了虚构的本质是文本内部的“横向真实”,这不仅发展了塞尔的话语“横向常规”理论,而且将虚构与纪实第一次如此清楚地区别开来:虚构只需建立在文本的“内部真知”上,而纪实还需依托文本的“外部真知”,即还需“符合客观事实”。两个真知符合论的提出,又使赵毅衡创立了“真知文本”理论,[22]264并在此基础上,将文本融贯论从“文本内”推向“文本间”[22]267“文本与体裁”之间[22]265,构建起“以纪实型为基本形态的”整个意义生产的文本互动网络。[15]88其二:立足双层区隔原则,彻底解开虚构本质的神秘面纱,第一次对虚构世界做出如此透彻的描述:它是一个“可能世界与三界通达”的世界。[15]176纪实的基础语义域虽然在“实在世界”,“却并不避免进入可能世界”;虚构的“基础语义域必然是可能世界,而且必然需要寄生于实在世界,却可以卷入不可能世界”。[15]196虚构本质与三界通达,尤其具有当下和未来意义,它为解开正在到来的以虚拟为核心的“元宇宙”之谜,率先提供了理论武器。其三:虚构的双层区隔原则,是传播论与叙述学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不仅是元媒介、元传播时代的内在要求,更显示其前所未有的学术统合力。这种统合力,源于传播论不是把虚构看成某个叙述主体、叙述对象、叙述媒介等某个单一环节,而是看成一项完整的意义传播或交流活动。这就意味着,它可以整合迄今为止包括实在论、制度论在内的所有学术资源,解决探求虚构本质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
三、 虚构的本质锚定何处?
问题可能正是出在用传播论统合实在论和制度论上,双层区隔原则提出不久,便引起王长才的质疑。王长才问:两度区隔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 文字类叙述的一度区隔框架在哪里? 二度区隔的性质是什么? 区隔框架与叙述者框架是重合的吗? 辨识真实或虚构是区隔框架在先还是虚构作品在先? 是否可能存在着多度区隔? [23]王长才问题的核心在笔者看来,并不是双层区隔原则本身,而是区隔框架中的实在论问题,即叙述文本尤其是文字类叙述文本中真的存在区隔标识吗? 如果有,制度论又是如何统合这些实在论要素的?
谭光辉对王长才的问题给予了创造性的长篇回应。在他看来,两度区隔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是“虚构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关联”问题。“虚构叙述虽不具有现实指称性,但可以经历从经验到纪实再到虚构的转化,对虚构叙述的接收最终必然还原为感知经验。虚构叙述是‘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并非再现两次必然为虚构,而是虚构必然被再现两次,必然与经验世界隔两层。”[24]97而且,“二度区隔只能建立在一度区隔的基础之上,没有一度区隔的符号文本,就不可能存在虚构,甚至不可能存在虚构的冲动”。[24]99文字类虚构不是没有一度区隔框架,而是它作为“构思过程”形成的“纪实文本”可以写出来,也可以不写出来,“一度再现可以缩得很短”,甚至完全不见。“下笔”“收笔”“翻书”“合书”等叙述和接收行为,则可以看成文字类叙述的二度区隔框架。在此,两度区隔的逻辑关系被转换为:纪实是虚构的逻辑起点,感知经验是纪实的逻辑底座,虚构虽然最终指向感知经验,却不可能从感知经验一跃而成为虚构。虚构不是绕不过纪实,而是绕不过感知经验符号化、文本化这一环节。
关于二度区隔的性质,谭光辉持赵毅衡的观点,它是“再现中的进一步再现”。它“不是判断虚构的充要条件,却是必要条件”。[24]100二度区隔作为“再度媒介化”与一度区隔作为“一度媒介化”的本质性区别表现在:“一度区隔的再现者处于实在世界之中,二度区隔的再现者处于叙述文本的一度区隔之中。一度媒介化是对实在世界中的‘现实’的媒介化,媒介化的产物是‘符号’,二度媒介化是对文本世界中的‘符号’的再媒介化,媒介化的产物是‘符号的符号’”。[24]100
这段论述十分精彩,却超出笔者对叙述学和符号学的某些认知,可能被误读。比如一度区隔的再现者如果是叙述者,哪怕在理论上它与实际作者同一,也不应该在“实在世界”之中,而只能在叙述文本里,否则它就将被叙述学排除在外。再比如二度媒介化的产物如果是“符号的符号”,那就等于说它是元符号,而按我们的常识,哪怕是虚构也不都是元符号。纪实与虚构的关系,也不是符号与元符号的关系,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也不会是符号与元符号的区别。
谭光辉的回应在王长才看来,并没有解决双层区隔如何在具体情境中作为标准对虚构和纪实做出准确的判断;并没有解决“为何虚构框架必然建立在纪实基础之上,或者说二度媒介化构成虚构的‘进一步再现’,这和第一次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纪实叙述是否是同一性质? 如果是同一性质,如何能说明两次再现就一定构成虚构”的问题;[25]211更没有解决“‘双层区隔’是附着于文本自身的客观存在呢,还是基于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主观认定”这一关键问题。[25]214该回应之所以不能让王长才满意,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他没有“直面”或者“绕过”了王长才所触及的区隔框架中的实在论问题,而是处处用制度论来“补救”,有时甚至有些“强词夺理”。比如,他明确谈到区隔框架与叙述者框架是同一的,但在回答辨识真实或虚构是区隔框架在先还是虚构作品在先时,他却认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只是一个“应用型问题”“操作问题”,不应该在双层区隔原理的层面来讨论。[24]102又比如,谭光辉承认存在多度区隔,且与叙述层次相关,但他又认为讨论过多的区隔层次“没有意义”,“最终只能简化为双层区隔”,[24]104至于其中的原因他并没有说明。再比如以下一些说法:“双层区隔原则……读者才是核心。”“判断一个文本是否是纪实,既不是依据是否是‘事实’,也不是依据是否‘真实’,而是依据该文本的表达与接受是否约定‘有关事实’。它只是一个文化程式的约定,而不是真实性判定,更不是事实性判定。”“理解虚构叙述的关键,就是对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非现实存在性’的约定……‘虚构约定’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论是作为区隔框架,还是作为叙述者框架,其实都是解释性的。”“文化程式与阅读经验在理解纪实与虚构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如果文化程式的惯例被打破,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纪实与虚构。”[24]98-102
笔者不禁要问:既然虚构的本质只是叙述方与接收方的一种“约定”,只是文化程式与阅读经验的一种“惯例”,那跟文本中的“双层区隔”有何相干? 更何况“区隔框架”也“都是解释性的”,“读者才是核心”,那“双层框架”的客观性又何在? 既然“双层框架”只活在“约定”和“解释”当中,它怎么会是文本中的一种“实在”? 既然不是文本中的一种“实在”,它又怎能在文本中找寻和找到? 谭光辉越为双层区隔原则辩护,结果越适得其反,这就像他最后为文章作结论所引用的伊瑟尔的那句判词一样:虚构的“功用是变化着的,而虚构与其变化着的功用相一致,所以它没有永久不变的本性,因为功用表明功能而不是基础”。[26]既然虚构没有本性,那又何来、何需用双层区隔原则来确定其本质?
文本的区隔框架本来是个实在论问题,但出于与上面相同的论述逻辑,最后必然消融在制度论中,就如区隔框架的大多数实在论例子,总是被装进制度论的套子。即如前面提到的霍尔杯子的例子:“当我把这个情景画进连环画,把这段情景写进诗歌小说,把这段录像剪辑成电影,就可以是虚构叙述的一部分,它可以不再纪实,不再与原先握在手中的那个杯子对应。”问题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段情景“画进连环画”,而不是拍成写真集? 为什么一定要写进诗歌小说,而不是写进日记或回忆录?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段录像剪辑成电影,而不是剪辑成纪录片或新闻联播? 再比如,裁判的哨音隔断练球进入比赛是虚构,是因为比赛已经等在那里,就像幕布拉开演员入戏是虚构,是因为戏剧已经等在那里,如果是信号弹升起进入实际战斗呢? 同样有隔断,它还是虚构吗? 当然不是,它是现实生活。
因此,在笔者看来,引发双层区隔原则争论的实质,是传播论视域下制度论与实在论的冲突。双层区隔不能理解为一种实在论,区隔框架也不能理解为文本中作为本质属性的某种客观存在。说到底,它们只是外在于文本的一种制度性存在,源于某一文化社群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约定俗成,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当然它也会在文本中留下一定的痕迹。对此,赵毅衡有着清醒的自觉,他不止一次指出,我们“不可能把这种区隔绝对化,因为任何符号都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规约性,也就是约定俗成的意义解释”;[15]80“虚构文体本身并没有与其他叙述相区分的明确标记”,“虚构叙述是靠符义,而不是靠符形与纪实型叙述相区分的”。[15]192-193事实上,赵毅衡的符号学和广义叙述学都是建立在传播论视域下的制度论基础上的。比如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27]这个“被认为”不是被哪一个接收者认为,而是被一个文化社群所认为,也就是被一种文化程式所认为。某物是不是符号,不是一种客观实在,而是一种制度性判断。符号的存在也因此是一种制度性存在。
笔者认为,实在论更应该是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金、木、水、火、土、空气等这样一些自然物,其本质属性是一种客观实在,但对于像虚构与纪实这样的文化物,制度论更为有效。因为它们只能是一种制度性存在,倘若有其本质属性,也只存在于一种关系之中、一种认知之中,当关系变了、认知变了,是虚构还是纪实也就跟着变了。这就如神话,对于初民是纪实,对于今人是虚构;亦如宗教经典对于教徒是纪实,对于非教徒或异教徒则纯属虚构一样。这不是说实在论无用,而是说假如有一种实在论,那也是建立在制度论基础上的,而制度论则须置于传播论的框架之中,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如何进一步处理好这种内在逻辑,实现传播论与实在论、制度论的统合与融通,是推进虚构本质讨论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4.
[2][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极简人类史:从宇宙大爆炸到21世纪[M]. 王睿,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53.
[3][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M]. 林俊宏,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5.
[4]梁启雄. 荀子简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09.
[5]唐小林. 信息社会符号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2:45.
[6][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
[Z].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22. [7][美]R M赛恩斯伯里. 虚构与虚构主义[M]. 万美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8]Terence Parsons. Nonexistent Object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11.
[9][美]纳尔逊·古德曼. 艺术的语言:通往符号理论的道路[M]. 彭锋,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9.
[10][法]热拉尔·热奈特. 热奈特论文集[M]. 史忠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1][韩]朴异汶. 艺术哲学[M]. 郑姬善,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2]徐敏. 虚构对象的形上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3][美]约翰·R塞尔. 表达与意义[M]. 王加为,赵明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4][美]乔纳森·卡勒. 结构主义诗学[M]. 盛宁,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71.
[15]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16]赵毅衡. 论虚构叙述的“双区隔”原则[J]. 外国文学研究,2014(2):136-144.
[17]中国大百科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4卷)[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390.
[18][法]A J格雷马斯,[法]J库尔泰斯. 符号学: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Z]. 怀宇,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162.
[19]马大康. 现代、后现代视域中的文学虚构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0][美]杰拉德·普林斯. 叙述学词典[Z]. 乔国强,李孝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36.
[21][美]西摩·查特曼. 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2.
[22]赵毅衡.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23]王长才. 梳理与商榷——评赵毅衡《广义叙述学》[J]. 文艺研究,2015(7):151-160.
[24]谭光辉. 再论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原理——对王长才与赵毅衡商榷的再理解[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97-105.
[25]王长才. 再论“双层区隔”: 虚构、纪实的性质与判断困境[M]//符号与传媒(21).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209-218.
[26][德]沃尔夫冈·伊瑟尔. 虚构与想象: 文学人类学疆界[M]. 陈定家,汪正龙,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181.
[27]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

本文刊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辑︱刘津
视觉︱欧阳言多
如果这篇论文给你带来了一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