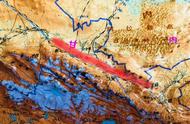如果三臭还活着,也有三十六、七岁了。
三臭是村长栓振家的三小子,十几年前一个深秋的夜晚,三臭和几个喝了酒的发小,开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疯狂的钻入了停靠在路边的大卡车之下,小车被削掉顶盖,五个孩子无一幸免。
那是一个北方的小县城,繁荣的商业街位于县城中央,中央向四周扩散,逐渐形成了与县道、省道相接融的环路,称之为“东环、西环、南环、北环”,对于闭塞的小县城而言,这四个方向的环路是他们通往外部的必经之路,也是外界物资运输的必经之路。路边常年停放着待修的、已修的、修完的八轮卡车,四轮卡车等等工业用车。
上世纪90年代,家家户户还以种地为生,计划生育没有现在这么严,栓振媳妇儿一口气连着生了三个男娃子,直到意识到自家的粮食无法供给的时候,才停了下来。
老大叫大臭,老二叫二臭,老三叫三臭,在农村,名字起得越孬就越好养活。一家五口的重担全部压在栓振的身上,虽然他起早贪黑地在地里耕作,但是随着3个男娃子越来越大,吃得越来越多,栓振无论怎么努力都觉得粮食不够吃。尤其是大臭,为了两个弟弟能吃饱,自己总是吃一点。饿的小脸总是蜡黄蜡黄的,这当爹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当时村里好多人出去打工,回来的时候都是穿金戴银,富贵气足的不得了,这让本就精明的栓振很是动心。
栓振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本家子都是一个村的,这个村叫“北定村”,干建筑队的人居多,而栓振一个辈的堂兄弟家就是干建筑队起的家。于是,这天晚上他掂了礼品拜访了同村的堂哥栓锁。
刚走到门口,堂嫂子梅珍端着锅出来倒刷锅水,闻言是栓振,便客气地让进了屋。一进屋,酒肉食完后的残渣散发着奢靡的味道,让栓振不禁咽了口唾沫。
“振子啊,你咋来了?是有啥事啊?”栓锁剔着牙打着饱嗝开口问道。
对于这位堂哥他既亲切又客气,亲切是因为他们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客气的是今天不仅有求于他,还因为人家财大气粗,自己在跟前抬不起头来。
他踟蹰而忐忑地回答道:“锁子哥,我想跟着你出外做活去。”随后,把自家的情况如实诉说了一遍。
“也不是不占,干建筑这个可是苦,你想清楚了吗?”
“哥,我想好了,庄稼人咱有的是气力,为了孩子们多苦多累,咱都能受着,你就让我跟着你去吧!”
于是,这个月十五号,栓振跟着堂哥栓锁的建筑队一起出外做活了。在外边闯荡了三、五年,衣锦还乡谈不上,但是回来的时候带了厚厚的一摞人民币,这足以证明栓振在外边混得不错。栓振用这些钱盖起了新瓦房,看着孩子们吃饱穿暖,脸上洋溢着笑容的时候,他觉得在外边受的罪都值得。
起先他是跟着堂哥栓锁的建筑队干小工,后来到大工,之后又是班组长,现在是堂哥的左膀右臂,安排工人,验收质量,看图纸等等这些活,他都能应付自如。
那个年代,建筑工地管理极其不规范,加上施工安全措施不到位,经常出现工伤事故。有一次夜班浇筑混凝土,罐车司机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卸料斗还没有收起来就着急走,直接撞到了毫无防备的栓振脑袋上,瞬间头破血流。
在外边这几年,能平安回来也实属万幸。由于积累了几年经验,栓振回来后就组建了自己的建筑队伍,主要做劳务分包。他本身就精明,加上当地素有“建筑之乡”的称号,没几年就摆脱了贫困的帽子。一家人以前干瘪的脸现在也变得油光铮亮,栓振也开上了好几个圈的小汽车,一副大老板的做派。这不,今年村委会选举,全村597户,他以588票当选新一届的村长。在农村,有钱就有权,钱权不分家嘛。当上村长的他,把家里的工程队交给大臭和二臭管理,三臭最小,还在上学。大臭也不像小时候那蜡黄的脸了,俨然一副二老板的作风。
在村里的街道上,总是有一辆看起来样子很怪的车疾驰而去,让人不禁侧目。长大了才知道,那叫吉普。那辆车便是大臭经常开的。他家车很多,黑色小轿车也有几辆。人有钱了,腰杆子就硬了。
一次,村里回迁房的施工队,不小心从楼上掉下一根方木,差点砸到栓振的宝贝孙子宁宁,儿媳妇一个电话,栓振开着车就来了,二话不说,先给负责人一记耳光,动作行云流水般,瞬间把人打懵了。俗话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建筑商是外地的,不得不赔礼道歉,还花钱专门搭设了安全通道棚,施工也规范多了。看起来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然而总有天不遂人愿的事情发生。
栓柱是栓振的亲兄弟,两家挨着住,虽然栓振家发达后住上了楼房,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栓振老两口子还是喜欢住在祖辈传下来的小平房里。平房旧了就翻新一下,冬暖夏凉住着也挺舒服的。拴住家的婆姨素华是一个嫉妒心比较强的女人,看着邻家大哥家天天吃香喝辣,出门小汽车,进门小汽车的,她的心里越发不平衡。那有什么办法呢?怪就怪自己当家的脑子不够活络,心思不够深厚。虽然大哥发家也给了自家不少好处,但是总归不是自己的。
拴柱也跟着栓振的建筑队干活,可是他天生愚笨,又不善言语,勉强干个小工维持一家的生计。虽说女儿已经嫁出去了,但是婆家也是一个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主,孩子不听话,非要嫁,当娘的还能拦得住?女儿一回娘家,素华就把家里好吃的拿出来贴补给她。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越发穷困。上个月儿子高考落榜使得素华的心里更加不平衡。她琢磨来琢磨去,想出了一个法子来改变自家的命运,那就是“移坟”。
所谓移坟,不是真的移坟,而是把自己祖宗坟的上贡口移动方向,也叫改风水,以起到兴家兴业的目的。思想落后,信奉鬼怪的人们,往往在付出努力仍无法改变自身现状时,总会寄希望于一些迷信活动。在农村,移坟可不是件小事,要所有一大家子当家人商议后才能实施。因为老祖宗不是一人的老祖宗,承载着一大家子人的灾难福祸。
有了这个想法,素华先跟栓柱说,栓柱也是个“妻管严”,老婆说啥就是啥。只是他们去和大哥家商量这件事的时候被大嫂撵了出去,悻悻而归。换位思考,栓振家这些年过的日子何止是舒服,岂会同意如此荒唐的决定呢。本想着事情会不了了之,但是素华却不罢休,几次三番念叨,专门在一家人聚集的时候提起,被否定后,就摔锅砸盆发泄着自己内心的不忿。
为了这事,两家闹得鸡犬不宁,差点动起手来。看着两家关系闹得这么僵,栓柱的心里是越发难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两家毕竟是亲兄弟,于是他趁着素华没在家就一个人去了大哥家。恰恰栓振出去吃喜宴还没回来,栓振媳妇一看兄弟来了,也没啥好脸色,还给了几句难听的。这栓柱是个孬货,也不敢顶嘴,回去就把事情跟素华说了。素华气一急,拿上锄头就往坟地里走,边走还边骂骂咧咧,“我让你家牛,我让你家横,从今天起我看你家还能横多久”。
没错,她去坟地改风水去了。栓柱知道自己惹祸了,一路跟着但也没拦住。等他赶到时,自家祖坟上原本放在西北45°方向的贡品台偏离了原来的轨迹,被移到了正北方向。他急得直跺脚,又急又气,可是生性懦弱的他,在素华跟前连个屁都不敢放。俩人就这样吵闹着回了家,半个月过去了,一家子都相安无事,这件事就这么被夫妻俩淡忘了。
今天晚上,三臭的发小彦斌过生日,几个小伙子约了个饭店,一起吃饭,三臭还特意给兄弟买了个蛋糕,他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三臭家经济条件好,三个儿子中属他跟栓振的秉性相似,除了脑子活络以外情商也极高,平常日下的一点小恩小惠就让身边小兄弟死心塌地的奉承着他。所以,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一帮人前簇后拥,让他无比享受着尊贵的待遇。三臭开着家里刚买的新车,载着兄弟们来到了饭店,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又去了KTV潇洒。
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们晃晃悠悠从KTV出来时已近凌晨,那个年代,小县城根本没有代驾一说,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普遍偏低,再加上一帮人觉得县城不大,开车几分钟就回家了。于是几人上车后,三臭毫不犹豫开车就走。殊不知,他们踏上的是一场死亡之旅。喝了酒的他车开得晃晃悠悠,加上车内兄弟们的嬉闹声,几乎无意识地开着车疯狂钻到了停靠在路边的后八轮下边,高跨的大车把小车的车顶都削去了一半,几人当场毙命。
众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接到交警通知的栓振被吓傻了,慌乱驾车来到现场,只见自家的新车已经被挤成了肉饼,三臭连个全尸都没看见。虽然这种死人的场面他也经历过不少,但现场的惨烈程度再加上是自己儿子,不禁让他脚下一软,瘫倒在地。旁边的交警也是见怪不怪,认定责任,处理现场,冷淡且专业地处理着事故。勘验过后,认定五个孩子负主要责任,卡车司机和维修店负次要责任,责任划分明确,处理起来就顺利得多。三个月后,五个孩子的家长拿到了为数不多的赔偿金,欲哭无泪。人活着为了碎银几两,可是人最怕的是碎银有了,命没了,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命。况且,这点钱不及栓振家九牛一毛。
一周后,在殡仪馆见到了自己的三小子,才让栓振意识到这几天的恍惚不是梦,是真的。他忍着巨大的悲痛,给三臭办了体面的下葬礼,路过自家祖坟(非正常死亡的未婚男子三年后配了阴婚才让入祖坟)时,无意一瞥,发现自家父母坟前的上供口有人动过。这一发现,让他对三臭的死亡有了自己的想法,他看似悲痛且平静地给自己儿子亲手盖上了棺木,内心实则早已风起云动。
事后,他暗地里调查,终于了解真相。原来那天栓柱两口子动上供口的事被人看到了。“真是那个恶婆娘”他恨恨地说。
栓振咽不下这口气,几天之内便动用自己的各种关系,找了打手,要给素华家一点教训。
初秋的夜晚月黑风高,素华吃完饭早早出来遛弯,
“年纪大了,再不走就真的走不动了”她出门时自言自语道。
自打三臭出了这事以后,她便对大伯哥家的挤兑少了,是因为多年的亲情被唤醒了还是自己心里有愧,她也说不清楚。
这天晚上,她照例在附近的公园遛弯,因为熟悉,即使在背人的地方她也没有害怕过。而今天,刚走到假山后边的她面前突然窜出四五个大汉,一下便把她摁到了地上,此刻她却是淡定无比,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似的说了句:“我知道你们是谁派来的”,随着话音刚落,为首的大汉便一棒下去,打断了她的右腿。惨烈的叫声引来了周围的居民,那几人落荒而逃,素华也被送到了医院。经诊断,她的右腿粉碎性骨折,即使接上了,痊愈的可能性也不大。下半辈子,只能依仗拐杖行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栓柱家连夜搬走了,此后再也没人见过他们,连带孩子们的消息也销声匿迹了。
一墙之隔的栓振家,随后也搬走了。多年后,村里改造,征收通知才刚下来,人们就发现两家的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推倒在地,旁边的铲车解恨般疯狂敲打着地上的残垣断壁。而此时,栓振仍是村里的一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