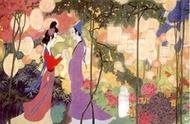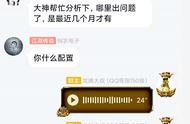绝句
——志南(宋)
古木阴中系短篷,
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我在研发《古诗词趣读与写作启蒙》课的过程中,发现各种诗词解析的教材、书籍、网站等对部分诗词的误读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在那篇“停车坐爱枫林晚”里的“坐”和“晚”究竟什么意思?的文章发表在头条后,已有12万多阅读量,其中有人留言说“诗不可达诂”:即每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同“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诗无达诂”一语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五《精华》。这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一首诗除了作者自己最清楚要表达的意思之外,他创作出来也是希望别人能懂的,至少在字面上的基本意思是可以做到尽量“达诂”的。至于作者当时的心情、想表达的言外之意,虽然可以通过作者的身份背景、人生经历等推测个大概,倒真是无法达诂了,搞不好都是些“自作多情式的过度解析”。
让我感到好笑的是:那些所谓的古诗词专家、学者们对属于“读后感”那部分东西“穷究其理”,却对本该很明确的字词含义翻译得漏洞百出;把近体诗的平仄讲得头头是道,却把诗句意思解释得莫名其妙。本末倒置,莫此为甚!
这首志南和尚《绝句》里的“短篷”被许多人解释为“短篷船”,当然大部分诗句里的短篷确实是指下图的这种“短篷船”。上面的“短篷”(顶篷)有遮阳挡雨的作用。

经查,同为宋朝的诗人陆游的诗里用“短篷”一词最多。其诗中的大部分“短篷”也是指这种有顶篷的小船。用事物的一部分特征来代表全部,这种修辞手法叫“借代”。但下面这首里的“织短篷”,如果把“短篷”直接解释为“小船”明显就不合适了。
六月二十四日夜分梦范至能李知几以尤延之同宋代:陆游
露箬霜筠织短篷,
飘然来往淡烟中。
偶经菱市寻溪友,
却拣苹汀下钓筒。
白菡萏香初过雨,
红蜻蜓弱不禁风。
吴中近事君知否?
团扇家家画放翁。
“露箬霜筠”中的“箬”是指一种竹子,叶大而宽,可编竹笠(竹帽),又可用来包棕子、织席子。“筠”是指竹子的青皮。可见这些材料用来做的绝对不是小船,最多是船上防雨的顶篷,或者就是类似“斗篷”的防雨工具。
再来看看同时期范成大的一首诗:
宿阊门
宋代:范成大
五更潮落水鸣船,
霜送新寒到枕边。
报道雾收红日上,
野翁犹盖短篷眠。
这里“盖短篷”的“短篷”当小船讲又不合适了,即便野翁躺在岸边地上,上面是翻转过来的“小船”,那也不能是有顶篷的小船。太阳都出来了,遮在脸上的“竹笠”,或者类似防雨顶篷那么长的竹编制品把头和身体遮住才能“入眠”。此处的“短篷”同样不适合解释为“小船”,最多是船上一个用来防雨的可拆卸的“配件”。
江苏省海安县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夏俊山曾经撰文说:志南《绝句》中的“短篷”是“背篷”。背篷作为雨具,最迟大概在唐代,因为唐代诗人皮日休就写过《背篷》诗:“侬家背篷样,似个大龟甲。雨中局蹐时,一向听霎霎。”唐代诗人韩偓在《江岸闲步》中也写道:“一手携书一杖筇,出门何处觅情通?立谈禅客传心印,坐睡渔师著背篷。”元代王桢《农书》(见卷十五),发现背篷还有好几个名称:“覆壳,一名鹤翅,一名背篷,篾竹编如龟壳,裹以箨箬。覆以人背,系肩下。耘薅之际,以御畏日,兼作雨具。” 最后他的总结是:同一物件因时代、地区不同,名称有变化很正常。僧志南与陆游同为南宋人,他和陆游一样,在诗中用“短篷”称雨具,而海安人干脆就叫这种雨具为“雨篷”。如果你觉得“夏俊山”分量不够,199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宋语言词典》将短篷清楚地解释为雨具。

苏老师的意见又如何呢?我分析哪种解释更合理,从来不看是谁说的,主要看逻辑。志南诗里“古木阴中系短篷”的“短篷”一词前面有个“系”字。那么这里的“短篷”就既可能是指上面图片中的”背篷“,也可能是指把小船绑在河岸边的木桩上或树上,因为许多诗里的“系短篷”就是“拴小船”的意思。古木也完全可以是指河岸边的古树,何况下一句又是“杖藜扶我过桥东”,都有桥了难道下面还不是河吗?这样解释似乎更没什么毛病。
那有毛病的可能就是志南和尚了,他明明有船,为什么偏偏要过桥呢?直接把船划到桥东边的对岸不就行了吗?如果说老和尚已经年老体弱需要拄拐杖了,那放着带有顶篷能挡雨船不坐,下雨了不怕路滑摔跤还非要走上去淋着雨过桥,这是故意要得感冒向庙里请假吗?还是船突然漏水了要维修,没办法只能过桥?
我们再来看看后面两句:第三、四句“沾衣欲湿杏花雨”与“吹面不寒杨柳风”属于两句对仗的倒装句,主语都放到了最后。所谓“杨柳风”和“杏花雨”是古人将树变绿、花盛开的季节与风、雨对应起来的一种表述(不代表杏花花瓣如雨),无疑就是春风和春雨。那么是不是因为春雨绵密,随风而无孔不入,所以即便头上有树荫遮挡、戴着雨具上桥也照样会“沾衣欲湿”?是不是因此桥上比较湿滑,所以志南才更要拄着“杖藜”呢?
(因为下起了春雨)我在古树的树荫下系上了背篷,拄着拐杖过桥往东边去。杏花盛开时的春雨沾在我的衣服上快要将衣服弄湿了,杨柳变绿时的春风吹在我☆脸上,一点都不觉得寒冷。(因为往东方去,春风又是从东面刮来的,所以是顶风迎面,斜向飘来的绵绵细雨当然是背篷无法完全挡住的,自然会弄湿衣服。)
有人反驳说有些桥只能从一头过(设置特定场景),又有人说这个桥不是河面上的桥而是山谷间、小溪上的吊桥(那样是不是写小船的必要性更小了?再者,谁说志南和尚一定是从外面坐船来的呢?他可不可以是从山里寺庙出来直接上桥的呢?)。相比之下,雨具的解释就不需要这么多额外设定。至于辩驳说“小船更富有诗意”、“他是看到桥下的空船”、;“志南和尚就是特意上桥感受这春风细雨”之类,这又变成“个人读后感”的问题了。即使你仍然坚持是“小船”,相比在雨天过桥,到底是“雨具”还是“小船”更可有可无呢?不能说“短篷”在这首诗里必定是“雨具”而不是“小船”,但从合理性与关联性以及诗句间的连贯性来看,无疑“雨具”更具“普适性”!

上图中书生头上用来遮阳挡雨的东西像不像船上的顶篷呢?这是我心目中两种用途都具备的“短篷”形象,当然材料是竹叶和竹皮。下面的竹箱叫做“竹箧”,类似如今的行李箱。志南和尚是否就是背了它行走江湖,遇到雨天将“短篷”系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