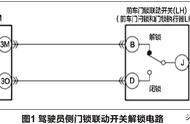文/季承
摘自《我和父亲季羡林》
父亲在德国的十多年里,孤身一人,思乡之情十分严重,特别是在他结束学业不能回国的时候,尤其如此。每逢过年过节,他的思乡之情剧烈涌动,除了要写点什么,不免要大哭一场。“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一直是父亲怀乡时的自诩,里面饱含着他这位游子深沉的孤独和寂寞。在怀念故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已故的母亲,其次是远在万里的济南的那个家。前者出于血缘亲情,后者则出于理智和责任。这是父亲对两个家庭的思念,是他对两个家庭的情结。
那时,父亲思念的还有另外一位母亲,那就是他的祖国,是祖国这个大家庭。父亲这两个母亲的情结,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常常表现在他的文章中和行动上。正是这两个情结,最终使他割断衷情回到自己的家,自己的祖国。令人感动的是,最近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从一个笔记本上发现了他写的一些文字,竟然仍在述说这两个母亲的事,他写道:“一个人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生身之母,这用不着多说;第二个是养身之母,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道理并不深奥,一思考就能够理解。”写这些文字的时间是2009年7月3日,距他7月11日离世只有8天时间。由此可见,这两个情结对他有着多么深刻的意义。
父亲的家庭情结较为纷乱,不像我和姐姐,我们只对济南那个家庭有感情的关联,和清平官庄的那个家没什么感情上的联系。除叔祖父之外,我们谁都没去过那里,对那里一无所知。在我和姐姐的心里,济南的这个家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管叔祖父和叔祖母叫“爷爷”“奶奶”。在此为了叙述清楚,才称他们为叔祖父和叔祖母。可父亲的家庭情结就不像我们那么单纯了。按我和姐姐的想法,父亲应该和我们一样,只对济南的家有感情,不应该有其他想法。可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父亲的家庭情结要复杂得多,这是当时的我和姐姐所不能理解的。
父亲是从一个农村家庭来到一个城市家庭的。他对农村那个家庭有什么样的情结,我所知不多。从父亲的叙述里,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只有两件事:一是“穷”,二是他对母亲的无限怀念和悔恨。自从他父亲把家产败坏干净之后,他家一贫如洗,父亲小时候连吃饱肚子都有困难。所以,捡食落枣竟成了解决饥饿的办法,而从大娘那里弄半个白面馒头就如得龙肝凤髓,为了抢吃一块白面饼子,竟被母亲一直追到水湾里去。除了穷困,父亲对他母亲的怀念和悔恨可谓深刻、长远。他6岁进城,21岁在清华大学读二年级时母亲去世,期间没能好好看望过母亲,何谈孝敬!那时他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只守着三分地过日子,其穷困可想而知。念大学的他,虽然有能力在经济上支持家里一点,可是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后来回家奔丧,为他母亲送终,他竟然回忆不起母亲的面容。对此,父亲终生悔恨,无论如何也不能释怀。尽管如此,清平那个地方毕竟是他的出生之地,那里曾生活过他的亲生父母、两个妹妹,还有很多同姓和异姓的亲戚;那里有他小时的伙伴,当然还有养育他的土地、房屋和他熟悉的树木、池塘、道路和其他的一切。这些,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都描述过。他对那个家庭的深刻感情由此可知。但是,除了母亲,父亲很少谈到他的父亲,偶尔谈起也只说他不怎么样,但究竟怎么不怎么样,不清楚。前面曾写过他的一些表现,譬如挥霍家产、赌博充大、无所事事等,恐怕也不过如此。但父亲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坏人。后来,父亲偶然谈到他的父亲,觉得他身上确实是有股侠气,并且也影响了父亲本人,父亲似乎是赞赏这种侠气的。我对父亲说,依我看,你身上好像也有这样的侠气。他微笑着说,是有的。这似乎是父亲对于他父亲的唯一的肯定。
对济南的家,父亲有怎样的情结呢?按常理说,他应该有幸运、幸福、感激的心情。可是,事情正好相反。他在济南的家里长大,叔祖父给他慷慨的支持,对他严格要求,又帮助他成家立室,可他对这个家始终觉得格格不入,甚至反感。之所以如此,叔祖母对父亲的态度是重要原因,此外,父母之命的婚姻也是原因之一。上文所述,第一任叔祖母对这个外来的侄子不感兴趣,不免在很多事情上慢待他。一些事情乍看都是小事,可就是这些小事,使父亲对济南的家产生了“见外”的感情,“寄人篱下”是父亲对这种感觉的描述。可以这么说,父亲虽然到了城里,和叔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并没有把济南的家真正当成自己的家。父亲到了济南以后,有机会念书了,眼界扩大了,知识增长了,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自己。他发现,除了调皮以外,他竟然是一个能够念书、成绩优秀、多愁善感、感情丰富、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是个文人坯子。济南的家的环境非常适合他念书,他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上了中国的两所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他到了北平,选择了清华大学,又学了西洋文学。这时的他,已经完全不是从官庄出来的农家子弟了,他已经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的感情生活里,对济南的家的异己思想已经越来越明确。那时的父亲,在家庭这个问题上,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他本来有一个自己的家,可是竟不得不寄居在其叔父家里。他本来有自己的意中人,可偏偏要娶一位自己无意的女人为妻。理智上,他承认自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而且除了生育后代、延续香火,在将来结束学业后,还必须承担起维持这个家庭的责任。然而,他与这个家庭又如此格格不入。农村的那个家,距离越来越远了;城里的这个家,也并没有贴近。从他的性格、感情、气质和理想来说,或者说透了,从他个人的愿望来说,那个时候他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家庭羁绊的自由人,由他自己去建立理想家庭。在旧中国,个人从旧式家庭里解放出来,正是那个时代革命大潮的一部分,许多人为了实现个人的解放,就背叛家庭,走上革命的道路,进而争取整个社会的解放。这样的故事是很多的。可是,父亲没有这个勇气,不满归不满,他没有走上和家庭决裂的道路。他走的是委曲求全、和家庭妥协的道路,他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他人生的最后。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济南的家的感觉。在他的《清华园日记》里,有许多记述:
家庭,理论上应该是很甜蜜的,然而我的家庭,不甜蜜也罢,却只是我的负担。物质上,当然了,灵魂上的负担却受不了。(1933.3.3)
济南空气总令人窒息。看着浅薄的嘴脸,窄的街道,也就够人受的了。(1933.6.10)
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厌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1933.6.30)
说实话,家庭实在没有念念的必要与可能,但心里总仿佛要丢什么东西似的,惘惘的,有醉意。(1933.8.9)
我最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寂寞呀,寂寞呀!我想到了故乡里的母亲。(1933.8.19)
家庭对我总是没缘的,我一看到它就讨厌。(1934.4.18)
……想到将来……前途仍然渺茫,而且有那样一个家庭,一生还有什么幸福可说呢?(1934.5.6)
家庭毕竟同学校不同,一进家庭先受那种沉闷空气的压迫。(1934.6.29)
中国的家庭真要不得。家庭本来是给人以安慰的,但大部分家则正相反,我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1934.7.3)
以上是父亲1933年、1934年日记中的话,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他的家庭情结的真实写照。为什么父亲对家庭会有这样的情结呢?客观地说,父亲从来就没有把济南的家当成他自己的家,这是他叔父的家,他是被寄养者;无论他叔父母待他如何,他终归是寄人篱下的。这里虽然有他的结发妻子,有他的亲生儿女,可这些都是他情愿的吗?这感情,跟我和姐姐的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家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听到父亲嘴里说“叔父”“婶母”,我们觉得奇怪、见外。除了上面的那些记述,父亲还说过一些感受。譬如他说,这个家里有两个女人使他对家庭产生了反感:一个是他的婶母,一个是他的秋妹。很显然,婶母没有儿子,对培养他这个外来的侄儿缺乏热情,况且,父亲只会读书、花钱,他乡下的父母都要靠城里的弟弟供给,婶母哪里会高兴?这是人之常情。秋妹则嫉妒这个乡下来的哥哥,这也很自然。在父母的娇惯下,她后来又嫁了一个有钱的丈夫,表现得“轻浮”和“高傲”,也在情理之中。至于给父亲不断地制造麻烦,譬如,她说她母亲的病是我父亲气出来的,等等,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把这些归为“女人天生的劣根性”,再加上他所谓“挥之不去的穷困”,父亲对此感到压力和气闷也是很自然的。
此外,如果父亲能够有一位可心的女人做妻子,或许还不至于对这个家有这样的不良情结。可是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父亲有了妻子,但还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硬性结合,父亲自然感到很不满意。父亲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当时他心中可意的人是“荷姐”,就是我的四姨,而不是行三的我母亲。于是,他终身背着这个感情的包袱,生活得十分沉重。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对我们这个家是不会有好的情结的。
可是,父亲从来没有直面过这个问题,对我和姐姐或其他家人更是讳莫如深。我和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我们常暗示要将母亲接到北京来,这时他才说了一句话:“我和*没有感情。”这是拒绝我们的建议的话,也是真话。不管是在说这话的20世纪50年代,还是今天,它都是真的。我父亲和母亲是没有感情的,他并不情愿和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结合是勉强的、机械的,他们的婚姻和生活是悲剧,他们的家庭也只是形式上的圆满或美好。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把父亲的家庭说成是美满的。
至于说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就的婚姻不一定都是悲剧,在很多情况下,也能成为喜剧,例子随手可拾,我也看不出父母的结合就一定要酿成悲剧,但他们为什么不可以产生感情从而营造幸福家庭呢?父亲为什么不去做这个努力呢?为什么他只是含着不满,听之、任之、受之、冷漠处之呢?我至今没有答案。
父亲曾在《清华园日记》里写到过他的婚姻:“……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即彭德华,他的妻子——作者注)。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 Schmerz(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不成的东西”虽然成了“东西”,婚结了,但是感情是没有的,而且得到了痛苦。为什么没有感情,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痛苦,父亲没有做具体的说明。为什么不能有婚后恋,为什么不能在婚后去培育夫妻间的感情,他更没有说。似乎,从那时他就给自己的婚姻宣判了死刑,不过是无限期地缓期执行罢了。一方面是寄人篱下,一方面又有了这样的婚姻,父亲对自己的家庭能有美好的情结吗?
在大学时期,父亲对自己所处的家庭,纵有千恩万怨,似乎并没有背叛的想法。一方面,那时他还没有独立的能力,要依靠这个家供他上学;即使毕业,以后的前途还难以预料。虽然他脑子里装满了当作家或其他什么人的想法,可是怎么实现,还大成问题。至于当教授,他压根儿就没敢想过。他想的首先是混个差事来养活这个家,这是他的责任感的表现。另外,父亲骨子里就是一个有背叛思想而没有背叛勇气的人。他感情丰富、文思泉涌、善于学习,天生具有文人气质,对女人、爱情、家庭自然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可这与他所处的家庭的情况相去甚远,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去甚远。对于父亲来说,尽管他已经由一个乡巴佬蜕变成一个现代才子,可他却缺乏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胆量。传统的道德观束缚着他,他跳不出那个圈子,他只能在日记里发泄。对叔祖父母、妻子儿女,对那个由他们组成的家庭,他虽感异己但没有背叛的勇气。他既不背叛,又不去培植爱。或许他会说,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背叛,他是为了求仁,才委曲求全的。但他却没有说他为什么不去培植对家的爱,或许那样做对他说来太过勉强,太不情愿。做文人固然美妙,但他身处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那文人做起来也不会快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大学毕业了,他在济南当了一年中学教员,然后幸运地去德国留学了。阴差阳错地,他走上了做学问、当教授的道路。虽然如此,这只是给了他一个出路,他和家庭的感情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父亲到了德国,脱离开自己的家,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攻读枯燥无味的学问,饱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饥馑和各种危险、苦难。但即便在那种严酷的条件下,父亲还是有机会体味到几个家庭的温暖:章用家、他的女房东家、伯恩克家、迈耶家、弗里堡的克思家……甚至也有几个女孩使他心动。其中迈耶家的大姑娘伊姆加德(Irmgard)对父亲表示了爱意。她经常帮父亲打论文稿子,他们有了密切接触的机会。他们曾经度过了一段热恋的时光。他们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几乎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父亲曾为她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而怦然心动。这时,父亲真正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了幸福。他们同时坠入了爱河。(见张光璘:《季羡林先生》,作家出版社,第83页。)更重要的,这恐怕是父亲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也可以说是初恋。可结果如何呢?伊姆加德一边替父亲打字,一边劝父亲留下来。父亲怎么不想留下来与她共组家庭,共度幸福生活呢?当时,父亲还有可能应聘去英国教书,可以把伊姆加德带去在那里定居。可是,经过慎重的考虑,父亲还是决定把这扇已经打开的爱情之门关起来。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理智地处理了“留下来”还是“回家(国)去”的难题。虽然“祖国”“家庭”使他战胜了“留下来”的念头,但可以想见,做这个决定是多么不容易呀!“祖国”是个伟大的概念,当时执政的是国民党,父亲对国民党不感兴趣,对自己的那个家也并不留恋。回去,就好像跳进了两个笼子。可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这两个笼子。父亲的这一决定当然可以誉为美谈,可以说是“仁”的胜利,而且是“至仁至义”。可是这个“仁”却成了我们这一家继续上演悲剧的种子。他的这种选择,也给伊姆加德制造了终生的悲剧——据说她因此终生未嫁。父亲的至仁至义的选择,为什么竟得到了双重悲剧?难道追求至仁至义,就一定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吗?而伊姆加德为了爱情就一定要孤独一生吗?虽然这的确是一个可以歌颂的恋爱故事,可是为了爱情,就只能有这样的结果吗?这可真是一个难解的题目!不知世上有谁能够给出一个万全的解答?
不管怎样,这是父亲自己的选择。不管怎样,这也是伊姆加德的选择。不管怎样,母亲也只能接受父亲这样的选择。就这样,父亲带着并未改变的家庭情结和复杂的感情纠葛回家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