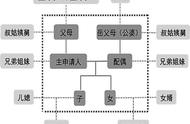楔形文字中“ME”的写法演化
“ME”这个神奇的概念写法是很简单的。如上图,楔形文字中“ME”起初是最左边的写法,后来经过简化、左转90度,变为最右边的形态,这可能是由于纵向的文字所占空间较大,书写不便。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历史铭文中,比如在一片碎陶器上写有基什的王恩美巴拉格西(EN.ME.BARAG.GE.SI)之名。米哈洛夫斯基(Piotr Michalowski)在其《一个名叫恩美巴拉格西的人》(“A Man Called Enmebaragesi”)一文中认为“不论怎么看 ,恩美巴拉格西这个名字没什么含义。”在《吉尔伽美什与阿伽》中提到了恩美巴拉格西之子阿伽(Aga)去攻打乌鲁克,与当时的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战斗的故事。恩美巴拉格西的年代比吉尔伽美什还早,在低年代体系中,他的生活年代约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而在高年代体系中则是约公元前2800年左右。在这个名字中“BARAG”是王的意思,“SI”是充满,“EN”是统治者的称呼,所以拱玉书教授认为,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富有王道的王”。
卢加尔札格西(Lugalzagesi)是温马的国王,后来也成了乌鲁克的国王,他生活在约公元前2350年左右。在卢加尔札格西的一篇铭文(Lugalzagesi I ii)中有一段话,拱玉书教授将其译作:“天下王者,悉数来朝,皆往乌鲁克,因其王权道(即王权中有ME)”(苏美尔语原文为:BARAG-BARAG KI.EN.GI ENSI2 KUR-KUR-RA KI-UNUGKI-GE ME-NAM-NUN-ŠE3 MU-NA-GAM-E-NE)。古地亚(Gudea)生活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的拉格什,他的铭文(Gudea B xiv 8)中有“战斗的臂膀中充满了王权道”一句。他的另一则铭文(Gudea Cyl. A ix 12)中则提到“他的‘ME’是最大,超过任何其他‘ME’”。还有一则铭文(Gudea A xvii 18-19)中则有“此庙之光接天穹,此庙之‘ME’覆大地”的说法。

现藏于卢浮宫的古地亚坐像
苏美尔语中有还“王权道”(ME-NAM-LUGAL)一词,其中的“LUGAL”表示王,“NAM”用来构成抽象概念,而前面还加了“ME”。拱玉书教授分析了其构词法:在普通的名词“王”前添加表示抽象概念的词缀,而在这个词之前又添加了“ME”,相当于将已经抽象的东西进行“二次抽象”。这反映了苏美尔人的认识论:苏美尔人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在这个普通的东西背后他们又看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力量或状态,就用“NAM”将其抽象化,如“王权”(NAM-LUGAL)。但拱玉书教授认为用“王权”翻译“NAM-LUGAL”是不准确的,因为“王权”只能体现王属性中“权”的层面,而苏美尔人的“NAM-LUGAL”要比“王权”的内涵丰富得多。苏美尔人在“NAM-LUGAL”中还看到了超越之上的更深一层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使“NAM-LUGAL”(王权)成其为“NAM-LUGAL”(王权),这个东西就是王权中的“ME”,用汉语表述即“王权道”。这说明苏美尔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很深刻,虽然他们没有像后来的希腊人那样用散文形式将他们的这种认识做文字表述。此外,还有更“玄”的“ME”。比如“大道”(ME-NAM-GAL)一词,“GAL”本就是一个表示大的形容词,没有固定的阈限,本就抽象,而前面又加上了表示抽象的“NAM”,相当于英文中的“greatness”,而在“伟大状态”前再加上“ME”,就变成了“成为伟大状态的状态”。如果将“大”本身视作抽象概念的话,这个词相当于是“三次抽象”的结果。
关于苏美尔语中“ME”的概念,拱玉书教授已在《论苏美尔文明中的“道”》一文中详细论述。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ME”字的楔形文字“分明是上天下地、天地结合的物象,或许这就是苏美尔人形象版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拱玉书教授认为“ME”有3个维度:第一,它是元神、元动力,表述方式是“恩利尔道”,与《道德经》中“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天地母”异曲同工。第二,“ME”指的是“器之道”,即英文所谓的“power”,它寓于器中。第三,“ME”指是“器”本身,比如前文提到的百余种“ME”。苏美尔人的“器”不仅仅包括具体的物件,还包括了很多抽象概念。它们都属于具体的“道”。
故事背后的文明传播观
对于《伊楠娜与恩基》这部作品传递的信息,学者们此前有不同的解释:格林(Margaret W. Green)在《苏美尔文学中的埃利都》(Eridu in Sumerian Literature)中提出,伊楠娜拜访埃利都的神庙是为了获取“魅力”(charms)和“装饰”(adornments)。她将“ME”说成“魅力”和“装饰”,显然不准确。克莱默在《恩基神话,能工巧匠神》中则认为,伊楠娜“把文明之艺术(arts of civilization)从埃利都转移到了乌鲁克”。这个评价的目光离开了伊楠娜本人,聚焦在文明上,出发点更高了,但用“文明之艺术”概括“ME”仍不全面。拱玉书教授认为这部作品反映了苏美尔人的“文明传播观”。“ME”代表的是截至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人类所取得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就,所以这部作品以讲故事的形式表达了乌鲁克的文明成就来源于埃利都的观点。
这部作品选择乌鲁克和埃利都来反映文明传播观是有原因的。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乌鲁克文明已经高度发达,到了崭新的阶段。可以说乌鲁克的文明代表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发达的城市文明,百余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此时的文明有3个代表性的特点——文字、大型建筑和大型艺术品,其中文字最重要。拱玉书教授认为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后来任何科学领域的发明。最早的文字出现在乌鲁克IVa期,其上限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而属于乌鲁克IV期至乌鲁克III期(约公元前3200-2900年)的楔形文字泥板目前已经发现了超过6000块。这批文献大多是德国考古学家通过正规发掘所得,其中约85%是经济文献,其余为辞书文献。所谓“辞书”就是表格文献,现在能恢复的约有15-16种,其中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人表”。“人表”出现在最早的乌鲁克IV期。到了乌鲁克III期,有很多抄本,将其补缀后可以得到列有百余种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详细的社会分工,可想而知,乌鲁克在距今5000多年前已是相当发达的社会。现在虽然没有发现很多物质遗存,但是“字表”、“人表”、“城市表”、“容器表”等文献已足以代表当时的文明高度。在大型建筑中有宫殿建筑与神庙建筑。这样的大型建筑代表了经济发达程度与政府的组织能力。大型艺术品也有很多,如“祭司王”雕像与乌鲁克石膏瓶等。这些代表了人们对文化和精神享受方面的追求,体现了精神和艺术的创造力。

现藏于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的乌鲁克石膏瓶
追本溯源是人类的本能。纵观古代文明,到了发达程度之后,人们都站在新的哲学高度思考自己“从哪里来”的问题。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美尔文明已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发展。当时“中央集权”、行省林立,堪称苏美尔人的盛世。乌尔第三王朝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非常丰富,思想活跃,出现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此时,苏美尔人的精英们产生对自己的历史探源的兴趣非常自然。《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中讲述了文字的起源。而《伊楠娜与恩基》涉及的则是整个苏美尔文明来源的问题。乌鲁克的辉煌过去一直存留在乌尔第三王朝苏美尔人的记忆中,这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甚至把乌鲁克的先王们视为自己同宗同族的祖先,所以对当时的苏美尔人而言,探索乌鲁克的辉煌过去实际上就是探索自己的辉煌过去。
乌鲁克的发达与繁荣从何而来?拱玉书教授认为,对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有着“神本主义”思维理念的人们而言,选择埃利都作为他们的源头是自然而然的。直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埃利都一直是苏美尔人的宗教中心。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苏美尔人的宗教中心也北移至尼普尔。两河流域的宗教中心,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伊辛-拉尔萨王朝前以埃利都为中心;之后以尼普尔为中心。所以选择埃利都作为“文明的源头”,是现实和遥远的记忆结合的必然产物。埃利都位于两河流域南部,现代名称为阿布沙赫兰。1946-1949年,由伊拉克文物总局主持对该遗址进行正规发掘,考古报告《埃利都》(Eridu)则于1981年才发表。约公元前6000-5000年,埃利都就已有人居住。在欧贝德时期,当地已是重要的居住中心,后来又成为宗教中心。所以乌鲁克人认为其文明来自埃利都,这在考古学上说得过去。
在文学传统中,埃利都很重要。《苏美尔王表》中提到洪水之前的5座城市,其中第一个就是埃利都。埃利都的第一位国王是阿鲁里姆(A2-LU-LIM),意为“鹿角”。苏美尔语版的洪水故事中也提到了5座城市,其中为首的也是埃利都。在这则故事中还包括了母神将恩基派至埃利都的内容。贝洛索斯(Berossus)是公元前4-3世纪的巴比伦祭司,后来移居希腊并用希腊语书写了3卷《巴比伦尼亚志》(Babyloniaca)。第一卷中讲到了欧阿涅斯(Oannes)的故事:欧阿涅斯是一位先贤,他人头、鱼身、人腿和人声。有一天他从海里出来教巴比伦人立法、书写、农耕、建立国家,从此巴比伦人走向了文明。欧阿涅斯白天教巴比伦人,晚上又回到厄立特里亚海(即波斯湾)中。据贝洛索斯记载,欧阿涅斯的故事发生在阿鲁鲁斯王(Alorus)统治时期。这位阿鲁鲁斯王实际上就是苏美尔王表中的“阿鲁里姆”。《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一块泥板第13-21行中写道:“……仔细瞧瞧那台基,好好看看那些砖,看看其砖是否炉火所炼,看看其基石是否七贤所奠。”贝洛索斯讲的欧阿涅斯其实就是阿达帕(Adapa),他是埃利都的“七贤”之首。而《吉尔伽美什史诗》将这“七贤”视为乌鲁克城墙的奠基人。《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第57-58行恩美卡也有“当我在阿普苏把你(伊楠娜)赞美,当我从埃利都带来‘ME’”的表述。拱玉书教授认为,恩美卡的这句话指的是前面提到的《伊楠娜与恩基》中描述的事件,即伊楠娜把百余种“ME”从埃利都带到乌鲁克的故事。在后来苏美尔人的“文化记忆”中,这件“历史大事”发生在恩美卡统治时期。恩美卡是乌鲁克第一王朝第二位国王,据《苏美尔王表》记载,“他是建立乌鲁克之人”。这个历史文献又恰好可以与文学文献中“当我从埃利都带来‘ME’”相互印证。二者同指一个事件,即恩美卡统治时期乌鲁克文明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苏美尔王表》记录了恩美卡取得的成就,《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提到了他取得成就的方式,而《伊楠娜与恩基》描述了成就取得的具体过程和文明的具体含义。

拱玉书教授的《升起来吧!像太阳一样——解析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书影
精彩的讲座之后,拱玉书教授回答了听众的提问。篇幅所限,这里选取部分问答与读者分享:
Q:请问苏美尔对华夏文明有何影响?考古学家李济曾在殷商古棺椁上发现“肥遗”图案,说这是苏美尔的典型特征。这是否说明殷商时期已经和苏美尔有联系?
A: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苏美尔文明对华夏文明是否有影响?有的西方人曾说是有影响的,比如拉古伯瑞(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我在写博士论文时也曾引用过巴尔(Charles James Ball)的《汉语与苏美尔语》。这些都是很早的了。在早期,有一些人主张巴比伦的文明影响了世界其他的文明。这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泛巴比伦主义”思潮,认为只有一个文明是源头。至于李济发现了什么,这我不太清楚。据我所知,中国没有明显的东西是来自两河流域的。有一些现代人认为很像是来自两河流域的东西,但很难判断这到底是直接的影响还是偶然或者其他什么因素。我以文字为例,实际上苏美尔人的文字中有“六书”,非常明显地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六书”是许慎分析中国文字提出的6种结构,而苏美尔人的文字这6种结构也一个不差。这就涉及到怎么解释的问题,能说苏美尔文字影响了汉字吗?苏美尔文字在公元前3200年已经很成熟了,而中国的汉字就算推到夏朝也还差1000年,而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晚商甲骨文差得就更多了。我搞不清楚这近两千年间是怎么影响的。所以,虽然现在我找出了这么多相似的证据,但得不出影响的结论,只能摆出这种现象。有很多人解释说这其实就是一种“偶然性”或者“共性”,文字发展到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必然就有这几种结构。这是人类思维的共性,而非文明影响的结果。所以我也在等待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证据,如果只是文字一个方面,就很难得出相互影响的结论。其他的也是一样,可能会发现一个东西有点像,但没有真正的证据。如果它上面写着楔形文字,那么就确凿无疑了。但如果没有这些,只是像的话,就很难说。所以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说苏美尔文明影响到了华夏文明。或者相反,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华夏文明是最早的,影响了苏美尔文明。《苏美尔王表》中提到,洪水之前有5座城市和8位国王。有中国人写信给我,将这些王与中国古籍中的8位王相对应,说他们都是中国人,虽然我自己看不出这种联系。比如第一位王是“鹿角”,他也许发现中国的王与鹿有关系。但两河流域的王名目前也不是都能解释。
Q:苏美尔人的宗教信仰或思想观念在后来有传承吗?还是它们仅存在于文献当中?
A:人都没有了,我不太清楚怎么传承。现在我们都是从文献中知道,他们真的有神庙、文学作品,也知道他们都崇拜什么神。或者研究宗教的学者能缕出一个线条:他们一开始的宗教形式是“多神崇拜”,然后向“一神崇拜”过渡,都有哪些表象等。随着不断和其他民族同化,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都已经被融合了,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我说不好他们的信仰对现在的宗教有什么影响。就思想观念而言,比如刚才提到的“牧羊人”就明显是苏美尔人的。从文献上追踪,苏美尔人比其他的人群更早叫统治者“牧羊人”。这也可能是苏美尔人对后世的影响。类似这样的例子可能还会有,个别的词可能会传承下来。历法、天文等科学技术上的传承是很明显的,比如把1年分成360天,设置闰月,还有六十进制等,都是苏美尔人已有的。苏美尔人对后世的影响很多,但是宗教方面不是我的专业方向,我想不出也不敢说。
责任编辑: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