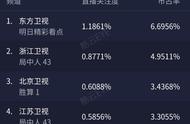盛夏,是小麦的收获季节,老季却高兴不起来。
老季今年将近七十了。去年在南方打工的大儿子回来了一趟,帮忙了秋收。四十多岁的大儿子在南方打了二十多年的零工,至今未婚。老季搞不明白,孩子为什么不找老婆。只是秋收过后 不苟颜笑的大儿子又一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那一刻,老季心中隐隐不安,因为断断续续爆发的疫情出现,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大环境。更重要的是老季在不经意间得,这次回来,大儿子已经失业。
二儿子在上海打工,原本是准备回来帮忙收麦子的。从去年收了秋之后老季便盘算着日子。本来过年的时候二儿子打电话回来说老大不回的话回来与父母团聚。在本地做家政的老季的老婆老曾告诉儿子,今年再不带女朋友回来就不要回来了,浪费钱。你看你哥哥过年都不回来了,还是等来年麦收时节回来,帮父母做点体力活。
老季其实很反感老曾的。他了解自己的老婆,说话做事不近情理。但他明白,自己没有办法。当年的老季也是像风一样的中原汉子,一米八五的大个,俊毅的脸庞,是相当的帅。然而,由于家庭兄弟姐妹多,当时生活是相当的捉见肘。无奈之下,老曾的大哥初中没上完就早早的招了工,不久之后又去做了上门女婿,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老曾也是一个苦命的人。由于历史原因,不得不离乡背井随着同岁的本家姑姑一起逃难中原。落好脚的姑姑在附近为她寻找了好几户好人家,老季的家境是最差的,但相对于其它相对殷实的歪瓜裂枣,姑姑相中了相貌堂堂的老季。其实老曾是从内心底瞧不上老曾的,只是形势逼人,迫不得已,只能强颜欢笑的答应这们亲事成了老季的老婆。
次年老曾为老季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老曾也大体的了解了老季的一家状况。老季其实不姓季,他是随母亲与其它兄妹改嫁到季家的。改嫁的季家也不是本地的坐地户,而是弟弟跟四处漂泊哥哥安家的外来户。老季的母亲后来又生了几兄妹,却是与老季隔山的。
还好那时是八十年代,年轻力壮的老季凭力气也没有饿着老曾。并且在己出嫁的同胞姊姊的帮助下建了几间土屋,毕竟也有了安身之所,生活也算过得塌实。平淡的日子在几年后开始了变化,疾病缠身的老季母亲在垂危之中见到了老季的第二个孩子,这是个女儿。本来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儿女双全吗!不巧的是,老母亲的病花光了家中的积蓄,再加上当时刚刚推行计划生育。苦叹人丁单薄的老母亲叫来了一个己出嫁家中没有女孩的女儿,嘱咐自己的女儿象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宠着侄女的叮嘱中在大年刚过的日子里闭上了安详的双眼,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令老人家经历坎坷的人世。
老季在埋葬完母亲的过程中,望着从异乡漂泊而终究魂归大地的一座孤坟 。老季感概万千百思不解,同胞兄弟竟然没有回来出席自己母亲的葬礼。不过不重要,兄弟之间的亲情终是血浓于水,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又过了几年,老曾又生下了二儿子,并东凑西借盖了几间砖瓦屋。
平静的生活终究会被打破。当如火如荼的计划生育政策偏离正常轨道的时候,那些凶神恶煞一般的执行人员,竟然是盯上了外来户加上单门独产的老季。可想而知,老季家当时的困境是多么的痛苦。有些人家几百块的罚款到了老季这里,是十几倍的疯涨,仿佛老季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好在艰难的生活在老季的硬扛下终于扛了过来。老季一下子仿佛是苍老了几十岁,神经也变得越来越麻木了。老曾在目睹了老季的种种无奈之后,也曾经试图一走了之和一了百了。总算是在亲朋好友的百般劝说之下苟延残存。甚至于在老季深夜由于对母亲深切思念的哽咽而无动于衷,岁月无情,令人费解。
儿子大了。老季也老了。后来大儿子出去打工谋生,过了几年,大儿子又带着小儿子一起打工。再后来,两个儿子各奔西东,相同的是,依旧在打工 。家中突然冷清了起来,老曾是愈发的看不起老季,虽然不说在明面,老季心里明白,一直小心翼翼地。甚至老曾要去城里打短工,也不敢说什么。因为它知道,现实的社会,不是他能左右了的。
麦子一天一天比一天黄了。二儿子打电话说可能会回不来了。这个消息也是在城里的老曾告诉老季的。其实,老季明白的很,上海这段时间的事情,别说二儿子不想回去,就算是他想回来,也未必能回得来。老曾告诉老季,她给大儿子打电话话了,但大儿子说不想回去,就算回去也要隔离,答应会在麦收的时候转点钱回去。老季苦笑着,一脸的无奈。
麦田的对面,还是麦田,中间只隔了一条生产路。老季蹒跚地走在自家已成熟的麦田,双眼掠过老母亲的坟头。想起了城里的老曾,还有在远方漂泊的儿子,身影渐渐消失在了无尽的金黄麦之中。
不远处,轰鳴的机器打破了宁静。一年一度的麦收己然开始 ,大地上忙碌的身影到处可见。一年一度的收麦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