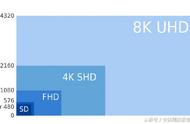在我年幼的记忆里,养鸡一直是为了收获鸡蛋。
很难想象,这些就站在我稚嫩双手之中,毛绒般存在的小生灵;将会在未来,长出一个该发功勋章般的屁股。
大概这样说,又愧对于这些有趣的小家伙。
一直不明白,为何奶奶非要在冬季买回小鸡。大约50只,装在一个上面印着苹果的大纸箱里,上面挂着昏黄的白炽灯泡。我好奇的问过,奶奶说那是为了给小鸡保温。
至于那时的我,数数才仅能刚到二十吧!
不懂就问,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我想说,就是我小时候那会儿,还有你小时候那会儿,你也应该和我一样吧?
我家的鸡舍就在院子的最里面,是用钉鞋底子那块月牙铁板剩下来的工厂废料,长长的大铁条子,钉出来带顶的小房子。那时候小,还问父亲,这是不是给我的新房子?镂空的墙充满着梦幻。
我每天都要打开纸箱好多次,看小鸡。这些傻乎乎的孩子,有几只就会非常懂事,好奇的侧着脑袋,静静的看着我。谁最漂亮,我就会伸手去抓谁,放在手心,看着它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发出呼叫同伴的声音。
也是在那时,第一次见识到死亡、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一大早欣喜的去看我的孩子们,在打开箱子的一瞬间,就看见倒在箱子里的两只小鸡。
轻轻的放在手心里,看到绵软无力的它俩,眼睛还在留着一丝缝隙中,闪烁着微弱的亮光。蓬松柔软的黄色鸡绒,也耷拉着贴在身上,一动不动像睡着了。我不敢相信,失去生命的它俩如此的轻盈。感觉如果我的小手慢慢抽离,它俩会漂浮在空中一样。
双手合十,为它们取暖,心中祈求生命,请不要离开它们的肉身。可最后,奶奶还是无情的把它俩扔进垃圾桶,在我哭死,坐在地上左右蹬腿了,闹了半天。爷爷才终于给垃圾桶里,又倒了一掀锅灰。
在我心里,好坏也是埋了它俩。
噩运连连,我的战士们,总在每天打开箱子的一瞬间,倒地牺牲好几只。这种压抑的心情,持续了好久,以至于后来的那些天,我在打开箱子前,总要祈祷一番。
终于有一天,我觉得是我的祈祷感动了残忍的上天,小鸡们不再死了,一个个略有白羽。它们也终于可以在家猫贪婪的注视下,在院子里适当活动。
可我失去了摸它们的快乐,这些小家伙根本不认我这个小大人。追它们的结果,是日后它们一见我就跑。
我也发现更遭殃的一件事,我成了地主家的童工。割草!
小小年龄的我,一睁眼就要喂养三十五张嘴。每个春夏季节,是野草最好的时候,割草并不是见草就割!蚂蚱菜、灰灰菜,鸡才吃。每天就学着大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手挎着蛋笼,一手拿着小铲子,带上草帽。(蛋笼是陕西地方话,就是大竹筐,常用来卖鸡蛋,就叫成这样)
偶然遇到一大片野菜,就感觉是得到宝藏一样,欣喜的蹦蹦跳跳过去,一顿狂铲。鸡也一天天长大,开始发出“咯咯”的叫声,开始下蛋。
真没想到,第二年的过年前,要*鸡。
地主家的儿子真坏,也就是我爸,逼着我俩看他*鸡。以后*鸡这活就交给我俩。
我和我哥第一次看着我爸下黑手,也感觉到我兄弟俩,一会儿也该洗脖子,*完鸡就要宰了我俩一样的恐怖。
如果今生定我有罪,那首*便是在我10岁那年,协助我哥,*了四只鸡。
其实,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呆若木鸡!这个成语说鸡很傻。的确要承认这一点。鸡看不懂被*。但也要否定这一点。
当时,我和我哥抓住四只鸡,放在院子里。鸡这种动物,大多数的确很傻,只会围着鸡舍跑。在我和我哥给第一只放血以后,我俩就直接开膛破肚,掏出鸡内脏,扔在旁边。可有两只鸡,就开始在那里啄食,那些鸡内脏里的玉米粒。只有另外一只,两个脸蛋都吓白了,半站半卧的站在那里,瑟瑟发抖。
很明显,它明白死亡。
所以,我和我哥,一致同意放它一条生路,换了它。
我想它一定是活的最长久的那只鸡,混在三四十鸡里,没人知道它老了不会下蛋,而我和我哥也永远不会宰它。
它和我们之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秘密暗号。就是如果抓到它,它会半撑翅膀,丝毫不会逃跑,半蹲着等你抓。
每当抓到它,我和我哥都会放开它。
看着它扭动着曾经功勋章般的肥硕屁股,就是你,看文章的那个,再不留评论,我磨刀啦!
(忽然发现,2点47分所以,赶紧乱写结尾,做梦去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