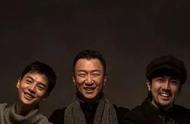文 | 杜维
那些年,国人腹内无粮,瘦肠饥悬,就对吃有了别样情结。谓之情结,不单指对食物色,香,味,形的认识。还扩泛餐食者那副吃东西的相、形、意、趣。旷日经年,多有些挥不去的记忆。
一九六三年,漫长的春荒艰难捱过。麦子黄了,在分分秒秒的焦急中,终于熬到开镰的一刻。生产队长也是饿过来的人,自然明达。下令;开镰第一茬麦子,按人头分到户下,每家的妇孺,下半晌可歇工,回家料理新麦第一饭。这对于当时的饥民,不谛是浩荡皇恩,早上开镰的麦子,一晌午晾晒,下午即脱粒,晒,扬,播,碾。好歹弄成粗粉,就能作成粗拉劲道的面条。
那天,我晚饭后去同学家串门,已是掌灯多时,夜色黑的严实。敲门,门内没有灯光,多时才有悉悉索索的响动,我大喊同学的名字,也报了我的姓名。那扇被称之为门的半截院门才打开。同学见我身边无他人,迅即把我拉进门。

院子里,黑黝黝蹲着四五个黑影,都默默地。同学问,吃了吗?这是那些年最上口的一句问候。我说我吃了。同学说家里吃面条,你也尝尝?我说我真吃了。同学进了屋,翻找了好一阵,黑影里有人说话,是他父亲的声音;柱子,我这个碗给你同学,我用蒜臼子吃。原来同学家每人一个碗,竟没一个多余的。
新麦面条,凝着春夏的气息,切的细细的腌香春芽调上蒜泥和醋,又是一样别类清香。旷日的饥肠对这些温热太亲融了,浓稠的夜幕里,漾着和煦的风,暗影里,没人说话,四五副可善咀嚼的牙口造出了许多声响;咯吱咯吱,吸吸溜溜,呼呼噜噜,然后有人打了饱嗝。饭后,我同学鼓腹而出,称自己吃了十三碗,又说;我奶奶六十了,还吃了七碗。
多年后,我一直忘不掉那晚夏夜的薰风,那薰风里的咀嚼声。我觉得那音符真的好,温馨,动听。上帝给人造了一副副好牙口,还有一些挺有能耐的人给人造了一副副饥肠,就有了这夏夜小夜曲。
好听,难忘。
壹点号山东创作中心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