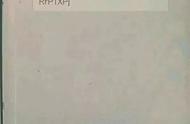1993年,金克木与邓广铭在朗润园
通人
张汝伦特别看重金克木所说,“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前些年,张汝伦看到报纸上有人发问:现在还有没有“通人”?“《泰晤士报》做了一个调查,在英国,这样的通人也就十来个了。他们的结论是,走一个少一个,不会再增加了。”
张汝伦惊叹前辈学人的修养。“我们这里有个王水照先生,他复旦毕业后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有一次,他听钱锺书先生说,找个时间,我把《十三经》温一下。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你看看,这是什么功力,我们《十三经》看都没看全,他是温一遍。这些文化典籍在他看来,是人生必须要看的东西。现在学者,做李白的做李白,做苏东坡的做苏东坡,我就做我这一块。《十三经》,对不起。他们这一代人不会这么想问题。”
张汝伦讲到了当下的新文科建设。他觉得立意是好的,但是在我们现在大学的格局下,不太可能做好。“大学里,各个系互相提防,学校里的这一块蛋糕,大家都要分嘛,自己总要把自己说得比别的系更重要。一起开课,一起交叉融合,很难。因为我们本身每个系里边,彼此讲的话已经不懂了,如果他是搞古希腊史的,那你跟他讲元史,他懂什么啊。他认为这是合法的,我可以不懂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儿,新文科要打破这一块,问题是小鸡是老鸡养的,老师对学生的示范效应是很强的,尤其是混得好的老师,学生都学着呢。”
“学科的分类是现代性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来不懂什么叫分科,卢梭和黑格尔也不会承认分科。从根本上来说,学科不是学科,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只是我们的精力能力有限,我们只能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史哲基本的东西你要知道的,坑挖大了,根才会深嘛。”
“我不瞒你说,我当年写关于金先生的文章,就是不能让别人忘记他,这就是我的一个目的,这些文字留下来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人。”张汝伦说,“金先生有一次跟我说,大家讲新儒家时,都讲熊十力,因为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都是他的学生。马一浮没有什么学生,讲马一浮的人就没那么多。后来金先生退休了,他没教过多少学生。我觉得他有感慨在里边,才会跟我说这些话。”
对于金克木给《读书》写那么多文章,张汝伦觉得是他那一代人耽误的时间太长,他急于把一生的积累和想法写出来。“肯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啊,觉得他只是懂得点皮毛,不系统。金先生不是什么都对,但他能激发人的想法,这很了不起啊。他每次都有新的东西啊。他这个年龄,不得了。金先生学不来的,是天赋和境界。这样的天赋不是一般人有的,自学成才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有天赋的人还是有的,但不要被外在的东西束缚了。后人可以做的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他播下的种子可以生根发芽,这是我的想法。”
纪念金克木先生主要纪念什么?这也是钱文忠想的问题。
“我在北大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跟金先生见面很多。只要见过金先生的人,你都会被他吸引。我特别想念他。金先生这样的人物,只有他那个时代才能产生。他是一个学术传奇,一个文化传奇。”钱文忠说,“他文凭都没有,为什么能得到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广泛尊重呢?为什么能在北大成为被大家公认的一代宗师呢?我们现在纪念金先生,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反思一下,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出现金克木。这是第一个问题。”
“纪念金先生,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反思的。”钱文忠继续说,“金克木先生的著述、翻译、论文,现在看来恐怕都不符合学术规范。你能说金先生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吗?你能说金克木先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吗?放在今天的学术评审体制之下,金先生可以说是没有学术成果的人啊。但是,他留下的著作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
张汝伦说,“我们强调专业化,他要是专业化的话,会受到人家尊崇,他要是说自己是杂家,别人可能会觉得他无非知道的多,没什么专业。我们对他的评价和他实际的成就、才气,是远远不相称的。”
1980年代,张汝伦去金克木家,天上地下,能聊很多。金克木说话,他听。“他没废话。”张汝伦说,“老一辈学者的风范现在不可及。我总觉得,这样的人,是很令人向往的。”
张汝伦觉得,他说这么多话,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多告诉别人。“他是觉得,我老了,很多东西做不出来了。他在《读书》上那些文章,把他的idea列出来,后人觉得有意思,可以顺着他的idea做下去。他的书,我觉得实际上一直被人低估了。有没有学生研究金克木的学术,把他做一个论文题目,硕士的也好,博士的也好,其实真的值得做,他代表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在我们国家很少有。”
“他老人家讲的话,不一定都对,但是这个不要紧啊,能打开思路的东西更重要,比你正确的但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信息的东西要好得多啊。真正的创新,是让人家眼前一亮。
“金先生最得意的是,有一天我去拜访他,他说有个英国人,剑桥的,做中国现代文学九叶派的博士论文,来采访他,一看他桌子上摆着德里达的书,大吃一惊,因为当时在国外读文学的人都视此为畏途,很难读的。来人问他,你到底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他哈哈大笑。这是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金克木看夫人与孙女下棋
先生
因为给杂志约稿,叶稚珊接触过许多北大老一辈的学者,其中包括冯友兰、陈岱孙、张岱年、邓广铭等等。“我跟季先生和金先生接触最多。”叶稚珊说。
叶稚珊说,“金先生的晚年很平静,他沉浸在自己的爱好里边。子女们很低调,对父母很尊重,继承了金先生那种很落地的性格。”
季羡林和金克木住在北大朗润园同一栋楼的两个单元。“季先生住在其中一个单元的一楼,一楼的两套房子都是他的。金先生住在隔壁单元的二楼。我去金先生那里,他都得不经意地问一句,你去那边了吧。我说,去了。去季先生那儿,他也问,你上那个楼了吧。我说,上了。金先生说了,他耳朵不好,眼睛不好,血压也不好,心脏也不好,不久于人世了。季先生说,哎,二十年前他就这么说。金先生身体不太好,基本不怎么出去,下楼很少。季先生住一楼,他可以出来看看荷花什么的。金先生很简朴。后来分了蓝旗营的房子,他一天也没住进去。金伯母也是身体不好,眼睛也看不见。金先生去世之前,金伯母被发现脑瘤。金伯母不工作,没有公费医疗。做了一次手术后,金先生跟我说,像抄了一次家一样,积蓄都投入进去了。你想想,金先生一个人的工资,要是家里人一场大病的话,全都给花去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很简单。印象中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韭菜饺子什么的,很普通,特别家常的饭菜。金先生家完全跟他做学问一样,随心所欲,盘碗筷,都不怎么讲究搭配,比普通人家还普通一些。我觉得是关注点不一样,他们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
将近三十年前,钱文忠去拜访金克木。“我是没见过书。金先生肯定借书来看。不像季先生,几间房间都是书。”
季羡林和金克木,这两位的名字经常放在一起,是难以避免的。“金先生跟季先生,共同创建了中国的印度学科和很多学科,在北大都是泰斗级人物。这两位老先生的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季先生有德国名校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接受了清华大学完备的教育。金先生则完全没有。一般人没有注意到他们学历的差距。大家都认为季金二位先生是了不起的学者,但是我们从这两位先生的对比,可以思考很多问题。”
“金先生离开我们22年了,真的是一眨眼,我现在都56岁了。当时初见金先生的时候我18岁。如果金先生在,金先生会怎么说?我觉得以金先生的智慧,还会用他那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笔,来写充满智慧和学术的文章。我觉得他会这么干,他一直这么做。另外,我自己也是去西方留学的学生。金先生去印度留学。今天我们研究印度学,好像没有人去印度留学了,都去美国欧洲留学。我们研究埃及学的,也是在欧美留学。我们研究好多古老民族的人,往往去欧美名校留学。金先生去印度留学的经历带给我们什么启示?你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是不是需要更接近他们呢?”
钱文忠一直致力于印度学和梵学的教学。“现在,在中国,梵文研究,印度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冷门学问了。这几年很多大学都有梵文课程,很多年轻人学习梵文,而且很有成就。这确实是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黄德海的这本《金克木编年录》非常好,我没有见过他,他寄了一本书给我,我非常认真地拜读了。我觉得这种纪念和研究金先生的态度就特别特别好。非常扎实,好多东西我根本不知道。要不是他收集整理,我们没有这么多关于金先生确切的资料。”
钱文忠觉得,看黄德海编写的《金克木编年录》,会有一种更深的感受,就是金克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读书人。“他是一个中国的士人。他是有关怀的。他可以关怀宇宙,他去学天文学。去关怀一个跟中国同样积弱的民族,他去学梵文。作为一个在印度决定了他学术生涯的学者,他和在中国占主流的那些学者和知识分子,是有明显不同的。”
黄德海将《金克木编年录》翻到靠后的位置。《秦汉历史数学》刊登的时候,金克木已进入人生最后的时日。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9至10月间,刊登在《读书》2000年第7、8期。他考察秦汉之间的承续及变化,指出高层机制运转的奥秘,兼及人才、经济、金融问题。“单就功能说,一个虚位的零对经济、政治、军事构成的三角形起控制作用。这个三是数学的群,不是组织、集体,是核心,不是单指顶尖。三角的三边互为函数。三个三角平面构成一个金字塔。顶上是一个零,空无所有,但零下构成的角度对三边都起作用。”“‘孤家、寡人’需要亲近助手,实际是隐形的稳定核心。能*皇帝如文帝、武帝会灵活运用周围的起这类作用的人,无能的就不行了,非有不可,于是他身边的能干人自然会发挥有效功能了。历史确实是数学,虽是人所创造,却不知道人的感情爱憎和道德善恶,只按照自己的隐秘公式运行。历史前面挂着从前城隍庙里的一块匾,上写着四个大字:‘不由人算’。”
这篇文章跨越了文理,充满了独特的思考,是金克木所思所想的集中写照。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去世。他说他是“哭着来,笑着走”。“金先生这样的人,现在我们纪念他,是希望中国还能出这样的人。有老师能给学生莫大的启发。引导学生走上一条创造性的道路,这样的老师功德无量啊。”这是张汝伦的期待。


金克木读信
宇宙
叶稚珊记得在金克木家看到过一张照片,他仰天大笑。“我想到他的第一个表情永远是笑,开心地笑,会心地笑。他说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发现了快乐。他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他在精神上一点都不悲观,他呈现给人的是乐观和豁达。”
在上海这家餐馆里,黄德海对于金克木的讲述也快到尾声了。他特别提醒说,他在《金克木编年录》里留了一条感情线。这条感情线是“保险朋友”。
扬之水在日记里写到过与金克木的一次聊天。“于是与我聊起了青年时期的一个恋人……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八八年,五十年啊,他说,他一生中只有这一次真正的爱情,虽然不过短短一年(甚或不足一年)。那一位就远走他乡(生活在瑞士—美国两地),如今只是一年一两张明信片的交往,倘有朝一日再次相会,真是相对尽白发了,而这种可能也是不会有的。”
《保险朋友》发表于1990年第4期《收获》。在这篇文章里,金克木相约和Z做保险朋友。“我下了决心。既然到了好像是总得有个女朋友的境地,那就交一交东京这个女同学作朋友吧。是好奇,也是忘不了她。于是写了信……又说,还是她这个通信朋友保险。……没多久就来了回信。……‘你只管把我当作保了险的朋友好了。’”“真是心花怒放。有了个保险的女朋友。一来是有一海之隔;二来是彼此处于两个世界,决不会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纠葛。我们做真正的朋友,纯粹的朋友,太妙了。不见面,只通信,不管身份、年龄、形貌、生活、社会关系,忘了一切,没有肉体的干扰,只有精神的交流,以心对心。太妙了。通信成为我的最大快乐。我不问她的生活,也不想象她是什么样子。甚至暗想她不如别人所说的美,而是有缺点,丑。”
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金克木一直保持着与“保险朋友”的通信。直到这位“保险朋友”去世。
在1990年1月24日的日记里,扬之水记下:“前些时金克木先生打电话来说,他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自日内瓦给他来信,道自觉生日无多,欲将旧日往来书信寄还与他,金恐经过海关时遇麻烦,问我有无便人。次日与老沈说了,老沈说可通过董秀玉从香港回来时带回。于是复金以信,今接来信云:‘谢谢你的信,多承关心。但我与她俱是风烛残年,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故已复信,不要将我的旧信旧稿寄来。’”
黄德海从《金克木集》里翻到了“保险朋友”的一半照片。“发乎情,止乎礼,这是伟大的感情啊。”
“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坦荡。‘她后事托我,我后事托谁?’这种自问,有一点冷酷,又有理性的成分。他是智者,这是金先生的奇特之处。”叶稚珊说,“要了解金克木,不能光读书,要读他这个人。”
耍枪杆的,耍笔杆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都见过。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对我讲着不同语言,表达不同思想。不知怎么我竟能记得住这么多人。若是电视连续剧吗,也太长了。还有什么样的人我没有见过呢?只怕是没有多少了。然而,我渐渐不懂这个世界。同样的,我想,这世界也不懂得我了。我在这世上已经是完全多余的了。
末班车可以是头班车。离开这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又是初生儿了。
“人生天地间,譬如远行客”。望见终点,我挥舞着这些小文要下车了。
这是金克木1995年写下的文字。
1936年春夏,金克木在西湖边孤山脚下的俞楼住了大约一百天。这是他一段“既闲暇又忙碌,既空虚又充实的时光”。这一百天中,他译出了一本《通俗天文学》。戴望舒来杭州看金克木,见他竟然翻译天文学,大为惊诧,写了一首《赠克木》——
你绞干了脑汁,涨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这是未读完的金克木,这是未知的宇宙。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