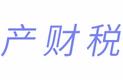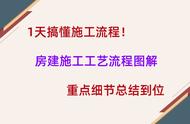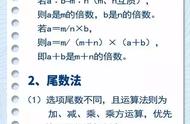韩国唐人街
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韩国早期华侨90%来自山东,而非广东、福建等南部沿海省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山东遭受了饥荒、干旱和严重的匪患导致许多人迁移到朝鲜和中国的其他地区,1922年朝鲜华侨达到高峰的10万人。朝鲜华侨多数经营农业、饮食业和建筑业,以山东省家常菜为基础制作的炸酱面便在这一时期推出,一般来说日本商人更关心的是快速获利,而中国人则是与客户建立关系,所以在与日本人的竞争中朝鲜华人取得优势。对于这些能产生大量税收的华商,日占朝鲜的政策是既利用又限制,例如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雇用华人不得超过总工人人数的1/3。
20世纪初的华侨数量并不是一直增长的趋势,而是随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据《间岛协约》日本人和朝鲜人享有租借土地务农的权利,1931年4月间地主郝勇德在没有中国政府的允许下就私自把土地租赁给朝鲜人,朝鲜人在租来的土地上修建水渠破坏了当地中国农民的农业生产,纠纷发起后朝鲜人原本准备离开,但在日本军警的教唆下矛盾激化,史称“万宝山事件”。日本人利用此事在日占朝鲜制造“中国人屠*朝鲜平民”的假新闻,愚昧的朝鲜人就这样被煽动起来发起排华运动,朝鲜华侨共计被*142人,伤546人,失踪91人,财产损失无数,在此情况下大量华侨人口降至三、四万。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后,朝鲜华侨数量又增加到1942年的82661人,二战末期随着日本的即将灭亡,1945年这一数字又减少到12648人。

万宝山事件挑事的日本警察
三、坎坷命运
1945年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被撕裂成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两个国家实行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外交政策,因此朝鲜半岛华人的命运也经历着不一样的变化。
(一)朝鲜
教育上则在初期受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帮助下,北朝鲜重建了中文教育,1949年4月,这些中文学校被移交给朝鲜政府,朝鲜政府开始努力将这些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在财政上予以支持,60年代后朝鲜开始进行本土化教育,后来受文革影响这些中文学校的学生鼓吹与“主题思想”明显不符的理论,对此朝鲜予以拒绝并关闭了一些学校,但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仍有四所中国中学采用中国的课程。
在身份上华侨被划为“外国人”获得了公民证(朝鲜公民证分为平壤居民、地方居民、外国人),并拥有了朝鲜永驻权。但是作为外国人没有资格加入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也没有资格进入军队或文职官僚机构,可幸运的是相对其他朝鲜人他们拥有较大的“自由”。例如有权拥有一台不被封锁的收音机,只要不在朝鲜人面前听不该听的即可,80年代他们还被允许出国旅行参与进出口业务,90年代朝鲜正经历“苦难的行军”的时候朝鲜华人利用这一便利搞倒爷,因此生活水平要较其他朝鲜人高。

“苦难的行军”
可惜这个“自由”不是永久的,朝鲜政府对待他们就像与后者祖国的“微妙关系”一样,由于2009年联合国安理会对朝核行为予以制裁,朝鲜华人开始被“保护”起来,许多华人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干脆不出国,2014年朝鲜当局为了防止“外界信息流入”和“内部信息流出”加强了对华人的“保护”措施。
数量上二战结束后在朝华侨有1万余人,除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数字一度增长到2万多人,后来人数陆续有所减少,60年代的时候由于中朝关系的变化所以朝鲜鼓励华侨要么加入朝鲜国籍要么返回祖国,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华侨归国定居的审批开始放宽,同时将归侨人数的安置作为任务指标下发给各侨务办,因此80年代有数千朝鲜华侨回归中国,1989年归国审批有所限制使得下降速度有所减缓,到21世纪初在朝华侨人数估计为几千至一万人。

朝鲜安全机构“国家保卫省”
(二)韩国
由于韩国在建国时与中国不愉快经历使得在韩华人过得并不顺利。虽然清末民初时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华人居住在朝鲜南部,且国共内战时期这里的华人也一度处于上升趋势,但朝鲜战争后韩国政府开始对在韩华侨施行“边缘政策”后华人数量不断减少,特别是朴正熙时期的韩国虽有“汉江奇迹”的成就,但华人的数量却与经济增长呈反比趋势,这是由于“民族主义”不仅 是维护独裁者统治的惯用伎俩也是韩国发展经济的精神动力。
朴正熙针对华人的限制主要在固定资产和餐饮业,1971年大韩民国政府实施了《外国人土地获取和管理法》,允许外国人(韩国华人与朝鲜建国初期的华人一样没有国籍)一户拥有200坪以下的一套住房和50坪以下的店铺,这意味着华人生意无法扩大,若要说前条法律是针对所有外国人,那么后来的法律则是赤裸裸地针对华人,1973年政府以奖励面食为名禁止华人煮米饭,而华人主要的营生便是餐饮业,米饭则是华人餐馆的主要食品。受到打击的华人陆续移居到美国和台湾等地,韩国华人数量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下降了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