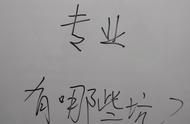结婚17年,丈夫突然离世,我发现,丈夫的手机通讯录备注,藏着太多秘密。
我的妈妈是鲨鱼,他的妈妈是乌鸦,一个陌生女人是饕餮。
直到看到了自己的备注,那两个字,让我觉得自己特别悲哀。
丈夫的手机通讯簿里,杜安静的名字不叫作杜安静,叫作狻貌。
不是母老虎、黄脸婆或是孩儿他妈,不是一切有关伴侣或是怨偶的称呼,丈夫挑选的是一种古书上的动物,压根儿未曾真实存在过的物种。
这是一件极其令人费解的事。当然,在杜安静暗流汹涌的婚姻生活里,不过是小菜一碟。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杜安静是在丈夫死后才发现的。
那天,是丈夫的头七祭奠。杜安静和孩子在小区外的空地摆上香烛果物。没有风,烧纸成灰,在低空盘旋不去,犹如贪恋人世的亡灵,在灰暗下来的暮色中,迟迟不肯离散。杜安静就有些发慌,叫上孩子,匆匆朝家走,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下意识地拨打一个号码。
包里的另一个手机却响了起来。杜安静一怔,旋即反应过来,她拔的是丈夫的电话。这个男人故去以后,按照习俗,身外物尽数焚烧,唯有手机,杜安静信手放在了包里。手机不时会响,她录制了一段自动语音,告之对方手机主人亡故的事实。噩耗传递得很迅速,手机几乎不再响起。但她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充电,像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履行着某种睡前仪式。幽暗漫长的夜里,丈夫的手机与她的手机在插线板旁并排放置,缄默、沉寂,同床而异梦。
她掏出丈夫的手机,诡异的字眼瞬间扑进她的双眼。可笑的是,她竟然没能第一时间准确地辨识出这两个字。她在自己的知识结构里搜寻了一遍,找到了一些诸如狐狸、猿猴、狸猫之类的词语,就是没有狻猊。她不认识它。它的读音,以及它所蕴含的意义。
铃声停止。她将信将疑地点开,在狻猊的词条下面,显示着她的号码。那一串数字熟悉得就像她自己,像她身体的一部分。
事后,杜安静一直想不明白,在那个天色灰沉的黄昏,她何以会鬼使神差地拨打丈夫的号码。事实上,在他们共同度过的最后十年,她甚少拨通这个男人的电话。需要援助的时刻,她的求援名单排序依次是:第一,她自己,第二,警察。绝大部分时间,排序第一的人物就能解决所有的麻烦和问题。
不久以后,在一次聚会上,杜安静向老李出示了这个词语。那是闺蜜们的例会,杜安静不是收藏家,但她鬼使神差地成了一个收藏圈儿里的座上宾,一群有钱有能耐的中老年女性操持着每月一次的相聚,准时得就像少女的月经。聚会通常是在一间茶艺馆里举行,那里有古树普洱,有琴女,有做得一手精致小菜的厨子,茶艺馆的老板娘是热衷于社交的字画收藏者。
老李是聚会里唯一的男人,男闺蜜。他迟到了一些,众的话题刚好停留在撒谎是男人的天性,还是后天习得这样一个半哲学半伦理学的范畴上,于是老李被推到了激流中央,他被要求从男性视角做陈述。老李抓耳挠腮,杜安静救下了他。杜安静不动声色地将题目转换到了健康管理方面,就像对垒中的一颗球,立刻就有队友热火朝天地接了过去。
老李坐在了杜安静身边的空位上。杜安静闻到了他衬衣上散发出的浓烈的消毒液的气息,跟她一样,老李的职业也是公务员但他时常被误认为是大夫。
杜安静找服务员要来纸和笔,写下了狻貌,递给老李。老李的眉头使劲儿地皱了起来。半晌,琢磨无果,起头,他一头雾水地挤出一句:甲骨文9?
杜安静侧身答复了一句朝向她的问题,等她转过身来,老李向她出示了手机百度里的词条:狻猊是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形如狮,喜烟好坐,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杜安静瞥了一眼,说,我查过了。
这是个新鲜词儿,从哪儿看到的?老李盯着她。
你会这样叫你老婆吗?杜安静保持着莫测深高的表情。
他......这样叫你?老李迟疑了一下。
没有人留意他们在谈些什么,在最近的聚会中,杜安静被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死了男人,高谈阔论不相宜,她可以随心所欲地静默或是游离。
杜安静没有回答老李,她突然丧失了继续聊下去的兴趣,她加入到了兴致勃勃的女人们当中,点评一部热播剧里的小鲜肉小鲜花,尽管她根本没有看过那部剧。
她能感觉到,一整晚,老李都用若有所思的眼神注视着她。这个圈子,是老李把她带进来的,有个核心人物的姑娘考进老李所在的单位,老李出了不少的力气。除此之外,倒是没什么利益关系。老李甚至不太喝茶。一开头,大家老拿他俩开涮,后来发现他们中规中矩的,毫无槽点,也就不怎么上心了。
说起来,她和老李的关系,还真不纯洁,更不是男女授受不亲。如果用化学课上的量杯来衡量,应该就是比蓝颜多,比情人少。
若干年以前,他们有过短暂的肉体接触。准确地说,是在杜安
静婚后的第九个年头,那一年,她34岁。老李比她还要大两岁。老李单身。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在一次培训中,他们碰巧分在了同一个小组。
那时候,杜安静与丈夫已经是相看两相厌的状态,他们的无性婚姻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老李的出现,给杜安静一地鸡毛的苟且生活带来了诗意,也带来了远方。他们的性爱激烈得一度让杜安静颠覆了三观,以为这才是把日子过下去的本钱。
在那个花事纷繁的春天,杜安静重新变成了一棵汁液丰沛的树,在风里,微微招展。杜安静喜欢那样的自己。她提出了离婚。
丈夫立马就同意了,甚至没有追问情由。可是,双方的母亲坚决反对。这两个老太太,从来都在敌视中对峙,都嫌对方不够阔气,彼此的政见从来都是南辕北撤으。而这一回,在离婚这件事上,居然出人意料地建立了统一战线,同时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老土手法。同时,俩老太太搬出了孩子,俩老太太设了个局,扬言他们一旦离婚,孩子就跟着外婆和奶奶,他俩谁都抢不着,连面都不许见。
末了,杜安静不离婚了。她的放弃,倒不只是因为母亲与孩子,当她陷入离婚的硝烟之中,老李正张开双臂,迎接着姗姗来迟的姻缘。
丈夫固然是凡夫俗子,老李亦非天神下凡,他享受着与已婚女子的调情,却绝不耽误自己的终身大事。婚礼当天,杜安静想都没想,就送去了一份厚礼。毕竟,老李曾经给她黯然无光的世界带来了片刻的光亮。她把爱情的幻觉埋在了泥土里,从温暖的大地中,萌生出了一个善意的存在,那就老李。
她那只慷慨的大红包,让老李解除了武装。他们竟然正正经经做起了朋友。那种真正吃饭喝茶聊天的知己,还常常是一大群人,他们相互进入了对方的朋友圈。肉体被彻底清场,他们再也没有滚过床单。
每次见面,老李总是按捺不住倾诉的*,他向杜安静诉说,也向别人诉说,这样,老李的家事渐渐被所有人知晓。高大挺拔的老李成了被同情的主儿。
老李的婚姻就是一个买一送一的坑,妻子倒是个傻白甜,温柔美好,附赠的却是魔鬼附体般的丈母娘,关键是,这赠品还不能随手扔掉,根本就是商品的一部分。
杜安静熟知老李生活中每个荒诞不经的细节,自然,这些与她毫不相*细节,不足以支撑起他们长久的交往,比这更重要的是,老李在她提升的关键环节拼力拉过她一把,现在,她的行政级别已经越过了他。在职场上,他们心心相印、相互搀扶,这比肉欲、比精神的交流都要来得持久与稳固。
聚会的尾声是例行的新茶品鉴,杜安静尝了一口茶艺馆新推出的古井水泡茶,突然来了一句:我说老李,你身上那味儿,无论我喝什么茶,都像加了消毒水儿。
众女哄笑不已。老李笑了,杜安静也笑,她想的是,这个内容密集的夜晚,已经将狻猊拒之门外。呵不对,它终究还是如影随形地缠上来了。
在纵情大笑的刹那,杜安静看见了一团小小怯怯而又坚定不移的暗影。那是狻猊,它从丈夫的手机里爬了出来,与她四目相对。杜安静慢慢收起了笑容。
狻猊到底象征和隐喻着什么呢?杜安静与老李有过第二次探讨。从头发到鞋尖都一尘不染的老李来到杜安静办公室,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来。门敞开着,看上去他们像在本该休憩的午后加班商议某项工作。
情况还好吧?
「不太乐观,呼吸肌衰竭,昨晚抢救了一次。
他们的对话像黑话,其实说的是老李的妻子。那个贏弱得像根枯草一样的中年妇人,如今正躺在一间三甲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她是半个月前住进去的,在那以前,她以同样的姿势躺在自家的床上,足足躺了五年。下半身和上半身一样丧失了神经感官,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包裹在一种叫作「包大人的尿不湿里。医学上把这叫作植物人。杜安静觉得这个名词有待商榷,显然植物被人类的主观臆断给强奸了,谁说植物就一定是无知无觉的?老李的妻子比植物还不如。
这五年,老李经历着无性婚姻,经历着杜安静已然煎熬过的一切。不同的是,杜安静的无性婚姻比老李长一倍,十年。在这一点,老李是强大的弱势群体,他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委屈。就连收藏圈里的姐姐妹妹们都拿这跟老李开涮,老李也毫不讳言,他加入姐妹淘就是为了沾沾雌性激素,以免直男癌上身。
不随时瞧着你们这帮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往后我都不知道啥叫女人了。老李这样说。他是个懂得自我调侃的男人。
老李的无性,是在明处,杜安静的无性,却是在暗处,除了她和丈夫,无人知晓。两人心照不宣地坚守着这个秘密。这个秘密如同卷心菜,每一层里都裹着更深的秘密。剥开第一层,杜安静发现了狻猊。
为什么是狻猊,而不是别的什么动物呢?老李自言自语着。杜安静期望能从他那里找到答案。他是男人,男人更能窥测男人的内心,不是吗?
据我所知,两口子的昵称无非是兔子啊、狗熊啊什么的,也许他想标新立异?老李点燃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朝烟灰缸里弹弹烟灰。
丈夫不是标新立异的人。他只是普通的路人甲。
给我一支。杜安静说。
老李有些诧异,慢慢掏出烟盒,抖出一支。杜安静接过来,就着老李递上的火,点燃。老李转头望望走廊,敞开的大门外,空无一人。
复吸了?
杜安静不置可否。她的烟龄跟她的无性婚姻长度一致。有一阵子,她抽得很凶,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还被群众提了意见。她下狠心戒掉了。老李送过她不少戒烟糖,她还因此而胖了好些。
不过,叫什么都有理由,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你这茬儿,这几天我倒想起来,刚结婚那阵子,我叫她小猪来着,你知道,其实她比一般女人都苗条,我没道理那么叫,但我就想那么叫,叫着心里舒坦﹣一总的来讲,在他离开前的这些年,你俩还算恩爱,对吧?老李望向杜安静,他的这个判断用了反问句。老李应该质疑,毕竟他睡过她,红杏出墙不是幸福婚姻的常态。
还好。杜安静淡淡地说,她掐灭了大半支香烟。她有足够的自制力。
午后的慵懒袭击了老李,他抽完烟,从随身携带的杯子里喝着决明子水。他有轻微的高血压。窗外明亮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叶,大片大片地投射在室内,光芒太过强烈,那种炫目的感觉,到像是灰黑的阴影,遮敝了双眸。
老李掩嘴打了个大大的呵欠,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杜安静有些失神,眼前的一切变得恍惚。每当他们心平气和、无欲无求地谈论着各自的人生与爱情,她老是会怀疑他们是否真的上过床。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说到底,杜安静的性经验相当贫瘠。她不是外貌出众的女人,性情里尚有阴郁的一面,纵然她竭力呈现出理性和智慧,连同一点点的俏皮,但对于雄性动物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在她当上副局长以后,她与男人的交际更是规范在了三个界面,上级、下级、同级。男人失去了性别,他们是她的同盟、属下或是竞争者。
除掉丈夫和老李,她只剩下一场风花雪月的初恋。那会儿她刚过二十岁,高中毕业以后,在老家的村小做代课教师。老家的小镇属于高海拔地区的低海拔地段,那个男孩儿在镇里的邮局工作,是藏族人。作为一名奔波在四千米高原的邮递员,男孩的交通工具只能是一匹马,一匹棕黑色的烈马。在少女杜安静看来,坐在马背上,依偎在男孩宽厚炽热的怀抱里,穿过雪山与草地,穿过不同纬度的植被,在煮着酥油茶的帐篷里男欢女爱,这样的情景浪漫就像好莱坞的大片。
这段恋情被杜安静的母亲挥刀斩*。母亲坚决反对这个骑马的男人,在跟杜安静的正面冲突宣告失败以后,她曲折迂回地为杜安静带来了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这个男人毕业于北京的名校,是一名硕士研究生,他是在完成了一次骑车旅行之后,搭乘长途汽车,前往省城的一所高校报到的时候,遇见了杜安静的母亲。母亲在车站对面开了一间杂货铺,这个头顶硕士与大学教师双重光环的矮小男人驮着沉甸甸的行李,他要把自行车、行李还有他自己一块儿塞进长途客车。这就超载了。他被要求给自行车和行李单独买一张票。他没带够钱。于是,他来到杂货铺,打电话找朋友借钱。他在本地的朋友外出了,他没有借到钱。但是,杜安静的母亲借给了他。母亲以一个猎人的敏锐,捕捉了这头外表木讷的猎物。
母亲赢了。学历的海拔超越了自然的海拔,这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战胜了骑马的男人,成了杜安静的丈夫。若干年后,那个藏族男人主动联络过杜安静,其时他已不再是邮递员,转行做起了虫草生意,荷包里的钱充实了起来,打算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杜安静所在城市的高价私立中学。找到杜安静,正是咨询学校的事情。他领着妻子、孩子,与杜安静一道,在一间藏式餐厅吃了顿饭,付账的时候,他以绝对的身胚优势完胜杜安静。多年以后的重逢,没有荡气回肠的悔意,唯有令人惊奇的陌生。杜安静一边客客气气地寒暄着,一边在心里想,起码在拆散他俩这件事上,母亲是对的。那个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藏族女人,看起来与他是多么的般配,而她,当初那个脸色苍白、纤细敏感的文艺女青年,完全是另外一种不搭界的生物。
她的婚姻,一度是家族里的神话,灰姑娘穿上水晶鞋,嫁给了王子。杜安静高攀了省城的高级知识分子,调到了省城工作,一步一步,从职员登上了领导的宝座。副局长与大学教授,一对神仙眷侣。没有人知道,门扉紧闭以后,他们形同陌路。
「有没有查查通讯簿里别的女人叫什么?」老李突然问。「当然,」她说,「查过,每个女人,都不叫自己的名字。」老李好奇地盯着她。「他的母亲,叫乌鸦。」「乌鸦?」老李嘎嘎地笑起来。「我的母亲,叫鲨鱼,」她一本正经地说下去,「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叫作饕餮。」她隐去了一部分,丈夫的女上司女同事们,以各种各样的动物命名。「这都是什么意思呢?」老李用指骨轻敲桌面,蹙眉沉思,「狻猊,坐在香炉上的动物,够高冷的,香炉———神龛,」他两眼发亮,两掌相击,露出胜利者的表情,「就是这个,坐在神龛上的妻子!太他妈的有意思了!」她悚然一惊。母亲到来的时候,跟以往一样,没有事先打招呼。杜安静开会开到一半,接到电话,只好让老李跑一趟,去高铁站接回母亲。在公车私用方面,她很审慎,宁可麻烦老李。下班回家,母亲已经做好饭,油腻腻的家乡菜,咸得像打死了盐贩子,杜安静血脂超标,不过略动一动筷子。母亲不满了。
「瞧你把日子过成什么样了?!」母亲的嗓门儿巨大,她的话像是一辆从远处轰隆驰来的火车,迅速地在杜安静体内引发隐秘的震动与战栗,「冰箱里像样的东西全都没有,你是出家了还是打算殉葬去?猪肉,猪肉没有,牛肉,牛肉没有,啥肉都没有!你都吃什么?就那几片青菜叶?你把自己当蚕子养?得亏老李搭我去了趟超市,什么都给你买齐了。我问老李了,他老婆也就数着手指头的活头了,我看你这个朋友不错,忠心耿耿围着你转悠了这么多年,等了你这么多年,现今你落单了,他也快了,他这总算是要把你给盼着喽!」老李在等她?杜安静差点一口汤喷出来,母亲要是知道自己早被老李抛弃过,估计得吐血。不过她什么都没有说,就让母亲以为老李是她的不贰之臣吧,老人家都是靠梦想活着的。
「去超市,老李要给钱,我拦着,没让,」母亲继续说着,「你俩还不是一家人,不能用人家的钱———不过,我这次来,你弟弟专门给我办了张银行卡,不让我带现金回去,不安全。」说着这番无厘头的话,母亲正使着吸尘器,一会儿在卧室门口探个头,一会儿又站在厨房门边,她的话语被房门与吸尘器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纷飞如雪。有一瞬间杜安静甚至产生了错觉,似乎进入了异度空间,有若干个被复制的母亲,从各个房间,以各种角度,上天入地、无孔不入地要着钱。杜安静从母亲零乱的语言中搞懂了状况,母亲是来找钱的,要一大笔钱。老家的弟弟头胎生了女儿,母亲想抱孙子,弟媳妇生二胎的条件是在县城买套复式房。母亲瞅中了杜安静的房子,杜安静在省城有两套房,其中一套小户型,卖了,给弟弟买房刚够。「那不行……」杜安静虚弱地说,她从小接受着「家里穷」和「一定要照顾好弟弟」的洗脑式教育,拒绝母亲接济弟弟的任何要求都像是忤逆不孝。「有什么不行的?」母亲声震屋瓦,「他走了,老李又还没跟你怎么着,房子都是你一个人做主!你说卖就卖,你说钱给谁就给谁,谁还敢说半个不字!」「我明早开会,得加个班,改改讲话稿。」她借故溜进卧室。从前,对于母亲的要求,她几乎有求必应。但这一回,她心里堵着。短信提示音响了,是老李。老李问她,你母亲让我明天去你家吃饭,我去还是不去?杜安静写了一条,给你岳母知道了,不得上门来揍我?临了删除掉,重新输入了简单的三个字,别来了。老李回复,好的,那你帮我编个理由。杜安静关了手机。她想着母亲的称谓,鲨鱼。鲨鱼是凶狠的、吃人的动物,胃口还不小。在丈夫眼里,岳母是这样的形象?结婚不久,杜安静跟随骑自行车的硕士老公调到省城工作以后,母亲前后脚就领着未婚的弟弟跟来了。理由是弟弟从没来过省城,想各处逛逛。这一逛,就逛了小两年。丈夫住的是学校分配的筒子楼,单间,卫生间公用,厨房就在走廊里。房间被一条布帘子隔开,母亲睡行军床,弟弟打地铺。母亲和弟弟摆出了长住的架势,母亲的逻辑无比严密,弟弟是骨肉亲情啊,是,这孩子是有那么一丁点儿不成器,那又怎么样?
弟弟确实不是坏孩子,不偷不抢,就是懒惰,身体里像是蛰伏着一根粗壮的懒筋,四面八方地蔓延开来。看电视、睡懒觉,平生的嗜好就这两样。漫长的白昼,他就呆在屋里,电视的音量开得很大。丈夫只好把备课的地点改在了屋顶天台。丈夫的所有用具,都被弟弟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好一点儿的外套、新袜子、剃须刀,全被弟弟占据了。与弟弟的大大咧咧相比,性事的严重压抑,才是丈夫真正介意的。杜安静隐晦地向母亲表达了不便,母亲顿时就奓毛了:「你看看那些戏里演的,人家就算当上了贵妃娘娘,也要提携提携自家兄弟,你瞧你这,不就是到城里来了吗?还什么都不是呢,这就不认你弟弟了?」母亲的奚落让她无所适从。但同时,母亲也做出了改变,一到晚上,就拖着弟弟出门溜达,溜达到深更半夜才回来。
有一回下大雨,杜安静和丈夫赶紧带着雨伞出门找他们,刚推开门就发觉母子俩哪儿都没去,就靠在过道的蜂窝煤炉子旁边打盹。这幅惨淡的图景让杜安静充满了犯罪感,她和丈夫不约而同地过上了游击队员的生活,他们把做爱的地点改在了电影院、小旅社,甚至是丈夫学校的操场。丈夫怀里揣着结婚证,随时应对校园稽查队的突击检查。杜安静的新婚生活过成了一坨注水的沙袋,无比沉重。母亲高高扬起结实的铁鞭子,驱赶着女儿,让她给弟弟找工作、找女朋友。找来找去,身无长技又好吃懒做的弟弟在城里没法儿立足,杜安静就帮他回老家的小镇栖身,在镇里为他买房子,找门路扶持他做起了小生意,筹钱助他娶媳妇,随时随地解决着他一家老小扑面而来的各种闹心事。
这么多年了,杜安静一路跌跌撞撞地拖行着自己的家庭以及弟弟的家庭,仿佛一匹同时拖行着好几辆马车的老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扑地而亡。还是不够。母亲对女婿的不满与日俱增。她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女儿好不好,关键看女婿。」母亲老是对比着女婿与儿子的生存环境。女婿在车水马龙的省城当着体面的大学教师,儿子在四面环山的小镇守着水果摊儿。女婿住进了带电梯的公寓楼里,儿子想把进货的拖拉机换成货车,姐夫给钱就那么磨叽那么不爽快。女婿领着老婆孩子乘飞机去泰国看人妖,儿子快当爹了,姐夫怎么就不肯痛痛快快掏钱负担产妇的营养费、手术费?女婿过得多好啊,他过得好,他就有责任让小舅子跟他一模一样地好,否则,就是他的错,他就是狼心狗肺,就是无情无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