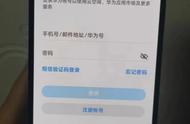《哭泣的游戏》
网红心理学家齐泽克在《快感大转移》一书中分析这部电影时写道:正是爱情的不可能性证明了爱情的无条件性。吉米并不是被迪尔慢慢地「掰弯」,在影片里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直男,他只是痴迷于永远不会完满的「完满之爱」本身。
在《刘慧芳》中,夏顺开其实就相当于吉米,而纯洁的刘慧芳就相当于迪尔。夏顺开鄙视她的虚伪、死板、无能,正如吉米鄙视同性恋,他绝不会爱上刘慧芳,他追逐的正是这种「不可能的爱情」本身:
刘:「夏顺开,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明知道孩子们准备逃学,不但不与制止,还包庇她们。今天上午我见过你两次,你只字未提。」
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小芳是你的孩子呢。」
刘:「别人的孩子就可以放任不管么?别忘了这里还有你自己的孩子。什么理由不充分?逃学根本理由!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这样作父亲的,真让我难以置信。」
夏:「是的,我知道我错了,刚干就知道错了,后悔莫及。」
刘:「认错倒是很痛快,可危害已经造成了。不客气地讲,说你是教唆犯也不为过。」
小说中,刘与夏的这段对话非常突兀,带有大段「上纲上线」式的「文革」用语,并不符合九十年代的氛围。表面上这是二人在讨论教育孩子,实际上却是在调情。
夏非但没有「批判」这套已经发霉过时的「文革」语调,反而顺着刘说,渐渐地为之吸引,在小说后面甚至想要强奸刘——对于在「文革」中度过了青春期的男孩来说,刘慧芳这种「假正经」的女孩其实是一个很有精神分析色彩的形象。
而《渴望》里刘慧芳之所以不嫁宋大成选择王沪生,嫁给王沪生之后又不顾丈夫反对坚持收养刘小芳,本质上是与夏顺开一定要娶她是一样的:夏顺开需要在刘慧芳身上验证自己的「玩世不恭」,刘慧芳也需要在王沪生和养女身上验证自己「温柔善良」。
正是为王沪生在工人阶级看来是穷酸无能的,刘慧芳才会爱上他。而从宋大成这个类似《芳华》中的刘峰的角色身上,刘慧芳实际上看到的是另一个自己:用表面的无私奉献来控制他人。
为什么「女德」这么传统的东西会在那个最革命的年代里全面复兴?考虑到刘慧芳实际上被革命剥夺了一切个人的属性,那么就不难理解了。她对爱情和家庭的「渴望」说穿了就是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竭力抓住一点可以被自己独占的事物而已。
如果只将「女德」理解为男性*规训主宰的结果加以简单的解构实际上是很粗暴的。对一个已经被剥夺了一切的女人(也包括那些为刘慧芳奉献了大把眼泪的观众)来说,想要占有一点确认自我主体价值的东西,是非常可怜可悯的初衷,而不是愚昧无知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场旨在消灭个性、整齐划一的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即使在完美的道德偶像心底也依然涌动着无法磨灭的自我满足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