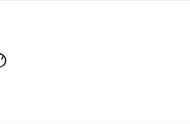诗人臧棣曾经说:“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和它能相媲美。”他为之感叹的这首短诗就是《萧红墓畔口占》,作者是“雨巷诗人”戴望舒。

雨巷诗人戴望舒
1
萧红和戴望舒的交往始于1939年初,那时候萧红和端木蕻良住在四川省巴县歌乐山上,萧红在家写作,端木蕻良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上课地点在重庆市菜园坝,那里是西迁的复旦大学的分部。戴望舒自1938年夏主编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以来,向国内名作家广为约稿,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也是戴望舒的约稿对象。萧红接到约稿信后寄去了小说《旷野的呼喊》——这篇小说完成于1939年1月30日,戴望舒安排在1939年4月17日至5月7日的《星座》上刊出。至此,萧红一发不可收拾,1939年又在《星座》发表小说、散文四篇,分别是《梧桐》、《花狗》、《茶食店》和《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端木蕻良则在《星座》发表了长篇小说《大江》,1939年3月16日至1940年1月19日连载。戴望舒经常写信给端木蕻良催稿,希望《大江》连载不要中断,端木蕻良写到第七章时病倒了,不能动笔,萧红想到戴望舒信里的嘱咐,不能误事,就替端木蕻良写了一大段。可以想见,萧红、端木蕻良和戴望舒的书信来往有一定密度,可称是没见过面的朋友。
萧红和端木蕻良准备离开四川北碚,商量去向时,之所以选择了香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在香港有戴望舒这个朋友,他们可以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文章,解决生活问题。
1940年1月1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自重庆乘飞机抵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的金巴利道纳士佛台(今诺士佛台)。在这里租房的原因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请端木蕻良为设在香港的大时代书局编“文艺丛书”,大时代书局设在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金巴利道纳士佛台离乐道很近,700米,住在这儿很方便。能到金巴利道纳士佛台租房,当是大时代书局职员予以了协助。大时代书局是孔令侃出资委托孙寒冰开办的,并由孙寒冰全权管理,当时孔令侃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主管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大时代书局资金雄厚,甚至可以为作者预支版费,端木蕻良为大时代书局编书,有编书费,出版自己的书和萧红的书还有版费,可以维持在香港的生活。由于孔令侃不干涉书局事宜,“孔家”的大时代书局倒出了不少好书,也是奇事一桩。萧红、端木蕻良住下不久,戴望舒就来探望,并接萧红、端木蕻良渡海到港岛,去他在薄扶林道的家“林泉居”做客,戴望舒得知萧红、端木蕻良到港应该是端木蕻良告知的。“林泉居”在坚尼地城半山,树林茂密,泉水潺潺,环境幽雅,戴望舒的妻子穆丽娟热情地接待了萧红和端木蕻良,穆丽娟比萧红小六岁,温柔沉静,她很喜欢性格爽朗的萧红,提出来让萧红、端木蕻良搬到“林泉居”来住,但萧红、端木蕻良刚租了房子,不好就搬走,端木蕻良又有关节炎,不能爬坡,萧红便婉拒到:“还是过一阵子再说吧。”1月底,孙寒冰来香港为复旦大学办事,告诉萧红、端木蕻良大时代书局隔壁有空房,主张他们搬过去,萧红、端木蕻良就搬过去了。新居在乐道13号或者8号,13号是《财政评论》杂志的社址,这个杂志也是孔令侃办的。13号在8号大时代书局斜对面,住房对面是《财政评论》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不常来,可以使用电话;8号是大时代书局所在,租了三间房,一间办公室,一间职工宿舍,一间是总经理卧室;萧红、端木蕻良搬到8号可能性大些。无论住在8号或者13号,端木蕻良上班都近,萧红、端木蕻良还可以方便的使用电话,一切都很便利,于是,萧红、端木蕻良也就不提搬到“林泉居”的事了。

林泉居 80年代卢玮銮摄
萧红到香港的消息在媒体上首次披露是在1940年1月30日,香港《立报》副刊《言林》“文化情报”称:“端木蕻良,萧红,日昨由内地来港,暂寓九龙某处。”《言林》的主编是叶灵凤,叶灵凤是戴望舒的好友,萧红到港的消息是戴望舒告诉叶灵凤的。按照这则消息,萧红、端木蕻良是1月29日到港,但端木蕻良在1941年的文章《纸篓琐记》中明确写到是1月17日到港,在没有别的依据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说法不得不被采信。也许戴望舒是在29日告诉叶灵凤说萧红来到香港了,叶灵凤误认为萧红是29日到港。但据端木蕻良侄子曹革成说,端木蕻良讲过因为香港局面复杂,他们低调来港,为混扰当局注意,故意说是29号到。
2
萧红、端木蕻良在香港和戴望舒的往来是比较频繁的,从香港报纸能看到的相关情况如下:
1940年2月3日,戴望舒在《星岛日报》发表消息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定于五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假座大东酒家举行叙餐会,招待新由渝来港之作家萧红、端木蕻良”。2月5日,香港文协举办的全体会员叙餐会如期进行,四十多人莅会,萧红、端木蕻良在会上发了言,戴望舒、叶灵凤参加了聚餐会。
1940年4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举行本年度会员大会,到新旧会员六十余人,会议下午二时开始,六时结束,选出本年度理事十四人。萧红、端木蕻良、戴望舒、叶灵凤参加了大会。
1940年4月23日,戴望舒在《星岛日报》发布消息《总会来函》,消息“附已在总会登记之留港会员名单”,有许地山、端木蕻良、萧红、戴望舒、叶灵凤等,总会告知香港分会安排会员登记。
1940年8月3日,戴望舒在《星岛日报》发布消息《今日鲁迅六十诞辰 港文化界开会纪念》,消息称:“纪念大会下午二时在加路连山孔圣堂举行,萧红女士报告鲁迅先生事迹。纪念晚会下午七时半在加路连山孔圣堂开演,公演集体创作《民族魂鲁迅》一剧,该剧由文协、漫协同人集体创作集体演出。”

萧红在鲁迅纪念大会上报告鲁迅先生传略
1940年8月4日,戴望舒在《星岛日报》发布消息《纪念巨人的诞生 加山孔圣堂昨天一个盛会》,消息称:“昨天的天气虽是这样恶劣,大雨如注的倾下,然而赴会参加纪念的人,并没有因此减少。三时开会的时候,三百多赴会者一同的肃静下来,许地山先生的开会词,萧红女士的报告鲁迅先生传略,张一麒先生的讲演,徐迟先生的诗朗诵以及长虹歌咏团的唱纪念歌,每字每句都抓着了听众的注意力”。据冯亦代回忆,这次盛会的办理登记、接洽会场等巨细事情都是戴望舒承办,筹备期间,费尽心力。
1940年8月下旬,萧红将她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交给了戴望舒,戴望舒安排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自9月1日到12月27日连载。
1941年3月26日,萧红的一篇背景为皖南事变的小说《北中国》由戴望舒在《星岛日报》刊发,到4月29日连载完毕。
另外,1940年和1941年,端木蕻良也有四篇文字经戴望舒之手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刊出,即《蒿坝》、《论阿Q》、《单表<六师爷>——从小市民说到新水浒》和《北风》。
1941年6月1日,周鲸文、端木蕻良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时代文学》创刊号在香港出版,戴望舒被列为《时代文学》的“特约撰述人”,创刊号上载有戴望舒翻译的法国作家圣代克茹贝里(即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绿洲》,文后有戴望舒写的作者简介,曰:“本篇作者圣代克茹贝里是法国著名的航空小说家……他写的不多。……可是他的每一部书都给予我们以新的感觉,生活在星光,云气和长空之间的人的感觉。”这是戴望舒应端木蕻良之邀所供稿,是对端木蕻良编辑文学刊物的支持。《时代文学》筹备期间,萧红积极地给端木蕻良出谋划策,帮助拉稿,戴望舒一定是萧红、端木蕻良首先依靠的朋友和作者。端木蕻良作为大时代书局的编辑,还曾约戴望舒写一本《诗坛随想录》,戴望舒答应了,并告诉端木蕻良他正在翻译一本外国的《诗论》,端木蕻良说那好,这两本书一起由大时代书局出版。端木蕻良说大时代书局出过戴望舒的书,但目前还没发现。
由于萧红和戴望舒都去世早,两人没有留下关于他们往来的文字,他们之间具体的往来故事就湮没在历史长河里了。

1941年12月8日8时日机轰炸香港
3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了香港,其时萧红身患重病,深受惊吓,无药可医,在兵荒马乱中,又被养和医院误诊做了喉管切开术,于1942年1月22日逝于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年仅31岁。萧红之死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否则她绝对不会走那么早!
戴望舒当时应该知道萧红去世。端木蕻良埋葬完萧红后,准备离开香港,碰见了叶灵凤,端木蕻良告诉叶灵凤说萧红已死,埋在浅水湾。叶灵凤和戴望舒是好友,理应告知这个消息。
1942年3月,戴望舒因宣传抗日罪名被日军逮捕,在狱中备受折磨。5月,叶灵凤设法将戴望舒保释出狱。11月,经一位萧红生前相识的日本记者的帮助,戴望舒、叶灵凤和那位日本记者去了当时是禁区的浅水湾凭吊萧红,三个人找了一下午,才在丽都酒店前面找到了埋葬萧红的地方,戴望舒他们在萧红墓上拍了两张照片,15年后,这照片成了确认萧红墓的物证。之后,戴望舒多次前往浅水湾,并在萧红墓前口占了一首纪念诗。
1944年9月10日,戴望舒在他主编的《华侨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上,发表了这首口占诗,诗题为《墓边口占》,诗如下: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偷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的闲话。
戴望舒保存了这首诗的剪报,并在上面备注到:“原题为《萧红墓边口占》,萧红二字被检。”萧红是著名的抗日作家,日本占领香港时期,萧红二字是不能见报的,所以被捡。这首诗写到“偷”放了红山茶,也说明了当时环境的恶劣。
这首诗的定稿在1944年11月20日,起因大约是戴望舒在11月中旬收到了端木蕻良从贵阳寄来的一封信,信写于11月1日,信中端木蕻良说马季明到桂林告诉了他戴望舒被捕的情况,对戴望舒因为向日宪兵承认认识自己而入狱并遭受苦刑表示不安,又请戴望舒照料萧红墓,并说想把萧红迁葬到杭州西湖,征求戴望舒意见。端木蕻良找戴望舒商谈迁萧红墓到西湖一事,大约是考虑到戴望舒为杭州人,想请戴望舒帮忙,戴望舒怎么答复已不可知,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戴望舒是无能无力的。戴望舒接到此信后,百感交集,斟酌修改了口占诗,成为定稿: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定稿和初刊稿相比有两处不同,一是第二句减去一个“偷”字;一是第四句减去一个“的”字。定稿显得更为精炼,节奏感增强。

戴望舒拜谒萧红墓(右一)
4
目前所知,这首口占诗1949年以前共发表过6次,诗句正文有两种——初刊稿和定稿,后5次发表的诗句正文均为定稿。但6次发表的诗题都不一样,如果诗后有写作日期或备注,也不一样,简述如下:
1、1944年9月10日,香港《华侨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第33期,诗题《墓边口占》(《诗二章》两首之一);
2、1946年1月5日,香港《新生日报》副刊《新语》,诗题《墓畔》(《旧诗帖抄》五首之一);
3、1946年1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诗题《萧红墓照片题诗录》,诗后写作日期和备注为:一九四四.十二.廿日 墓在香港浅水湾海滨 (中华文艺协会保存物);
4、1946年2月25日,天津《鲁迅文艺月刊》第1卷第1期,诗题《吊萧红》(《虏居诗钞》六首之一),诗后写作日期和备注为:一九四二.十二.二〇 墓在香港浅水湾海滨;
5、1946年3月15日,上海《文艺春秋》3卷4期,诗题《萧红墓前口占》,诗后日期为:(一九四四.十一.二十。);
6、1948年2月,戴望舒诗集《灾难的岁月》,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诗题《萧红墓畔口占》,诗后日期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萧红逝世后,朋友们纷纷做诗写文哀悼,但最好的文是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最好的诗则是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它们情感异常真挚,艺术手法高超,读后余韵悠然,使读者感染至深。
戴望舒作为萧红的朋友,对萧红在侵略者的炮火中早逝悲伤不已。他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去浅水湾,在萧红头边放一束红山茶,问候毕,便坐在墓畔和朋友喃喃私语。他说他在等待着漫漫长夜何时消去,他可受尽了苦难的折磨!他埋怨他自己说来说去,萧红你怎么不回答啊?却静卧在那里,默听着海涛的闲话!

《萧红墓畔口占》证明了一种永恒的情感——萧红和戴望舒的深厚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