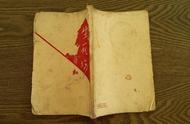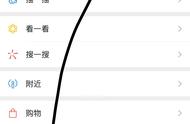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短暂的三十一年生命,七十万字的作品留传,历尽一个女子所能经过的沧桑,却堪称现代小说史上最纯真不伪的作家——永远以最真诚的态度,写她最真实的感受。萧红笔下对“乡土和女性的人文关怀”深刻优美的呈现,使她的小说长期以来感动读者,使其成为新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小说”风格的“小说家”。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分析萧红文学作品中的乡土情怀和女性关怀。
乡土情怀萧红虽然出身乡绅地主之家,但对她周遭那些寒微贫贱的乡土人物却有着深刻的了解与同情。这一点,一方面与她童年和农人相处的经验有关;一方面则由于她善良的本性受到祖父启发;对世界、人生恒常以温暖和爱的态度对待。

萧红影视图
她深知农人生之艰难,《生死场》一书开章第一景刻划二里半寻找他走失的羊,即在说明牲口对农人的重要。一头羊、一头牛、一匹马、一匹骡,往往正是农家生存之所依赖,它们的生命比人命还珍贵。其实不止牲口,一畦菜圃,一片麦田,其重要性也远远超过人。所以金枝因为*而失魂,摘了满篮的青柿子回来时,便遭母亲一顿踢打。萧红写到:
“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生死场》)
而王婆因为农忙,疏忽让三岁的孩子摔死时,她根本无暇悲哀:
……啊呀!……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她的小手颤颤着,血在冒着汽从鼻子流出,从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断了。我听一听她的肚子还有响;那和一条小狗给车轮压死一样。我亲眼看过小狗给车轮轧死,我什么都看过。这庄上的谁家养小孩,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掘菜的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子硬搅出来。......
可是,邻人的孩子都长起来了!……到那时候,我好像才忽然想起我的小钟。(《生死场》)
为着麦子,一个母亲竟不得不使她自己像一具空躯壳似地,压抑着丧女的悲痛,这是怎样不堪的人生!萧红并不刻意夸饰,只是用平静的语调描写出人物内心的曲折,而生活——对乡土人物而言,无异是一巨大的梦魇,此一主题便有力地、生动昭晰地传示出来。在这里我们也已经不难发现萧红那种最特异、最具魅力的,平静而含蓄动人的笔致。

《生死场》
面对如此艰难的生之现实,乡土人物所表现的逆来顺受的生之韧力,深深地震撼了萧红。《呼兰河传》里写粉房里的粗人:
这粉房里的人吃蘑菇,总是蘑菇和粉配在一道,……他们做好了,常常还端着一大碗来送给祖父。等那歪鼻瞪眼的孩子一走了,祖父就说:“这吃不得的,若吃到有毒的就吃死了。”但那粉房里的人,从来没吃死过,天天里边唱着歌,漏着粉。……他们一边挂粉,也是一边唱着歌。等粉条晒干了,他们一边收着粉,也是一边唱着。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快乐,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否苦多乐少。
好一句“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否苦多乐少。”这些人“逆来的,顺受。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他们愈是坚韧地活着,就愈教人钦佩、同情,却也愈教人感伤,这种复杂的感情萧红幽美的写道:“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然而萧红终究对这种坚韧的生命是给予高度礼赞的,所以她把人性中最高贵的美给了冯歪嘴子《呼兰河传》,给了王亚明《手》。
冯歪嘴子的外表是丑的,可是他勤劳地工作,诚挚地待人,疼爱太太,疼爱儿子,他对旁人七嘴八舌的调侃毫不在意,他宽容东家的苛刻无情,妻子死后,他一手牵大的,一手哄小的,在别人以为他一定完蛋的情况下,身兼母职的,强毅的活了下去。他的内心是至美至善的。萧红说:“他在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 。“于是他照常的活在世界上,他照常的负着他那份责任”。事实上,不仅冯歪嘴子如常的活下去,连那人们以为必死而似乎永远长不大的小儿子也渐渐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会伸手拿东西吃了,而当他微微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我们清晰地看到强韧的生命力,在瘦小的孩子身上继续地承继着、发扬着。
至于王亚明,她是染坊家的姑娘,到城里的中学念书。因为帮忙家业的关系,她的手是“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 这竟成了学校师生一致厌恶她、排斥她的因素。她在学校里备受捉弄、羞辱,可是她从不记恨,也不闹事,只是勤奋地用功——午餐桌上,她想着地理课本上的知识;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读书;天将明时,她就坐在楼梯口;甚至到最后,她被剥夺考试权利而等着父亲接她回家时,她赶上上课的行列,呼喘着说:“我的父亲还没有来,多学一点钟是一点钟… …”
在这篇作品里,萧红不但让我们看到王亚明勤学的美德,也看到她俭朴的美德,更看到她温厚的心胸,在她被迫离校时,没有人去跟她告别或说一声再见,而她仍向每个人笑着。我们终于可以深刻地感知到作者所安排的种种王亚明污暗丑陋的外在——不论是黑紫的手、灰色的上衣、腌脏的被褥,都是她洁白、美的、高尚的心灵的反衬,而同时是她周遭那些徒具清新外表的人物内在的真实写照。

萧红影视图
萧红对乡土人物的礼赞态度是可以无疑了,但她也不是没有看到他们的卑微、愚昧、无知、残酷的一面。以卑微而言,生死场中的赵三便是个典型的例子:赵三与李青山等人本来组织了镰刀会,要教训刘二爷,反抗他无理的加租。可是在一次误打小偷,坐了牢,赔了半条牛之后,他整个人又退缩了、怯懦了。他甚至有点感谢他原先要教训的人,他觉得这一切是自己犯错的惩罚。
他说话时不像从前那样英气了!脸上有点带着忏悔的意味。羞惭和不安了。王婆坐在一边,听了这话他后脑上的小发卷也像生着气:『我没见过这样的汉子,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后来越看越是一堆泥了!』赵三笑了:『人不能没有良心!』于是好良心的赵三天天进城,弄一点白菜担着给东家送去,弄一点地豆也给东家送去。为着送这一类菜,王婆同他激烈吵打,但他绝对保持着他的良心。
萧红的笔致真是不疾不徐,而嘲讽的意味却充分极了。其实何止赵三如此,整个镰刀会也就不声不响地衰弱了、消灭了。赵三的表现完全和前述寻羊的二里半一样:二里半因为寻羊,误踏了人家的菜园,遭到了毒打,后来羊自己回来了,他竟觉得羊不是好兆相,要找买主卖掉。二里半把自己粗心而遭来的毒打怪罪到羊的头上;赵三把误打小偷而坐牢看成自己反抗东家的惩罚,二者反映的都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卑微。萧红笔下的乡土人物是不会反抗的。
这种不会反抗的卑微,就和他们的牲畜马一样。《生死场》的第三章“老马走进屠场”,写得血泪淋漓。一般评论者都认为这一章在描写人与牲口亲密的感情,其实萧红笔下还有另一层意义——马的一生就是农人的一生——它们卑微的生,卑微的活,卑微的死。老马不偷食麦粒,不走脱轨,转过一圈又一圈,绳子、皮条有次序地向它光皮的身子磨擦,它无声的动在那里。写的不就是农人劳动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