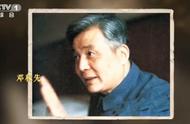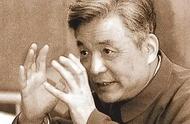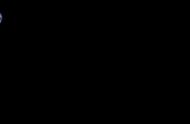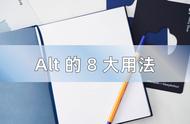时间退回到1958年,那是邓稼先加入“两弹”研发的开始。当时,领导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义无反顾地表示同意。
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许鹿希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了。
许鹿希问:什么工作?答:不能说。
去多久?不能说。
可以写信吗?恐怕困难。
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大院和茫茫的大漠戈壁,就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邓稼先一家
当时的研究条件有多艰苦呢?邓稼先计算数据时,只有手摇计算机,甚至还要用到算盘。他在青海基地试验原子弹时,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只能吃酱油汤泡饭,饿得全身水肿。许鹿希给他从家里带的油炒面,还经常被前来蹭饭的同事瓜分,没多长时间就吃完了。
对于邓稼先当时的研发过程,杨振宁在《邓稼先》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非常好哭:
也不知道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这篇文章中的另一段,则让我们对邓稼先的人格魅力有一个大概的感知: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别人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而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在一次空投核弹试验中,降落伞没及时打开,炸弹一直没炸。邓稼先不顾其他同事的劝阻,走进辐射核心区,用双手捧起了核心部件。他此前就已经受到了常年的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在随后的体检中,他体内被查出有大量放射性物质,癌细胞最终扩散,无法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