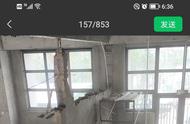这样的眼神是陈洪最不愿意看到的,立刻颤声说道:“这两个太医主子要是不满意,奴才立刻去另找。”
嘉靖不看他了,望着床顶在那里出着神。陈洪屏住呼吸直望着他。
“怎么论的罪,”嘉靖仍望着床顶问道。
“回主子。”陈洪立刻答道,“百官写了奏本,都不愿再说话。更可气的是那个王用汲,连驳海瑞的奏本都没有写,反而呈上了个说宫里矿业司贪墨的奏疏,摆明了是跟主子对着干。奴才已经将那个王用汲也抓了。”
“内阁徐阶他们是什么个意思?”嘉靖的目光倏地望向了陈洪。
陈洪:“内阁的意思,将百官驳斥海瑞奏本里的话都摘集出来交三法司明日定罪。奴才有些担心,那些人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声,给海瑞定一个不明不白的罪,玷污了主子的圣名。”
陈洪这番话嘉靖其实听不进去,圣名在海瑞上奏疏,后来他亲自公开的时候已经被玷污了。他现在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脸面能挣回来多少,官员里面还有几个能站在自己这边的。
嘉靖两眼又翻了上去,露出了那副怪怪的眼神:“取纸笔来。”
“是。”陈洪立刻站起趋到御案边将纸笔砚盒放进一个托盘中,捧着又踅回到床边,先放到床几上,扶着嘉靖坐好了,然后又捧起托盘呈了过去。

嘉靖靠在床头,拿起了朱笔,想了想,在御笺上先写下了两个字:“好雨”。接着,他的手有些颤抖拉开了这页御笺,又在另一页御笺上写下了两个字:“明月”。搁下了笔:“这里说的是两个人。送给裕王,叫他召徐阶他们一起看。”
“奴才立刻就去。”陈洪捧着托盘立刻应道,接着又轻声问嘉靖,“奴才再请问主子,徐阶他们都指哪些人?”
嘉靖不看他了,望向了床顶:“要是吕芳在,这句话就不会问。”
陈洪不晓事的又一个典型,这话从嘉靖嘴里说出来,就是无比的失望了。裕王平日里和几个师傅们走得很近,这是人尽皆知的,以吕芳秉性是断然不会让嘉靖说明白的。找对人了,是奉旨行事,找错人了,是自作主张,下面的人把锅背了,嘉靖岂不省心?陈洪是揣测不明白,所以才要嘉靖把话说清楚,嘉靖内心的失望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嘉靖突然提起了吕芳,而且那颗头一直仰着望向床顶一动不动,好像吕芳就趴在龙床的床顶上。
陈洪身上立刻像被电麻了一下,回话时居然结巴起来:“奴、奴才愚钝,奴、奴才明白”
到底是愚钝还是明白,这时连陈洪自己也不知道了,将托盘放回御案,捧着那两张御笺梦游般走出了精舍。

裕王府书房
两张御笺摆到了裕王的书案上,由于是密议旨意,陈洪遣走了裕王府当值的太监,自己临时充当起伺候裕王的差使。只见他绞了面巾捧给裕王擦了脸,又拿起了一把扇子站在书案后替坐在那里的裕王轻轻扇着。裕王竟也默坐在那里出神地琢磨着嘉靖写的那四个字,一任陈洪在身边悄然伺候。
自那回裕王性起对陈洪发了一阵雷霆之怒,陈洪跪着向裕王做了一番披肝沥胆的表白,这时裕王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礼敬,其实是已经接受了他的投诚。如同山溪之水,虽然易涨易退,一旦流入河中,便再也回不了山中。裕王作如是想,陈洪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徐阶他们来了,竞只有三个人,一是徐阶,二是高拱,第三个却是张居正。
“臣等见过王爷。”三人同时向裕王行礼。
裕王也站了起来,侧了侧身子:“师傅们请坐吧。”
“陈公公。”徐阶三人没想到陈洪也在这里,这时掩饰着内心的厌恶,只好都向他拱了拱手。
陈洪在这里却一脸的谦笑:“王爷说了,师傅们都请坐吧。”
徐阶三人在靠南窗的椅子上坐下了,陈洪却依然站在裕王的身边轻轻地给他扇扇。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望向了裕王。
裕王:“有旨意。”
三个人立刻又站起了,准备跪下去接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