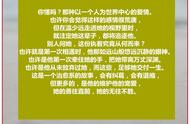“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九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日语译者竺家荣的故事。
那天的场景竺家荣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珠海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突然登门,手里拿着一本日文小说。竺家荣当时只翻译过一个短篇,但编辑只通过这个短篇,就认定竺家荣是翻译这本书的不二人选,请她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翻译出来。接过这本名为《失乐园》的小说后,竺家荣随便翻了几页,大段大段露骨的性爱描写跳入眼中。
“不行不行。”她把书递回去,拒绝得很干脆。编辑没却有放弃,二次登门,再三说:“我跟你说两点你一定会改主意。第一,允许删节以及朦胧化处理;第二,翻译了这本书,你就出名了。”从九岁开始学日语的竺家荣,直到四十岁才终于等来了独自翻译一本书的机会,然而面对的却是这样一本“有伤风化”的小说。翻还是不翻?竺家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进了外语学校,将来就是大使夫人”
竺家荣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解放前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工学系,曾在鞍钢任电力自动化工程师,后来因工作调动举家迁到北京。竺家荣在鞍山出生,在北京长大。父亲虽然主攻理科,但文史兼通,会英语、俄语、日语等几门外语,家里藏书丰富。家里姐弟三人,唯有竺家荣沉迷于这些藏书,“姐姐弟弟都比较外向,在家里待不住,只有我个性好静,不大喜欢出去玩,常常在家里看书,所以从小就对书有一种偏爱。”希腊神话里的九头蛇以及自恋的美少年被自己的化身拖下水的画面、百科图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里的爱情故事、以及各种小人书等等,构成了竺家荣最初的文学记忆。
1964年,为应对外交人才短缺的问题,*指示“外语要从小学起”,国家开始实行一项从适龄儿童中选拔外语人才的培养计划。全国开办了8所外国语学校,招收从9岁开始学习外语的小学生,其中有两所在北京。“外语学校主要由外国教师教课,直升外国语大学,将来培养出来都是大使或大使夫人!”小学二年级的竺家荣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介绍情况,非常向往。不过竺家荣虽然成绩还可以,但外貌并不突出,老师只推荐了班上最漂亮的“四朵班花”,没有推荐她。
竺家荣懊丧地回到家,跟母亲讲了这件事,得到了母亲的支持:“你想去的话,就去跟老师说说呗”。第二天,竺家荣在班上同学的鼓励下壮着胆子跟老师说“我也想去参加考试”,老师看了看她,说了句,“那就给你加一张表吧”,就这样竺家荣报上了名。
接下来是笔试、面试、身体检查,过了一关才能进入下一关,在忐忑的等待中,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不久后的一天,竺家荣在家里听到有人“蹬蹬蹬”地跑上楼来,她开门一看,是老师,吓了一跳。这位四十多岁的女老师跑上四楼,气喘吁吁地一把抱住了竺家荣,叫道:“没想到,你真棒!”后来竺家荣得知,外语学校考试竞争相当激烈,而她是班上唯一一个通过了考试的学生。

竺家荣很想学习德语、法语这些听起来很洋气的语言,结果被分到了日语专业,原因竟然是她的视力问题。竺家荣的眼睛先天屈光不正,她从小看书便要戴上奶奶的老花镜,但依然十分费力,看一会儿就得闭眼睛休息一下。外语学校要求的视力是1.5,竺家荣只有1.0。她记得检查视力的是个高大的很帅的叔叔,对她说:“小妹妹别紧张,给你写1.2吧。”虽然过了体检这关,但因为视力不达标,竺家荣被分到了没有人愿意学的日语专业。那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学日语很受歧视,在寄宿制的外语学校里,学日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但父亲的话给了她很大信心:“好好学,中国和日本用不了多久一定会建交的。”七年后的1972年,这句话果真变成了现实。
但还没等到中日建交,中国国内局势开始动荡。竺家荣刚进入外语学校两年,文革爆发了。学生们纷纷变成了红卫兵、红小兵,到处充斥着政治口号、大字报、*像章、“忠字舞”……竺家荣对政治始终不太关心,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依然一天到晚只想看日语书,因此被大家批评为“白专”。“我记得到后来,全班都是红卫兵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是了!”17岁那年,竺家荣从外语学校毕业,只有“根红苗正”的毕业生才能分配到外交部、公安部等国家机关,而成绩全优的竺家荣被分到一所中学,成为了一名日语老师。
从17岁到22岁,竺家荣在丰盛中学度过了五年茫然的青春岁月。文革还在继续,学生们根本不愿意学习,竺家荣比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们大不了几岁,作为小班主任,面对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学生常常是束手无策,她的自行车经常被坏孩子破坏,只能推着走回家。她还得经常带学生去工厂农村开门办学,也曾下放到五七干校受了半年再教育,养过猪、干过各种农活。“对这段日子我不太愿意回首,感觉自己的青春都被耽误了。当时我们去外语学校时,老师说你们的学校是宝塔尖,你们将来就是国家的栋梁,没想到如今从那个宝塔尖上掉到底层,觉得特别失落,不知道将来的出路在哪里,只能整天混日子。”还不到二十岁,竺家荣就长出了白发。
1977年,*出来主持工作,恢复了高考。竺家荣感到机会终于来了,非常兴奋。“恢复高考就等于拯救了我”。她报考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由于“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竺家荣“落了选”,最后被黑龙江大学录取。“虽然必须离开北京,但只要不再当中学老师,我死活也要上大学。”由于有从小学日语的底子,竺家荣直接跳到了二年级。很快国家又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1979年竺家荣考入了国际关系学院读研,1981年毕业。在这四年的时间内她迅速地拿下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位,然后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
看到《失乐园》里大段大段的性爱描写,她把书推了回去
对竺家荣说,当初学日语是一次偶然,但走上翻译道路却不是偶然的。留校任教之后,竺家荣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入到了教学和家庭中,一直到四十多岁,才翻译了人生的第一部书。这其中15年的时间“好像都荒废掉了”,但竺家荣说,自己心中一直保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做翻译。
从上学的时候起,竺家荣就不是那种特别受老师重视的孩子。“毕竟不是能歌善舞,嘴也不是那么甜”,加上视力天生不好,竺家荣说,自己从根儿上来说是一个自卑的人,到现在都是这样。“我属于自尊心极强的一个人,自尊心极强的人,往往自卑感也很强。我总觉得,自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但是学习还可以。兼通中日两种语言以及爱好文学的底子,因此长项很可能是做文学翻译了,只有在翻译中,能够感受到快乐,只有翻译才能使自己获得尊严。后来的发展也多少验证了自己的这个预感。”
在中学教书的那五年,竺家荣就曾几次向学校提出想要调走,去做与翻译有关的工作。成天与一帮学生混在一起让她焦头烂额,她觉得“搞翻译不用跟人打交道,管我自己就好了,至少是清净”,但学校始终没有同意。大学期间,竺家荣也会自己找些日语文章,纯粹出于兴趣“翻译着玩”。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带着学生们集体翻译过一本《日本民间故事》,竺家荣在其中翻译了一篇童话故事,对翻译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之后竺家荣也翻译一些作品,给杂志投稿,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复。
在大学任教了十五年之后,竺家荣受邀去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三岛由纪夫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结识了国内知名日本文学翻译家叶渭渠。叶渭渠当时正在组织人翻译一些日本文学作品,看到竺家荣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后,对她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想不想试着翻译一些作品呢?”竺家荣听了喜出望外,“太好了,我这么多年苦苦寻求,一直找不到门槛……”由此,她获得了人生当中第一个翻译机会——安部公房的短篇小说《狗》。她翻译得极其认真,这篇翻译处女作收录在安部公房作品集里,由珠海出版社出版了。
出乎意料的是,不久珠海出版社的编辑亲自找到了竺家荣的家里,带着一个月前刚刚在日本出版并引起轰动的《失乐园》。“你看看这本书,我们希望尽快翻出来,越快越好。”出版社希望赶在台湾的前头,让它的简体中文版尽快面世。看到里面大段大段的性爱描写,竺家荣把书推了回去。但执着的编辑隔几天再次上门,同意进行删节和“朦胧化”处理,并说,你既然想做翻译,就应该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希望再慎重考虑一下。

经过再三考虑,竺家荣最终没有错过这个机会,“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态,硬着头皮上阵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整个人都陷入了《失乐园》之中。《失乐园》出版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轰动,几乎到了尽人皆知的程度。但是那时国内的版权制度极不完善,合同也不正规,出版社甚至拖着不付给竺家荣稿费。不过这本书也确实给竺家荣带来了名气,一时间书店里出现了许多渡边淳一的盗版书,都冠上了“竺家荣”的名字,《失乐园》的盗版更是层出不穷。
《失乐园》在中国出版后,同日本一样,评论也是毁誉参半,不过比起这本书在日本的评价,在中国批评的声音反倒要少一些。竺家荣觉得“我们中国人往往习惯于站在自己的文化角度上去解读,把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殉情理解成自*谢罪,或者认为渡边淳一这样写是在批判日本社会的堕落,这种解读可以说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 。但是这些“误读”反而助推了《失乐园》的传播,也正是在这些误读下,《失乐园》得以安全过关,并畅销多年。
在竺家荣看来,《失乐园》探讨的主题是与自《源氏物语》以来的“物哀”一脉相承的。“物哀”是对事物的一种感伤,或者说深刻的体验,在男女之情上表现得最为典型。”作者通过小说男女主人公所陷入的婚外情,深刻地探讨了婚姻和爱情的含义。在日本的“好色”美学传统中,爱情是灵与肉的和谐统一,而婚姻往往导致激情逐渐淡薄,爱情也随之消亡。小说中男女双方的殉情,是为了避免重蹈婚姻的覆辙,要在快乐的巅峰、最美的时刻结束生命。当然,作者绝非在推崇殉情,是希望人们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不要失去人生的乐园,竺家荣补充说。她前后翻译了十来本渡边淳一的作品,几乎每本都专门写了译后记,详细探讨渡边文学的美学意义。

竺家荣说,《失乐园》日本版的封面是耐人寻味的。正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封底则是盛开的樱花,这里边含有很深的寓意。火焰象征燃烧般热烈的情欲,将一切化为乌有,而樱花则以其盛开时的美艳,凋落时的决然,,让人联想世事无常,爱的短暂。渡边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生死观和美学观:死亡是绝对的、无限大的“无”。这种“无”不是西方式的虚无主义,而是东方式的虚无,所谓“无中万般有”,蕴藏着丰富的东方文化的内涵。
当年她曾因《失乐园》有着大量性描写而拒绝过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如今竺家荣认为,这些不拘一格、不受束缚的日本文学,“能够让中国读者接触到多种文学表现,看到各国文学对人性的多方面探究,拓展视野,善莫大焉。翻译是一个构筑人类精神的巴别塔的神圣事业。”这也是她投身文学翻译的目的之一,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感。
翻译《一个人的好天气》,让她在灰心时重新振作
翻译《失乐园》之后,竺家荣虽然有了一些名气,但并没有因此大红大紫。她一边继续在学校教书,一边断断续续翻译了十几本书。2002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由于评职称不顺利等原因,竺家荣又一次陷入了低谷,如同在丰盛中学的那5年一样,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表任何译作。“我天性敏感,柔弱,一旦遭遇挫折,很难振作。可以说当时完全看不到出路,对自己对人性对社会都感到绝望,即便是最喜欢的翻译也觉得毫无意义。用现在的说法有点忧郁症的样子”。“总觉得这个社会不公,无论你多么努力,最终人家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地否定掉你” ,因此得出结论,“一切都是虚无,还是什么也不做为好。”竺家荣没有再争什么,她开始自我封闭起来,2005年,以副教授的职称退了休。
就在退休的第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找到竺家荣,带来了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请她翻译。竺家荣翻开书,第一页第一行是这样一句话:“一个雨天,我来到了这个家。”她当即便感到,这是一本好书,而且自己也一定能把它翻译好。出版社的编辑也像多年前《失乐园》的一幕重演一样对她说,只要您翻译,这本书一定会畅销。
竺家荣又一次犹豫了,自己以前翻译的都是些经典作家,从来没有翻译过这种青春文学,而这位作者的年纪几乎跟自己的女儿一般大。但她还是决定挑战一下,“我觉得作为译者应该什么都可以尝试,应该挑战一下自己,就像演员不能只演一个角色,那就模式化了”。《失乐园》的成名让竺家荣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定了位,仿佛她就是一位日本情色文学的翻译专家,甚至有编辑拿来一本名叫《性*扰应对》的书请她来翻译。竺家荣想,自己应该“跳出圈子,翻译一本清纯的作品试一试”。
尽管年龄相差一代人,竺家荣却觉得自己跟青山七惠是有缘的。青山七惠作品当中处事不惊的淡然笔调,很接近日本传统文学中的《枕草子》,让竺家荣颇有些感慨。“我在中国见过青山七惠,跟她一块儿吃过饭。这个年轻人很是老道,真是很成熟,对什么事都很淡定,好像什么都无所谓。她对命运是一种承受的态度,觉得不一定非得改变。”相比起来,竺家荣觉得自己都不够成熟,有些“童心未泯”。“我觉得跟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种处事态度挺好的,很淡然,不能太纠结于一些事情。怨天尤人只能制造负面情绪,无助于自我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