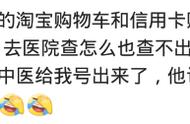《到婚礼去》,[美]约翰·伯格著,郑远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272页,52.00元
但凡詹姆斯·乔伊斯的书迷,不会不知道6月16日这个日子。1904年6月16日,乔伊斯初次约会诺拉·巴纳克尔(Nora Barnacle)小姐,后来的乔伊斯夫人。出于纪念,作家把旷世之作《尤利西斯》的背景设定在此年此月此日,以小说男主角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游荡十八小时的经历和意识流动开创出文学里活色生香的一天。每年世界各地均有读者庆祝“布卢姆日”。
曾经有一个十四岁的伦敦小伙子,在连接1940年与1941年的那个冬天航行于《尤利西斯》的词语海洋,迷途忘返,当时他不知道,此书作者乔伊斯正在瑞士苏黎世奄奄一息。当二十世纪列车骎骎行驶到世纪末,那个十四岁小伙子约翰·伯杰(John Berger, 1926-2017,又译约翰·伯格)早已是著名作家,六十九岁写成一本以时间为母题的小说To the Wedding(1995)。他同样透露给读者一个日子:妮农(Ninon)的婚礼会在“六月七号,礼拜五”举行。我因为翻译《到婚礼去》记住了这个日子。
故事梗概倒也简单,因“冷战”而分隔于异国多年的父亲尚·菲列罗(Jean Ferrero)和母亲泽德娜(Zdena),一西一东,同时穿越半个欧洲,去出席女儿妮农的婚礼。在讲述旅途的同时,小说穿插以尚、泽德娜、妮农等人物的往事,各人自己的嗓音逐一浮现,忆及往事多采用过去时态,但也不尽如此。美丽又活泼的妮农,爱上了年轻的意大利人吉诺(Gino),但她很快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绝症病毒,一度万念俱灰。最终妮农和吉诺决定结婚来庆祝尚在最美时候的青春。两人商量着婚礼地点和日期:“吉诺知道全年的每一天是礼拜几。这是他赶集练就的本领。”他们准备在“六月七号,礼拜五”,在波河(Po)入海口的一个意大利村子结婚。
婚礼一幕是全书的华彩段落,它以将来时态糅合现在时态来叙述。叙述者这样告白:“……婚礼尚未发生。但是正如索福克勒斯知道的,一个故事的未来永远在当下。婚礼尚未开始。我会给你讲它的事。”将来之中又有将来:在婚宴狂欢的叙事主体中,插叙着如同电影闪进一般的场景,妮农预先想见了自己未来病重的情形,小说在狂喜里交织大悲。
译竣后意犹未尽,于是把文学教授拉尔夫·赫特尔(Ralf Hertel)讲它的论文也一并译介出来,赫特尔将婚礼日期写为“六月八日”,不是我已熟悉的“六月七号,礼拜五”。询之于教授本人,方知不是笔误,他依据的英国版确实另有一个婚礼日期。我感到震动。

《到婚礼去》
英语名家的原著通常分为美、英两个版本,由不同出版社发行,在各自地区的市场销售。我住在美国,本来顺理成章地采用了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95年美国版作为工作样书;英版同年由伦敦Bloomsbury出版社推出,我手边也有。英语国家发行的《到婚礼去》至今还是这两个版本的重印。英、美版页码相同,版式也大致相同,除了美版别出心裁,在每章开头多放了一个塔玛(tama)许愿牌图案之外,似乎没有区别。那“六月八日”却推翻了想当然耳。身为译者,我不得不追究两版的差别,最终发现英、美版的文本有好几处时间歧异:
(一)第十六页(英文原著页数,下同),泽德娜忆及自己离开爱人尚·菲列罗和女儿毅然回国的往事,思绪中有一句:“十七年前那天晚上,她对尚问及签证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英版)此处美版为“十年前”。
(二)第七十五页,妮农刚确诊感染艾滋病时,英版内心独白为:“爸爸,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二十三岁,就要死了。”美版“二十三岁”作“二十四岁”。到第八十三页,妮农去监狱探望将病毒传染给她的露水情人,愤然对他说:“二十四岁我就要死了。”此处英、美版则一致。
(三)第一百十一页出现全书最耐人寻味的版本差异。英版将婚礼日期定为“六月八号,礼拜三”,美版则作“六月七号,礼拜五”。两个日子一望而知不同年——一场婚礼,两个年份?
讨论时间歧异(一)(二)(三)之前,让我们先找到参照时刻,来搭建一个结实的框架,这种时刻包括布拉格之春。
约翰·伯杰落笔细致,兼用明写、暗写来交代妮农成长不同阶段的岁数与年份。非但如此,他还提供足够的线索让我们追溯妮农父母尚·菲列罗、泽德娜生命中的一些关键时间点。小说提及不少历史大事,比如原著第十四页(中译本页码同)写泽德娜“二十五年前”在布拉格读书,时值1968年布拉格之春;而小说中提示的最晚发生的历史事件,当为斯洛伐克变成独立共和国(1993年1月1日):中译本一百八十四页,去婚礼途中的泽德娜,手袋里有“新办的斯洛伐克护照”。据伯杰自己在纪录片《恩典的轻触》(A Touch of Grace, 1996)中回忆,他花了两年写《到婚礼去》(1995年出版)。综合上述可以推测:作家在1993年动笔写这小说,并将现实生活的当下,用作故事里的当下时间。换言之,小说动笔之初把故事当下设定为1993年。
同样第十四页,泽德娜1969年圣诞节逃亡国外,辗转到达巴黎,其后和未来的妮农爸爸尚·菲列罗邂逅于声援捷克难民的晚会,晚会时间可推断为1970年。值得一提,原著第十二页(译本同页)还交代“二十六年前”尚·菲列罗和妻子妮戈尔(Nicole)一起住在法国市镇莫达讷,妮戈尔无法忍受丈夫对社会运动的热忱,弃他而去。参照布拉格之春为“二十五年前”,可知妮戈尔1967年出走;三年后,尚与泽德娜相遇。
第十四到十五页还讲了1970年10月的事:智利政治家、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赢得大选,就任总统,使恋爱中的尚、泽德娜动了迁居圣地亚哥的念头。11月,泽德娜告诉尚她*了,两人决定留住孩子。孩子就是妮农,她肯定生于1971年。
女儿妮农六岁时,泽德娜从电台广播得知一百个捷克公民联名请愿,政治气候出现转机,决定回去看看,当时她出国已有八年(15页,各版本同)。小说虽未道破,但这无疑是指《七七宪章》发表那一年,1977年。
上一段的基础让我们能够探明时间歧异(一)。
美版“十年前”与女儿分离,明显有误,因为1977年再加上十年才1987年,到不了当下(前述小说动笔之初,它设定为1993年)。英版“十七年前”,计得故事当下为1994年,以小说1995年出版而言,是合理的。美版“十年前”犯了编校错误。
现在来谈时间歧异(二)。英版先二十三岁,再二十四岁;美版始终二十四岁。英版未必自相矛盾。从发现感染到探监,妮农中间经历了一些事:她取消和男友吉诺的约会,用明信片告知他去做血检,并向监狱寄材料申请探监,经等待,方才获得狱方的批准。在此期间,且不说妮农是否度过了生日,她至少是更接近二十四周岁了,在狱中冲口而出“二十四岁我就要死了”,合情合理。此时她对青春流逝的感受肯定特别强烈。可是,如果英版“二十三岁”系作者有意为之,美版为什么偏偏要用两个“二十四岁”呢?我们称它为疑问(I),押后讨论。
轮到时间歧异(三),不可能位于同一年的“六月七号,礼拜五”(美版)和“六月八号,礼拜三”(英版)。它显然要求我们探究:“婚礼在哪年举行?”
先来探讨故事的当下设在哪一年。中译本附录的赫特尔论文总结了故事的当下时间框架,它开始于复活节礼拜天(通常为3月底4月内),终结于当年6月上旬的婚礼(婚礼以现在时态糅合将来时态叙述,效果恍如当下)。故事的当下未曾跨年。所以,问婚礼哪年举行,等于问:哪年是故事的当下?
前面讲过小说动笔之初把故事当下设定为1993年。它和两个事实不接榫:
(a)故事中妮农1971年生,现年二十三/二十四岁;
(b)由万年历查得,1993年6月7号、8号为礼拜一和礼拜二,与美、英版的婚礼日期均不符。
看来伯杰疏忽了:小说两年写成,这已不是动笔时的1993年。笔下“二十五年前”“二十六年前”云云,本应与时俱进才对。既然妮农生于1971年、年满或将满二十四岁,按理,故事当下该是1995年。然而查对万年历,1995年6月7号、8号却是礼拜三、礼拜四,与美、英版的婚礼日期也均不相符。
伯杰计年是不够周密,但意图足够清楚:他提示了女主角的生年,说明了她的年龄,又以“几月几号,礼拜几”的相交之点,使婚礼年份能够被读者锚定。既然婚礼不在1995年,我们且看周边年份。依据万年历,1994年的六月八号确是礼拜三,和英版婚期相符。1996年的六月七号,则果然是礼拜五,让美版的婚期也有了着落。
现在可谈谈疑问(I):英版妮农的当下年龄从二十三岁进展到二十四岁,较显年轻,令1994这偏早的年份更为可信。其实,英版故事梗概讲明妮农“二十三岁,将死于艾滋病”(为中译本的文案所沿用)。英版妮农偏年轻,与该版把当下 婚期定于1994年的事实互为佐证。美版的两个二十四岁稍后谈。
通观时间歧异(一)(二)(三),英版处处合理,美版则在(一)有明显差错(“十年前”)。英版表现更佳,况且,伯杰是英国作家。我至此决定,把英版当作翻译所依据的“善本”,郑重地修改婚期为“六月八号,礼拜三”,并嘱咐编辑在中译本前面加上:“据英国Bloomsbury出版社1995年版本译出。”
美版稍有纰漏,我们无须把婴儿连洗澡水一起泼掉;它的“六月七号,礼拜五”仍可能意味深长。首先要明确,这不可能是笔误、印错,鉴于约翰·伯杰的盛名,也决不会是编辑擅改。对此,赫特尔教授回复电邮表示,如有更改也肯定是伯杰自己所为,婚礼日期看来对作家很重要,至于为何要两版不同,则不得而知。上文谈时间歧异(三)为求简练,只说到英版婚期为礼拜三、美版为礼拜五,其实差别不止于此,书中还存在用其他“礼拜几”信息与相应版本的婚期相配合的做法。比如尚·菲列罗开摩托车前往婚礼时,从法国山区进入意大利地界,清晨在山路遇见牧羊人并交谈,牧羊人问他今天是否礼拜天,英版摩托车手答“礼拜一”,美版答“礼拜三”(原著42页),各与相应婚期之间留空两天。进入意大利后,摩托车手在波河边几个网络黑客少年的小屋过了一夜(可推断,英版为礼拜一夜晚;美版为礼拜三夜晚);循另一路线前来的泽德娜,同一天夜晚则在跨境大巴上度过。次日,在英版该是礼拜二,在美版该是礼拜四,摩托车手在码头接到了泽德娜。这天晚上即婚礼前夜,两人已抵达目的地,小说言明泽德娜是在举行婚礼的村子下榻的;婚礼那天拂晓,她被面包车的声响吵醒了(译本202页)。此外还有一处歧异,在礼拜三结婚的英版十一页,摩托车手在电话里向未来亲家公说:“礼拜二咱们就在一起了”,显然将两人在婚礼前夜(礼拜二)的碰头也算作“在一起”;美版为“礼拜五咱们就在一起了”,即礼拜五婚礼那天才正式算作大家“在一起”。各种细节珠联璧合,无疑是作者手笔。
所以“六月七号,礼拜五”有何微言大义?即便它(或者英版的“六月八号,礼拜三”)像乔伊斯的“六月十六”一样是个暗码、私人纪念日,我们也无从知晓,就让我们专注于有实证的年份问题吧。前述和它吻合的年份是1996年。然而妮农生于1971年,她二十四岁是在1995年——小说的出版年。把1995用作故事当下,难道不是最合理的吗?美版偏偏绕路而行,一脚跨进未来,把当下 婚礼设定为1996年。美版着重于故事的未来性。
回到疑问(I):前述英版妮农先二十三岁、再二十四岁,年龄偏小,向较早的一年1994年靠拢。同理,美版妮农两次二十四岁,年龄偏大,为较晚的一年1996年增强说服力。
伯杰没有同时改动“二十五年前”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14页)等指涉故事当下的时间说法,导致居于时间轴较远一端(1996年)的美版故事当下,比英版含有较多矛盾。但请注意,他在任何版本都从未写出婚礼的年份,一切都是隐含着的,那一处二十三/二十四岁的歧异也是很微妙的差别。虽然“二十五年前”云云是计少了,一般读者并不会看出漏洞。

约翰·伯杰
我无意煞有介事。除了我这样的特殊读者因工作需要以外,试问有多少人会兼读英美两版,并且注意到当中的细微差异?作家明知读者难以察觉而照样予以安排,可以称之为匠心独运,也可以叫做任性。伯杰的“任性”,是想告诉读者什么吗?他这样处理近乎瞒天过海,也许是更想告诉自己一点什么,并杜绝好事的记者追问。要知道,《到婚礼去》在他是个分外切身的故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艾滋病仍是世纪绝症,无数人因而身陷地狱般的苦难,也令亲友痛彻心肺;在欧美一些大都市的同性恋男性群体中,病魔夺走的是整整一代精英。苏珊·桑塔格有感于此,写了《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伯杰作为桑塔格的好友,同样有朋友罹患艾滋病,他说这疾病对他“并不是那么遥远的事”,他感到自己也要做些什么,开始写起《到婚礼去》来。岂料小说写到一半,想象竟与现实悲哀地交集相会:他从事电影导演的儿子雅各布(Jacob)之妻确诊感染了HIV。由于此事,他一度考虑放弃这小说,后来才决心继续写完,一边从旁照料儿媳。出书不久,儿媳就因艾滋病去世了,那是1995年。
所以,英、美版近乎隐秘的时间差异,在出版那一年,令读者当下走进一条他们难以发觉却毕竟存在的语义歧路,故事在这里神奇地分岔:它要么回顾1994年,已经发生;要么前瞻1996年,尚未来临——犹如古罗马的双脸门神雅努斯一般,既面向过去,又面向将来(说来也巧:Janus和Jacob第一个音节拼写相同)。雅努斯司掌过渡、产生、旅程、流通(exchange), 均属《到婚礼去》的主题,伯杰自己就说,To the Wedding题目的关键词是介词to。雅努斯是开始与终结之神,一月一号为其圣日(沿用至今表示“一月”的单词January意即Janus之月);他也是古人缔结婚姻时崇拜的神明,而关于妮农,吉诺不是说过他们俩“结婚那天会是她重生的开始”吗(210页,译本,下同)?小说只有一次提到罗马,因为婚礼广场上有一棵悬铃树:“许久以前,在一棵悬铃树的挖空的树桩里,有位罗马执政官举办过十八名客人的晚宴”(221页),虽然仅此一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举行婚礼的地方正是意大利,小说也强调意大利人活在当下(“天才全部发挥在享受上”“和斯拉夫人正相反”,173页)。既然这是一部蕴藏无数神话典故与文学象征的小说(参见赫特尔,亦见拙文《〈到婚礼去〉的重负和恩典》),伯杰可能暗用了雅努斯象征来喻示这婚礼既在过去又在未来的二重性。这么说当然是我的猜想,绝非考证,但也不妨以王尔德的理论视之:评论是在作品之内创造(a creation within a creation)。如赫特尔所言,小说征用了古罗马以降西方文学里恒久不衰的一个主题——carpe diem:把握今朝、及时行乐。雅努斯身处当下,掌控着时间,过去未来之门同时对他敞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在过去,妮农有过一个给她带来死亡前景的露水情人,可哀可叹;但是在未来,她依然会拥有一个予她生命希冀的丈夫,又何其幸福!然而,我们也不该忘了《到婚礼去》的元小说(metafiction)性质,它被设定为一个希腊盲人怀着深情拟想出来的故事,是各种嗓音合成的祈祷、寄盼,而激发盲人想象的、作为故事模特儿的妮农,其真实人生际遇兴许和小说截然相反:她似乎患了重病,预定的婚礼已告吹(第4、5页)。“在音乐里,希望和失落双生”(227页),一如生死、福祸之相倚,一如想象与现实之交织互成,一如灵性与物质之不可分割:这种种辩证关系,本来就内蕴于《到婚礼去》,是故事的精神张力所在。莫非,伯杰舍弃最顺理成章的当下一年(1995),利用1994/1996作双重安排,是暗示着当下时间之门兼向过去和未来洞开?我不禁想起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带有玄学色彩的电影《薇若妮卡的双重生命》(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片中波兰少女登台演唱时突发心脏病死去,而那个和她面貌毕肖、心脏也一般脆弱的法国姑娘在冥冥中似有所感,决定停止学声乐,仿佛因而避免了自己的夭折。伯杰称赞基氏为“电影小说家”;我思索他笔下的妮农拥有双重婚礼日期及年龄歧异这一点时,总会隐隐感到她好像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女子,代表两种命运。基氏电影另一个译名是《两生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或许可以说,伯杰用一枝悼念绽放并凋谢于过去的逝者,另一枝是未来之花,献给生者,可能预示着一颗希望的果实、一次命运的逆转:毕竟,美版中1996年结婚的妮农,比1994年结婚的她多了整整两年,而那两年极其关键(因为婚期将近时医生对吉诺说,可以指望妮农前面还会有“两年、三年、三年半的好时光”)。不同于英版文案,美版只字未提妮农“将死于艾滋病”,也许并非偶然。
恰也是1996年成了艾滋病治疗史上的转捩点:这一年,发明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美籍医生何大一当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该疗法的推广令艾滋病发病率在欧美很快降了下来,渐渐地,艾滋病感染在世界发达地区成了一种可控的慢性病。文学创作以想象力介入现实,科学进步也干预着小说的天地。伯杰肯定欣慰于人间悲剧的减少,但是他这本杰作并没有随着旧闻埋没,却因其超越性的文学品质而常读常新:每次重读,便是再次进入那个当下。
在一篇写于1991年向詹姆斯·乔伊斯致敬的散文里,伯杰这样写道:“今天,五十年后,我继续过着乔伊斯以巨大力量为我准备的生活,我成了一个作家。在我尚且懵懂无知的年纪,是他向我展示了文学敌对于一切等级体系,而去区分事实与想象、事件与情感、主角与叙述者,便是停留在旱地上,永不起航。”《到婚礼去》从创作到传播,从作者那一端到读者这一端,都有种种“事实与想象”始终在交织不已、难解难分。本来妮农是死是生,皆属小说,和我们有什么相干?然而她不是向壁虚造的人物,她代表着千千万万曾因艾滋病受苦的当代女子。我们觉得她近在眼前,才会念念不忘,而正是这种萦怀,方能使一部文学作品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