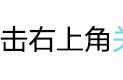上下铺的“同学”情谊
上课点名代答“到”,已成为而今许多大学同窗表达“相互关爱”的普遍方式。但对于恢复高考后最早的两批大学生:77、78级大学生来说,在经历了十年知识断层后,他们入学时,表达“同学友爱”的方式,可能是代表同学去申请更多的学习时间。
一位中国国家*早年在复旦念数学系时,他所在的班级同学白天上课,晚上去自习室和图书馆,回宿舍后还要挑灯夜读。由于寝室10点半熄灯,同学们都觉得太早,这位*当年就作为学生代表去和校长协商,最终将熄灯时间延迟半小时。
即使这样,熄灯后,室友们还是会打着手电筒在走廊里,一起背英文。30多年过去,这位*和他的同窗室友,都分别成为中国政界、商界、学界的知名人物,也因此被网友称为“复旦史上最牛班级”。
作家、哲学家周国平和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的同学故事,发生在更早时期的北大,他们是共同就读于哲学系的室友。郭世英床头的一本《牛虻》,开启了周国平的文学阅读之路。这类世界名著,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在当时,只是内部发行,并且只有具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到。
这些通过父亲郭沫若才拿到手的书,郭世英都很慷慨地与周国平分享。正是这些阅读,使周国平“对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有了零星模糊的了解”。回忆同学少年岁月,周国平这样说:“我从与郭世英的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
而在20世纪上半叶,更为紧迫有限的学习机会,给得以留洋的中国学生,赋予了更多“为国为民”的共同使命。徐志摩就为此与在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四位中国室友设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六时起床,七时朝会(激发耻心),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时间表上,还特意加上了一条“晚唱国歌”。
诗人徐志摩当时的室友之一,即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李济。
室友的救命之恩
默多克的夫人邓文迪,当年在留学困顿中,也是靠着大学室友的帮助,获得了在美国的第一份体面工作。当时,邓文迪在耶鲁求学,她刚与第一任丈夫离婚,生活拮据,只能靠在中餐馆打工赚生活费。她的室友陈永妍见状,将其介绍去了自己老公李宁的公司工作,负责推销运动服和健力宝饮料。
当年的胡适,则是由一位江西老表室友领着进了文学大门。这个室友叫钟文恢,因留着一撇小胡子而得外号“钟胡子”。1904年,在上海新式学校读书期间,胡适被室友“钟胡子”拉入“竞业学会”,并受邀为鼓吹“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和主张自治”的白话报纸《竞业旬报》写稿。他先后用几十个笔名在这份报纸上发表文章,从小说、传记、诗词曲、札记,到翻译、新闻、时事评论,什么都写,后来还成为《竞业旬报》的主编。
胡适后来在自述中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不但给了我一个发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机会,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杨振宁和邓稼先其实做了多年的“好室友”,从战时的西南联大,听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曲起,同为安徽老乡的两人便每日一起论辩量子物理学,后来又一起赴美留学。
毕业后,邓稼先回国造氢弹,杨振宁留在美国研究量子物理。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访问大陆,提出想见邓稼先。时值“文革”,邓稼先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在青海做“牛鬼蛇神”被群众批斗。后在*亲自过问下,邓稼先因此被“放”,回到北京与杨振宁叙旧。

帮追女孩,成人之美
一位国家*在北大念书时,则替当时的老同学、而今的著名法学家姜明安做过媒。据《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姜明安曾经想找一个法律系同级的知音,递了一个条子给人家,被人家退回来了。后来,姜明安又认识了同级中文系的一个女生,这次他不敢写条子了,就请同学帮他去“递个话儿”。这位*当时还是校学生会主席,同中文系接触较多。他“欣然受命”,并且很快传回了话:“姜明安的事让他自己来说。”
曾经的苏联“老大哥”戈尔巴乔夫也受过大学室友的“成人之美”。戈尔巴乔夫当年死追赖莎,常邀请“女神”来寝室做客,室友特意为戈尔巴乔夫量身定做了一个“日程表”贴在门上,每周某天固定一小时留给戈尔巴乔夫迎接女友。而在这一个小时时间内,其他室友都必须去别处“忙”。同时,为掩人耳目,日程表上,这一个小时的约会时间,被室友贴心地公示为“打扫卫生时间”。
和室友干过的“蠢事”
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里,柯景腾因为组织了一场格斗比赛,而失去了沈佳宜,这是导演九把刀大学时的亲身经历。“一个白痴学生,办了一场低能的自由格斗赛”,尽管九把刀这样形容自己*这件蠢事,尽管三个室友纷纷表示这个比赛根本不可能成功,但他们还是愿意一起干这件蠢事:“下场的只有八个人,其中,有四个人是我室友。”
胡适留学时与室友一度“玩牌丧志”的故事则更像一个黑色幽默。故事是胡适自己说的:《胡适留学日记》中有关“打牌”的记录累计36次,从1911年2月5日至胡适“誓言”戒牌的9月6日为止,他和室友平均每六天打牌一次。在最频繁的七、八、九月,平均不到3天就打牌一次,可谓“三天两头打一回”。
当然,室友的共同爱好,也会有风雅的。比如,少将毛新宇,当年就常与室友下围棋,彻夜聊明史。
死敌与“死党”
作为在北影读书时的上下铺同学,多年后,赵薇和何琳这对好友,毫不介怀地在电视里互爆当年“糗事”。赵薇说何琳曾坐塌她的床还坚持不认错,何琳则称:“赵薇同学的床下有无数双臭鞋,经常被我们批斗。”
股神巴菲特也有过被嘲笑的岁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时,他常与室友克莱德互相嘲笑。克莱德说巴菲特:“你的球鞋太烂了,你的T恤太土了,你的外裤太长了,你的内裤太臭了。”巴菲特马上回击:“你的内裤不臭,可是,你的考试成绩实在太臭了!”
如此“人身攻击”下,两人的友情维持了一生。这位后来成为巴菲特一生“好基友”的克莱德,其实是在大学第二年才“递补”成为了巴菲特的室友:巴菲特的前任室友非常用功,看到巴菲特日日在眼前闲逛,考试成绩却比他好,最后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干脆搬走了事。
只是,按照当今的标准看,他其实也是巴菲特的“好室友”:感谢这位看不惯巴菲特的聪明、愤而搬走的室友,当年对巴菲特的“不*之恩”。
文/秦 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