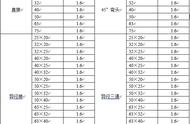原创作者:俺家官人
昨天偶然看到一篇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怎么坐火车的文章,一下子勾起了我关于铁路、关于站台、关于火车的许多有趣记忆。而在这些记忆里,给我感触最深的无疑是大一寒假时的归家之路——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自长途旅行。1995年那会儿,从湖南长沙到新疆库尔勒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先从长沙坐火车到西安,西安倒车到吐鲁番,再从吐鲁番倒车回库尔勒,通常用时4天3夜。为挨过这漫漫旅程,我在一只很袖珍的黑色手提软包里塞进了1瓶辣酱、5张饼子、10根火腿肠、1卷卫生纸,以及1部随身听、4盒磁带、32节5号电池。
国防科大的后勤部门保障有力,居然给订到了一张从广州到西安经停长沙的异常火爆的列车的硬座票。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忙昏了头的车站工作人员忘了及时检票放行,伤心欲绝的我眼睁睁看着这趟列车驶进又驶出,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不得已,两个半小时后我认命地挤上了路过的另一趟火车,坐票也变成了站票。整整18个小时,把人站成了一根不会打弯的棍子,并创造了憋尿时长的个人最好成绩。到西安后,进疆的火车还有9个小时才发车,因为担心买不到票,我根本不敢出站,靠着一根背风的柱子,把大檐帽的防风带拉下来勾住下巴,裹紧军大衣酣然入睡。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感到有人掀我帽子,睁眼一看是个扛着扫把的环卫大爷,“小伙子别睡了,别被人把帽子偷了。起来活动活动,一会儿冻感冒啦!”
托老爷子的福,火车进入甘肃金昌地界时我果然发起了高烧。“咦~~恁刚才净说胡话咧。”邻座是个50来岁热气腾腾的大妈,“俺会气功,给你发发功吧。”她不由分说按住我,边在我的太阳穴、眉弓和耳轮部位反复揉掐,边念念有词:“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走你!”一时天地大动,天雨众华,诸天神佛,咸共称赞。一息尚存的我最后终于爬上了从吐鲁番到库尔勒的火车。当天夜里2点来钟,一个拿着木棍的醉汉嗷嗷叫着追着个小伙子一路打,怪这个哈怂问候了他的妈妈,然后迅速被小伙子这一方的3个同伴缴了械,按在座椅下面好一顿踩。我正准备上去劝架的时候,他们已经和好了。对战双方一人一瓶啤酒开吹,大家都表示以后喝了酒要“把话好好说呢”。这帮人的隔壁坐着另外4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弹着吉他唱着歌,完全不为所动。这一路末了,深受触动的我总结了一首三句半:长沙车站嬲*,好心路人实可夸。喝酒打架管么子?傻瓜!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说:“世界旅行不像它看上去的那么美好,只是在你从所有炎热和狼狈中归来之后,你忘记了所受的折磨,回忆着看见过的不可思议的景色,它才是美好的。”如果把时光向前倒转66年回到1952年,我时年39岁的外公在这个时候也坐在一列自渝进疆的火车上,这趟旅程对他而言则是无比的艰辛苦涩。

外公是民国二年生人,也就是1913年,在当地称得上是名门望族。拜辛亥革命所赐,他在洋学堂念完了高中,考上黄埔军校后,因家庭反对没有投身行伍,后来当了县党部*兼县中学校长,并加入了国民党。一向热爱读书教书,县党部基本不去,工作从来都是虚应故事。解放后,在清剿反革命分子时受到牵连,被押送进疆劳动改造。“我是死中得活,如果继续留在重庆,运动一来必死无疑。”外公多次带着劫后余生的宽慰诉说这件事。他常常给我诵读《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重庆口音,字字泣血,昔人虽去,言犹在耳。外公拔腿就走,庆幸捡了条命,身后却留下了妻儿老小。彼时我的妈妈还不满2岁,再次见到自己的父亲已是16年后了。
闷罐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载着一车“地富反坏右”驶向未知的命运。回望来路,万丈深渊;眺望前程,愁云惨雾。何来送别酒?亲人亦须划清界线。未到阳关城,身边已无半个故人。车过乌鞘岭,这岭藏语意为和尚岭,海拔3500多米,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中部,是河西走廊的门户,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进疆的必经之地。乌鞘岭上有韩湘子庙,解放前香火甚旺,过往者皆驻足礼拜,或求一签,以保一路平安。外公当然不可能下车,他只能把脸紧紧贴在裂了缝的车厢壁上,睁大眼睛望进黑沉沉的原野,尖利的风刀刺得双眼泪水长流,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凝成了霜,那被无数双手摩挲过、被无数张脸贴靠过、被无数个额头虔诚地触碰过的板壁光滑而温润,竟有一丝柔软的触觉,给了离人短暂的慰藉。在那一刻,他向韩湘子诉说了什么、乞告了什么,都被时间永远镌刻在了乌鞘岭。倏忽过去了一个多甲子的时光,对这样的一段旅程,他可曾忘记过所受的折磨吗?
2017年立春刚过,元宵未至,因为身体病痛的原因,我年近七旬的父母终于无力继续在家照顾已和他们朝夕相处42年的外公了,选择了一家敬老院,扯心扯肝送他离家。走的那天,敬老院派了一台面包车来接。厚厚的积雪覆盖了路面,即便是富有冰雪道路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也开得战战兢兢。车子一寸一寸地破冰碾雪,外公一步一步地离开家园,前方是白茫茫一片清净世界。这样的一段旅程,最后留在他心里的又会是什么呢?13天以后,外公在午睡时平静地走了,无疾而终。
杰克·凯鲁亚克说:“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呢?怎么走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路上,除了行走在路上,等待我们此生的终点,我们别无选择。”
104岁的外公在日记本上也写着这样一句话——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