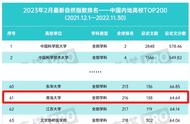第一章
三十七岁的我那时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十一月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扁平扁平的候机楼上的旗,以及BMW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幅的背景一般。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刚一着陆,禁烟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扬声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地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脑袋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不要紧?”
“不要紧的,谢谢。”我说。于是她莞尔一笑,转身走开。音乐变成比利·乔尔的曲子。我扬起脸,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飞机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快满二十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It’s all right now, thank you, I only felt lonely,you know.)”我微笑着说道。
“well,I feel same way, same thing,once in a while. I know what you mean.(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说罢,她摇了下头,起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动人的笑脸:“Ihope you’ll have a nice trip. Auf wiedersehen!(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再会!(Auf wiedersehen!)”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度春秋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冻僵的湛蓝的天穹。凝眸望去,长空寥廓,但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抚过草地,微微拂动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丛中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脚步,一边向我讲水井的故事。记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对那时的我来说,风景那玩艺儿似乎是无所谓的。坦率地说,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只是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都像回飞镖一样转回到自己手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极为纷纭复杂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微寒,山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得仿佛可以用手指描摹下来。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情形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一时间竟也无从想起。我所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当然,只要有时间,我总会忆起她的面容。那冷冰冰的小手,那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以及紧靠其底端的小小黑痣,那冬日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那总是定定地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那不时奇妙地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像在强风中的山冈上说话一样)——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她的面说突然而自然地浮现出来。最先现出的是她的侧脸。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随之,她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歪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
不过,让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如此浮现出来,总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需时间越来越长。这固然令人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起初五秒即可想起,渐次变成十秒、三十秒一分钟。它延长得那样迅速,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步步远离直子站立的位置,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站过的位置一样。而惟独那风景,惟独那片十月草地的风景,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拗地连连踢着我的脑袋,仿佛在说:喂,起来,我可还在这里哟!起来,起来想想,想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不过不痛,一点也不痛。一脚踢来,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就像其他一切归终尽皆消失一样。但奇怪的是,在这汉堡机场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它们比往常更持久地、更有力地往我头部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惟其如此,我才动笔写这些文字。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必须诉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她那时究竟说什么来着?
对了,她说的是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至于是否实有其井,我不得而知。或是只对她才存在的一个印象或一种符号也未可知——如同在那悒郁的日子里她头脑中编织的其他无数事物一样。可是自从直子跟我讲过那口井以后,只要看不到那口井,我就想不起那片草地的景致。虽然未曾实际目睹,但井的样子已作为无法从脑海中分离的一部分同那风景浑融一体了。我甚至可以详尽地描述那口井——它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地面豁然闪出的直径约一米的黑洞洞的井穴,给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又不见略微高出的石沿,只有那井张着嘴。石砌的井口,经过多年风吹雨淋,呈现出难以形容的浑浊的白色,而且裂缝纵横,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绿色的小蜥蜴“吱溜溜”钻进那石缝里。弯腰朝井内望去,却是一无所见。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井非常之深,深得不知有多深;里面充塞着浓密的黑,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了里边。
“那可确实——确确实实很深哟!”直子字斟句酌地说。她说话往往这样,慢条斯理地物色恰当的字眼。“确确实实很深,可就是没一个人晓得它的位置,虽说肯定在这一带无疑。”说着,她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口袋,觑了我一眼,妩媚地一笑,仿佛在说自己并非撒谎。
“那很容易出危险吧,”我说,“某处有一口深井,却又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是吧?一旦有人掉入,岂不没救了?"
“恐怕是没救了。嗖——砰!一切都完了!”“这种事实际上不会有吧?”
“还不止一次呢,三年两载就有一次。人突然失踪,怎么也找不见。于是这一带的人说:准保掉进野外的井里了。”
“死法怕有点不大好。”我说。
“当然算不得好死。”她用手拂去外套上沾的草穗,“要是直接摔折颈骨,当即死了倒也罢。可要是不巧只摔断腿脚没死成可怎么办呢?再大声呼喊也没人听见,更没人发现,周围到处都是爬来爬去的蜈蚣蜘蛛什么的。这么着,那里一堆一块全是死人的白骨,阴惨惨混漉漉的,上面还晃动着一个个小小的光环,好像冬天里的月亮。就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一分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想想都让人汗毛倒立,”我说,“总该找到围起来呀!"
“问题是谁也找不到井在哪里。所以,你可千万别偏离正道!”“不偏离的。”
直子从衣袋里抽出左手握住我的手。“不要紧的,你。对你我什么都不担心。即使深更半夜你在这一带兜圈子转不出来,也绝不可能掉到井里。而且只要紧贴着你,我也不会掉进去。”
“绝对?”“绝对!”“怎么知道?”
“知道,我就是知道。”直子仍然抓住我的手说。如此默默走了一会。“这方面,我的感觉灵验得很。也没什么道理,凭的全是感觉。比如说,现在我这么紧靠着你,就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再黑心肠的、再讨人厌的东西也无意把我拉去。”
“那还不容易,永远这样不就行了!”我说。“这话——可是心里的?”“当然是心里的。”
直子停住脚,我也停住。她双手搭在我肩上,目不转睛地迎面盯视我的眼睛。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便是那样一对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定定地注视着我。随后,她踮起脚尖,轻轻地把脸颊贴在我脸颊上。一瞬间,我觉得一股暖流穿过全身,心脏都好像停止了跳动。
“谢谢。”直子道。“没什么。”我说。
“你这样说,太叫我高兴了,真的。”她不无凄凉意味地微笑着说,“可是行不通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可以的事,那太残酷了。那是一-”说到这里,直子一下子合拢嘴唇,继续往前走着。我知道她头脑中思绪纷纭,理不清头绪,便也缄口不语,在她身边悄然移动脚步。
“那是——因为那是不对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良久,她才接着说道。
“怎么样的不对呢?”我轻声问。
“因为,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嗳,假定、假定我和你结了婚,你要去公司上班吧?那么在你上班的时间里,有谁能守护我呢?你出差的时候,有谁能守护我呢?难道我到死都寸步不离你不成?那样岂不是不对等了,对不?那也称不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吧?再说,你早早晚晚也要对我生厌的。你会想:这辈子到底是怎么了,只落得给这女人当护身符不成?我可不希望那样。那一来,我面临的难题不还是等于没解决么?”
“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我把手放在她背上,说道,“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另作商量不迟,商量往下怎么办到那时候,说不定你倒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毕竟不是眼盯着收去账簿过日子。如果你现在需要我,只管用我就是,是吧?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呢?好吗,双肩放松一些!正因为你肩膀绷得紧,才这样拘板地看待问题。只要放松下来,身体就会变得轻些。”
“你为什么说这些?”直子用异常干涩的声音说。听她这么说,我察觉自己大概说了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直子盯着脚前地面说,“肩膀放松,身体变轻,这我也知道。可是从你口里说出来,却半点用也没有啊!嗯,你说是不?要是我现在就把肩膀放松,会一下子土崩瓦解的。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往后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我就会分崩离析--被一片片吹散到什么地方去。这点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还能说什么照顾我?”
我默然无语。
“我心里要比你想的混乱得多。黑乎乎、冷冰冰、乱糟糟……嗯,当时你为什么和我睡?为什么不撇下我离开?”
我们在死一般寂静的松林中走着。路面散落的夏末死去的知了干壳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和直子就好像寻觅失物似的,眼睛看着地面在松林小路上缓缓移步。
“原谅我。”直子温柔地抓住我的胳臂,摇了几下头说,“不是我存心伤害你。我说的,你别往心里去。真的原谅我,我只是自己跟自己怄气。”
“或许我还没真正理解你。”我说,“我不是个头脑灵活的人,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但只要有时间,总会完全理解你的,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得彻底。”
我们止步站在那里,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我时而用鞋尖踢动知了残骸或松塔,时而抬头仰望松树间露出的天空。直子两手插在衣袋里,目光游移地沉思什么。
“嗳,渡边君,真喜欢我?"“那还用说。”我回答。
“那么,可依得我两件事?”“三件也依得。”
直子笑着摇头:“两件就可以,两件就足够了。第一件,希望你能
明白:对你这样前来看我,我非常感激,非常高兴,真是——雪中送炭,即使表面上看不出。”
“还会来的。”我说,“另一件呢?”
“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待过。可能一直记住?”
“永远。”我回答。
她就再没开口,开始在我前边走起来。树梢间泻下的秋日阳光,在她肩部一闪一闪地跳跃着。犬吠声再次传来,似乎比刚才离我们稍微近了些。直子爬上小土丘般隆起的地方,钻出松林,快步走下一道缓坡。我拉开两三步距离跟在后面。
“到这儿来,那边可能有井。”我冲着她后背招呼道。
直子停下,动情地一笑,轻轻抓住我的胳臂,两人肩并肩走那段剩下的路。
“真的永远都不会把我忘掉?”她耳语似的低声询问。“是永远不会忘。”我说,“对你我怎么能忘呢!"
尽管如此,记忆也还是一步步远离了。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了。在如此追踪记忆写这篇东西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的记忆都失去了。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安置所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化为一摊烂泥。
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命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时刻模糊下去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为了信守我对直子做出的诺言,舍此别无他路。
更早些时候,当我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就有过几次写一下直子的念头,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往下就会文思泉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就像一张十分详尽的地图,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派不上用场。但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蒂——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的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越是模糊,我才越能更深入地理解她。时至今日,我才恍然领悟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记她的原因。直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