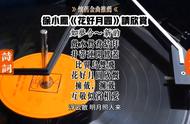再后来之后,我就留在了大陆,我没有跟着部队到台湾去。我想凭着我的劳动,就可以过一个平淡的生活,我的要求并不高,我们都很希望,只要平淡生活,就算是到农村去也好,只要团聚在一起,平平安安就行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到贵州去找工作。贵州没有找到工作,我们又回到南昌那儿开了个店,但是开店也不成功。于是我们又回到上海,因为我有一个舅舅,他在开大德医院,他是一个妇产科专家,他同时又办了一个出版社。
所以我在大德医院做会计,一百二十块钱一个月,我同时又在出版社做编辑,又拿一百二十块钱一个月,所以我一个月工资有二百四十块。从五一年到五五年,这份工资相当高了,那时候一个大学教授也不过是一百五十块钱,所以我那个时候很风光。
但是好景不长。我在家里是怎样生活的呢,很多人生活困难的时候,家庭里面要掌权什么的。我不要这个,我不管经济,钞票我不管的,我没有小金库,我的钱统统交给她,我不管,我的一些衣服,鞋子袜子缺什么,她就给我买什么,我不会买东西的。
我只喜欢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我喜欢什么?我喜欢写写画画玩玩,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配合得很好的,她也替我想,也照顾我,我要买什么,她都照顾我。
所以她到临终快要走的那个时候,她是2008年的时候病重,她没想到她自己,她晓得自己不行了,那是病已经很重的时候了,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昏迷的。有几分钟想起来清醒了,她就讲一句话,我死之后你怎么办?她想的还是我,牵挂的还是我。
有一次她住在医院里头,病很重,不知道半夜里面,什么时候醒来了一下,女儿在后面看着她,她睡醒了,就几分钟啊,跟女儿讲了一句,你要照顾好你爸爸啊,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又糊里糊涂睡下了。

所以她在临终最后走的时候,还是放不下的就是我,她是这样一个人。我也很感觉到庆幸,为什么呢?我是奉父母之命,但是如果是叫我茫茫人海之中去自由恋爱,去找一个跟她一式一样的一个人,恐怕也不见得能找得到。
这是我讲的最愉快的事情,或者说青年最愉快的事情,以后我们到上海找到工作之后,那个时候上海是非常之开放的,东西又便宜,一个大闸蟹五毛钱一个。五一年的时候,五毛钱一个大闸蟹,你们可能不相信,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问问你的爷爷奶奶就可能知道了。
五一年五二年的时候,这么大的螃蟹,五毛钱一个,对虾,天天有,新鲜得不得了。现在我去买的对虾都是灰的,又没一动一动的,头都掉下来了,不新鲜,摆了很久,而且价钱很贵,那个时候都是新鲜得不得了,油都是红的。
所以那时我们的生活很好,而且每个单位在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开舞会,大家一起跳舞,嘣嚓嚓,嘣嚓嚓,跳舞也不到舞场去。地板上撒点滑石粉,拿个留声机,大家都开始跳舞了,鼓励跳舞,大家有什么好衣裳就拿出来穿,每个礼拜都有,非常之热闹。
而且舞会是工会组织的,私人舞厅也开放,延安路开好多舞厅,你去买票好了。那一段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也是我印象中最美丽的一段时光。

最痛苦的一段时光,那就是,大家是知道的,这个是历史造成的原因。五八年我被送到安徽去劳动教养了,这是最痛苦的,因为一下子突然离调,不得了了,家里面这个生计啊,经济马上就困难了。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美棠她那个时候非常之艰巨,她是一个中法文优秀,有着传统文化美德的女性,我非常之敬佩她,承担这么一个责任。
当时有人劝她跟我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就是拜拜了。她不,她坚决不,她讲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她没有理由离开我。她不离开我,她就苦下去,她就做里弄工作,所谓里弄工作就是生产组,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什么她都做。
比如附近有一个旅社,她就去那里做勤杂工,她就倒痰盂,扫地,拖地板,她也干,甚至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台阶坏了,要修理这个台阶,要水泥工去背水泥,一袋水泥十五公斤,就是三十斤重,她也去做。
所以现在我经过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时候,我会停下来,我到那个台阶上,坐下来,摸一摸,在那里有她的劳动。我不知道哪一块水泥是她的,但是有她的一块,她付出了劳动,她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她过得很艰苦,她必须吃下这个苦,完成她这个做母亲的任务。
她把五个孩子都教育得很好。我在安徽那边,条件是比较困难的,那个时候买糖买饼,都是需要票的,大家都知道,要凭票。她把全家的票子,糖票,银票,一个月只有一次的,拿了集中起来,买了这么一包糖,大概一斤糖的样子。
然后她把五个孩子叫了过来,说,你爸爸现在在外面很辛苦,这个糖,你们现在,一个人尝一粒。孩子大的只有九岁,小的只有三岁,每个人尝一粒,其余剩下来的,寄给爸爸,好不好?五个孩子都都点头同意。
她虽是这么做,但是呢,钱还是不够用。她就变卖她的首饰,她有些首饰过去陪嫁,她就是卖卖卖,卖光了,她有五对手镯,都卖了,只剩了最后一只手镯,明天不得不去卖了。
这天晚上,她跟我的女儿,大概只有五岁吧,睡在一个床上,心里很难过。做母亲的,哪一个不想替女儿,留一点点东西作为陪嫁呢?但是想留始终又留不下。于是她把这个手镯女儿睡着了,给女儿戴在手上,让她戴了一晚上,再把它拿下来,总算给女儿戴过这个手镯了,了了母亲的一个心愿。

最后她留了一件羊皮袄,那是我母亲的遗物,羊皮袄啊,你们知道的,羊毛很好,很长,雪白雪白的,她说留着老了再穿,御寒。但是不行,到了六几年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插队落户,插队落户是要买热水瓶啊,铺盖啊,都要买东西,钱从哪里来啊?那只有拿这件羊皮袄子,拿羊皮袄子卖也没办法卖了,你到哪里去找买家啊。
要马上拿钱的话呢,要当。那个时候有很多当店,一当就可以了,她为了找一个比较好的价钱,从老北门一直跑到了老西门,跑了五六家七八家这样的当店,一家一家去问,找了出价最多的一家,六十块,当掉了。
拿了六十块钱,两个孩子插队落户到江西去啊,买被子热水瓶什么的,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家里当票这么一沓厚,从来没有赎的,哪里有钱去赎啊。后来我在那里之后呢,我们是互相通信的,那个时候也没什么手机的,哪有这么便当啊,互相写信。
在信里面,她讲的都是家庭琐事,什么柴米油盐啊,孩子们读书啊困难啊,这个那个的。我就谈我在安徽的一些生活情况,我们一直是心灵相通的,此时此刻,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会做些什么,她也知道此时此刻,我在做什么,我会做什么,我不会做什么。
真的,我现在理解到古人讲的话,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正有爱情的人,他理解对方,他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这个心自始至终是相通的。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等待,我想总归有解决问题,总归会有团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