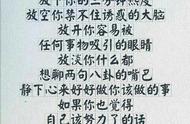今日小雪,父亲吃过早饭,坐在后院檐下,独自剥豆。刚从菜园扯回,经冬枯黄的豆杆在他手里上下左右地慢慢翻转,我能想像细心的他,在把豆荚全部剥过之后,还要逐个捏一遍,以防有遗漏。
种了一辈子的田地,对于土地里生长而出的东西,父亲是带有感情的。
冬日特有的阴天,雨似下过,新铺的柏油路面有寒凉的湿意。虽然节气为小雪,并没有下雪,“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的意境,只能想象了。
家里因疫情被封,第二天了,哪里都不能去,村与村、镇与镇,连高速出去的路口,也全被封了,日子一下子回到2020年武汉疫情初发的时候。
这样的情形,对父母的生活影响不大,他们一生的年月里,寻常走动的轨迹,不过是两个弟弟的家和菜园,最远不过骑上摩托车,去杨旦老家的菜园,或种油菜,或捡棉花。
杨旦从前是条街,至少民国时是,家里红漆酒柜上,摆着一件青花瓷罐,白底圆肚,瓷面光洁,是已过世二十多年的奶奶陪嫁之物,旧时风俗,嫁去夫家的第二天早晨,需向来客散发炒米糖等零食,是以有了这个糖罐。九十年代我出嫁回门的三朝,午饭后奶奶洗净了碗盏,便在那口能做十来个人饭菜的土灶锅里,炒了一锅上好黄豆,颗颗粒大溜圆,让我带走,我没问过,现在想来,都取与炒米糖相似的喻意吧。旧时日子,不以钱为中心,一切只以风物日露为主,人就如阳光下树上的叶、河边的水,日子自然流淌。此时想起昨晚看过的法国电影《我与塞尚》,生长于普罗旺斯埃克斯地区的塞尚和左拉,未入巴黎之前的美丽乡村时光,红土地上风吹过蓝天,我小时的记忆与他们何似。
民国世界山河浩荡,十五岁的奶奶于一个夜里,坐在花轿里,被人抬到了爷爷家,两家并不远,一个在河的上头,一个在河的下头,无意应了“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的浪漫。古时尚早婚,茜茜公主唯一的英俊儿子鲁道夫,奥匈帝国的唯一继承人,也是16岁时就被指婚,娶了与他并不相契的比利时公主斯蒂芬妮,我不知道古人的用意,大概是知生命的有限,趁着最好的年华赶紧把人生大事完结。当晚奶奶一双被缠过的天足,裹在不足三寸的红色绣花缎鞋里,从金枝玉叶的王家小姐,转瞬成为宋家七娘。旧时婚约,结婚前两人并不见面,直至结婚当夜。所嫁是鸡是狗,全凭命运,婚姻的事,是命运的事,放眼古今或中外,莫不如此。奇怪即便这样,那个时代,却很少听到离婚事件,一嫁一娶,都是一辈子。
那个夜晚或许有月光,也或许是秋夜如水,乡村习俗,秋后年前,婚嫁最多,十五岁的奶奶,二十五岁的爷爷,第一次见了面,因比奶奶大十岁,爷爷格外疼她,奶奶说爷爷一辈子没叫过她的名字,只一个字“伢“,那是家乡对小孩的爱称。
旧时出嫁的闺女,没有一个月,不准回娘家。骤然离开自己的家,去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境地,奶奶应该是哭过的。新婚过后的爷爷,曾体贴地护送奶奶到河外地,让她站在河边,和对岸的娘家人喊话,以解思家之苦。
爷爷弟兄七个,个个魁梧洒然。爷爷排行第七,所以上一辈人都称奶奶为“七娘“,从前的男女,身高180是普通水准,三队的李嬷,后院有棵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栀子花树,枝叶如伞盖,五六月的早晨,下了早读课,我常故意绕道去她家,一夜醒来,栀子花白露已开,香气十里,家里那时没有栀子花,艳羡得我一次次地在树下转悠,必须回家吃饭了,才不舍地带着满鼻子的香气走开。李嬷也长得身量高大,骨眉方长,盘髻的头发抹了松发油,常年溜光不乱, 用胡兰成形容张爱玲的四个字来形容她:“正大仙容”,再合适不过:。物质如此匮乏的年代,偏偏那时人的身高,却能普遍超过现代人,这是个谜。
从前的日色很慢,车、马、邮件都慢。
新婚不久,爷爷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后来,他千辛万苦地逃了回来,步行千万里,躲藏于泥泞之中,餐风露宿,只为回家,只为家里有他刚嫁来的妻,这样的场景,与《冷山》何似!当国民党的连长带人追到家里的时候,爷爷不由分说,拿起菜刀,斩断了大拇指,当即血流如注昏倒在灶门口,奶奶赶紧哭着拿灶灰给他包上。从此,他再也无法扣动枪了,连长这才放过了他。
爷爷以失去一只指头的代价,换来与奶奶余生岁月的相守。为谋生,爷爷做了对面杨墩地主家的帐房。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与饥荒抗争的年月,奶奶做月子时,那时刚吃大食堂,爷爷在饭桌上,碰到有粘米圆子,总会包几粒,人家问他,他说,”我家还有个做月子的“,圆子带回,送到奶奶手里的时候,还是热的。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宿命,所谓时代洪流。一九六0年的冬天,中国因过度浮夸而产生的恶果,最终落在了无辜的老百姓身上,爷爷被活活饿死。奶奶说爷爷走时是一个冬夜,冷得出奇,爷爷走后,奶奶哭得撕心裂肺,她用自己的身体的温度,抱着爷爷整整坐了一晚,即使他走了,她也想要他暖和一点。最后不得不转头含泪吩咐年幼的父亲,出门去喊其他伯父。从此七岁的父亲和不到三十岁的奶奶,还有两个姑姑,在这世上成了孤儿寡母,父亲也不得不从板桥私塾弃学,离开同龄同学,回家务农,用七岁未成人的肩膀,和奶奶一起,挑起养家的重担。
所以当今年暑假,七岁的侄儿站在堂前背唐诗,七十多岁的父亲心思恍惚,辛酸不已,当年他也是这么大,被迫把板凳拿回,离开了学堂……
杨旦旧时的街上,有位太公在那里开杂货铺,也是身长八尺,一生未娶,无孩子的他,很疼父亲,常常把小时的父亲架在他脖子上,哪里好玩哪里去,他那个铺子里的糖果子,是随便父亲吃的,吃不完便放在兜里带回家,这样的旧话,不知听过父亲叨过多少遍,我们也不点破,父亲虽然现在牙已全落,说时仍是怀念不已。
四反时,形势不好,全民不允许经商,这位太公被迫回到了老家山乡株林,离杨旦有几十里路,回去的他,在人家屋旁,起了个厦子,半间茅屋,起居停息全在里面,父亲曾去看过他一次,他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他一个人在上面什么时候过世,没人知道。年年清明,父亲都会坐车几十里,去陇他的坟,指给我们看:这是那个开铺的太公。
小时找东西,塞满布角顶针的抽屉里,偶尔会翻出一个白花花圆滚滚的大银元,拿在手里,厚实有份量,上面有袁世凯的大头像,奶奶说它叫“铜洋“,如果碰到匣子一样的火柴,奶奶便叫它”洋火“。
奶奶的娘家有位嫂子,听说做女儿时生得秀美无比,只是不知为何一嫁过来,便成了疯癫,听迷信的说法,是当晚花轿抬来的路上,路过河外地,风吹起了轿帘,因为太美,而被什么鬼怪迷住了,但她从不乱行事,除了自言自语,看不出于常人有什么两样。
从此小学到外婆家蹭饭的我,见一个身长高大的老太婆,常年坐在临河边的家门口,低矮的旧纺车里,一缕缕纺出白色的棉线,再用手搓捻成一根根细线,铺上蓝色棉布,绣出一朵朵白花,她绣的花,式样、大小、间距无不相等,然后就变成她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这小小的白花,从胸前到后背,从领口到下摆,无处不是,拿现在的话来说,纯属原创。
再也没有人,能创造出那样蓝底白花的衣服。对于其实早已与世隔绝的她来说,如何能做到此,完全又是个天方夜潭的谜。
“牛衣古柳卖黄瓜,村南村北响缫车“,我爱一切旧的东西,旧时场景。
她和她唯一的儿子,那个国字脸忠厚的舅公,我还记得小时到他家做客,不大的土砖屋两间,里间是疯舅太婆的卧室,外间泥土灶台,饭桌旁边一张竹床,铺上被褥,就是他睡觉的地方了。屋子不大,却无一陈设不简单干净,地也扫得干透清爽。他在灶间烧火,小小的锅台上冒出雾气,米粒开始炸锅时,饭便熟了,松黄的锅巴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虽是家常小菜,舅公却做得林净,招待人客,也能拿出几大碗。
舅公陪着老娘,一生未娶,娘俩静静地过完了这辈子。,送走了老娘,没过几年,他也走了,亲戚本家分他的东西,我家分到的是,他睡的竹床,那是七十年代的中国。
有时我分不清,梦境与现实,还会梦到去偷摘栀子花,而且还是在月光底下,没做过贼的人,总是在花快要到手时,被倏然惊醒。
土砖屋的隔壁,是郑嬷,提起这位奶奶,不能不说。
郑嬷嫁过来时,奶奶已在。奶奶说她第二天起来,“哪里来的这样一个好看的女人“,心悦诚服地赞叹,出自高傲的奶奶的口,可见当时她确实被惊艳到了。
等我记事,眼中的郑嬷已是一头白发,平整的脸上,无半点星斑,身高一米七八九吧,腰间经常系一条布褡裢,褡裢上有白色的银环。和肃穆的我们不同的是,她见人一口笑,说出的话很甜,用奶奶的话说:果泯人心。
和奶奶一样,郑嬷也是年青丧夫,老人们过早地抛下了这些女人而离开。而后其一子参军到南京军区,成为烈士家属,一子却无故遭害,媳妇出门干活时,家中大多只她一人,她有时思念不过,便坐在后门,痛哭一场,听到哭声,我便知道,她又在想她的儿子了。
老屋屋角有棵泡桐树,那时还只人高。她喜欢把洗过的洗碗布、洗脸巾,搭到树上去晒,如今,那棵树,已经窜到天中央了。
日露风雪,体现在一棵植物的身上时,是让它年年茁壮永无凋谢,体现在人的身上时,却是盛景一过便要枯萎,细想起来,却是没有答案。
郑嬷爱干净,天晴的日子,她必会拿着她的流粟扎成的扫帚,从屋里扫到屋外,别人扫地只扫屋里,一般不管门前的路,她不会,心情好的时候,门前的地,也是她的爱,地上的树叶和杂屑,在她的扫帚下,必会被清理得净净爽爽。
那时整个村里,和风荡漾,阳光温暖明亮,安静得仿佛几千年以来,都是此时的样子,这样的动作,这样的情景,安慰了她,扫完后,她扯下遮挡灰尘的蓝头巾,笑容灿烂,如同功成名就。
“身体的劳动会解除心灵的痛苦,这就是穷人幸福的原因“,尼采如是说,当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香奈儿,读到此处不禁念出声,卡柏便笑着调侃她也开始读尼采了。
回想我年少在家时,带着两个弟弟,七月流火的太阳底下、弓背于泥田与水里一整天,进行双抢插秧,间或裤子卷到膝盖的腿上,还有至今想来犹有心悸的蚂蝗叮咬,更别提傍晚如麻的蚊子嗡嗡地叫嚷在脸上眼前,那是一身的汗臭。就这样坚持下来,到三人一天内插完一亩五升田的秧,夕阳西下,歪歪倒倒赤脚走在回家的路,傍晚凉风如许,那时的心情,却是满满的成就感,犹如凯旋归来。
原来这就是幸福的原因。
当年失意的鲁道夫患病,靠打吗啡支撑多年,他问医生他还有多少日子,医生说:如果远离布拉格维也纳的宫廷,侍弄园艺,可能还有二十年;如果继续忧心于无法改变的变革,则…….,结果没过多久,年仅三十的他就选择了自*离世,他的过早离去,引发了后来的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统一欧洲的梦想,一百年后终于被他人实现,证明不是痴人说梦。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精彩,大人物有大人物的悲哀,民间向来不缺乏智慧的小人物,笑着过是伊的本事。
父亲说他活这么久,只佩服一个会过日子的女人。她是村里的袁嬷,袁兵哥的奶奶,父亲说她“无论么事出世,便会做么事来吃”,风过知声,雨过知绿,与田野里的植物最有灵犀的是她,最会尝鲜的是她,最会做吃的也是她,想必她的手下,出过多少时令美食:米欠圆子、荠菜饺子、荞麦面、小麦酱、水芹菜、蚕豆花、糍粑盖粑栗粑、粘米圆子糯米圆子、萝卜馇、菜馇,以我贫乏的想像,有限的经验,如何能数得过来?
那也是一个好女人吧,春天行于田野,年轻时走过的她会不会也是风景,四季流转,都活灵活现地被她看在眼里握在手里,这样的人,生命应该是不匮乏的。
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互连网,没有离家打工人,一代又一代。
记得家里的土砖屋,多少次煤油灯下,就着板凳,我在房里做作业,由于没有灯罩,火苗极易烫到头发,闻到焦味方才惊觉。奶奶已在靠墙的床边外侧睡下,却总是醒着等我,她的孙女做作业,她从来不催,节约惯了的她,这时却不怕耗煤油。未到五更,她就会叫醒我,起来刷牙洗脸,挑上一担靶子,舀杯米,拿罐咸菜去杨潭上学,有时她还会大声唠叨,怪母亲不早起,先做点东西,让我吃了再走。
出门时小燕已在等我,我们再去等战军、等新桃,月光汤汤,四围寂静,几个人边走边说,走到六围大桥,把龚大围走过,走到杨潭合作社,走过桔园,到了水库,也就到了洼地中的学校。教室的门并没开,来得太早,于是坐在月亮底下,至少等了一两个小时天才亮。
那是没有手表的时代,奶奶误以为天快亮了,太早喊醒了我。
我那没读过书的奶奶,是否要整晚数着时辰,听着鸡啼,才能充当她孙女的闹钟?
如果我善于渲泄,此时电脑前的我,深圳福田的我,其实很有必要就斯时斯景大发一番感叹,可惜多年单调的岁月已让我失语,想要精准地表达,得先用力摧毁厚厚的壳。
这是集体失语的时代,陈丹青说。
唯记忆留存。
我记得正午一大撮明亮的光,带着暖意,透过房顶的亮瓦照射进来,于是那间小小的土砖厢房里,便有了光,我站在房里,一动不动,眼见着无数浮尘的颗粒,就在那道光里上上下下地跳着舞,时间在我的仰视中,在浮尘的颗粒中,凝固与消逝。
如果能够,我宁愿回到那四间土砖屋里,冬暖夏凉,母亲、父亲、奶奶、弟弟和我,每天都在一起,没有生离,不知死别。
那时家家户户没有阁楼,只在房间靠近屋梁的地方,架几块木板,以放靶子棉花杆之类的柴禾,做饭时,用锄头勾下一捆,拿到灶下,再回来把地扫干净,记忆中最好烧的是麦草,一点就着,生长于五月的麦草,有大把的热烈。有次生病了,不善表达的父亲不知如何安慰我,便从那样的楼板上,翻出一个如石墨一样的东西,坐在床前拿给我看,父亲说这是一个玉砚,是爷爷磨墨写字时留下的,再后来,这个砚台,于哪一年的夏天,被走乡的小贩贱价收购,永远离开了我们,无从考证了。
眷恋从前朴素的日子。
端午那天,早饭刚过,你会听到明亮流利的二胡声,穿过后院和水井,穿过桔树枝枝叶叶,声声传来。二泉映月,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都是熟识的,那是对面发修爷的即兴演奏,平时他并不拉,过节才偶尔拉拉。年青时他参加了*时代的宣传队,没上过学的他,也没有基本功,若非聪明,否则如何能学会这最最复杂的二根弦的乐器。他的二胡声,就这样陪着全村人的颠前忙后,其时家家煎炸喧哗,炊烟亮蓝,斯时斯景,只觉人世的华丽与安定,仿佛人生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仿佛整个村子,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前几天听说他已走了,原本他应该,至少还能多活好几年。
稍稍出众的人,都会多一些孤独,琴音不再,渴求不再。
再也不会有人在端午的上午,在桔树和炊烟里,穿着白衬衣,坐在门前拉一上午的二胡,少了他的二胡的端午,少了很多的味道。
杨旦这条街,从康熙到民国,到细爹细嬷饭后所讲的“东洋鬼子被拉到河外地”,到父亲有时提起的“双沟”和“五七干校”,历史重叠交错于这一条随着两边店铺的荡然无存而消逝的街道,除了星星点点的零散记忆,像此时般的偶尔散落在深夜,以后,谁还会记得呢?
我们无法忘却现时萦绕心头的忧惧,这些文字断续记录的时候,很多大事在发生着。
平静的时候,追忆似水流年。
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当素朴的青菜上桌,坐在窗前,切断网络,静静吃一顿合口的饭,这便是存在,心满意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