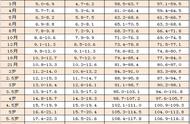3
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小乐写出了《雨夜曼彻斯特》。
这首歌来自于一个北京的雨夜,回忆起在英国曼彻斯特晚上真实发生的际遇,但其中“加入了一些渲染”。
歌词并不复杂,但暧昧湿润的编曲和古典气质仿佛是地下河流的交汇,规律的鼓点和动人的旋律瞬间征服观众。小乐把声线压得很扁平,听起来像是一支英国乐队,比如绿洲。
相似?抄袭?致敬?小乐没有避讳这些,“模仿学习是每一个人必经之路,我觉得因为人不可能生下来就会干所有的事情。”他觉得有这类疑问的观众“音乐听得太少了”,“当年oasis出道的时候,多少人都说他们模仿披头士,都是从那个时代长大,他怎么可能不受影响呢?音乐是有传承的,不可能说你生出来你就啪弹了一个完全不一样,吹呢?这么多年也没人编出来第八个音。”
“我更喜欢说是一种传承,模仿听起来不够高级。”他补充道。
“高级”,这个词对小乐应当很重要。他曾在其他采访里说过在英国孤独的日子,乐队不在身边,也没人说中文,盘尼西林也面临解散。
但现在他再回忆英国生活,用词非常正面,几乎全是快乐的,“非常自在,太享受了”。周末去看球赛,平时听听歌上上课看看书,最重要的是,平静得不像那个在school一言不合就动手上了热搜的小乐。
他对这件事有点伤心。他觉得自己内心一点也不崇洋媚外,他非常喜欢国内的山河大川和传统文化,但国内有些氛围让他很失落,人与人之间有太多情绪。“回国之前我特别peace,大家特别礼貌。”但是回来之后所有事情都不同了,他觉得自己每天都在生气。“天天有一肚子的气要生,会有一堆一堆的情绪跟疑惑。”
除了不会每天要生气,外面的世界也让他开眼界。“从音乐到审美到美术,你知道什么叫领先者,什么叫世界级,而不是停留在我们的互联网自娱自乐的环境里,世界的标准是什么标准,价值观和美学观会改变。”“行万里路”对他大脑皮层的刺激和以前他读了那么多书完全不同。
“巴西在物理距离上是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今年2月底,他带着乐队去了巴西演出,这个极端的距离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的愿望。“当你自己真的站在亚马逊河上,让你站在赤道上,你一看google map,你xx站在赤道上的时候,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不用再有任何东西告诉你,他们(队员)终于明白原来我在讲什么了。我老在强调世界和世界,就是他们终于明白我在说什么。”
小乐有点激动,用重复句式表达其他人终于明白后他总算松开的那口气。他觉得被乐队成员理解是很重要的事情,他不断去努力,希望他们能被他带入更好的审美中,因为,“审美的高级实在太太太重要了。”

“我从小就挺臭美的,参加节目所有衣服都是我自己配的,不是节目组设计师安排的。我觉得我是我们这节目里穿衣服最好看的。”在对音乐审美强调中,小乐突然插入衣服的话题,让人有点措手不及。还没想好怎么深入展开这个话题,小乐主动把选衣服跟摇滚乐挂了钩,“玩摇滚乐如果你连你自己的美学都控制不了,你是崩塌的。”并且这种崩塌是体系性的,“在我的认知里,音乐是一个特别强调审美的事儿,因为中国欠缺的就是审美,你不是技术上的能力,也不是说你们配合上不好,或者说才华不行,就是审美。”
但是多数在舞台上发光的乐队都没有去国外浸润过,这不能代表国外就能浇筑有关摇滚乐的才华。小乐的解释是天赋。“可能天赋很重要,其次就是生长环境和经历。但是好多东西,我觉得都是talent,有时候你无法解释的东西才能叫天赋。”
天赋说在成人世界里有时候并不是真心的称赞,这背后似乎意味着天赋不能支撑多久的前景。但小乐认定自己是天赋型音乐人,“因为我就是一个懒蛋。”他的乐队每周才排练一次,他很烦把所有细节都卡得那么死,“我喜欢的乐队都是没有那么重设计感的。所以我不喜欢电子乐跟现在特别新派的音乐,就是因为它每回那咬得那么死,看起来声光电特别震撼,但是我觉得特别无聊,我喜欢的是每场可能演的都不一样。”
每场都能不一样,表现全靠现场,演得不高兴了他会直接再见。“这才是摇滚乐的一部分。”
小乐希望能尽可能接近人心,人心就是想干嘛就干嘛。比如别人都费劲巴拉改编歌曲的时候,他就想抱个吉他怀念朴树,就唱哭了张亚东。
“这叫无招胜有招,我就一滴汗不出,我把那好东西就告诉你了。不想听你就出门右转。音乐是一个特别本质的东西,100年前或者80年前,三四十年代或者五十年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声光电的时候,大家乐队怎么演?不就是这样吗?”
他花了一大段口舌跟记者解释为什么他厌烦电子乐。从乐器是有灵性的讲起,“它是木头,是自然界的,木头变成了琴,多少年后纹路会出来,它会承载生命……”最终说到,“科技还是比艺术要晚好几百年。”

4
小乐让一切作品、语言、穿着都散发着他自己的美学体系,很难说这不是从小就开始逐步形成的性格要求。他很少提及出国前的年少光景,追问之后,他说嗨,也不是大事,就是以前不算是乖孩子。
1992年,张哲轩出生河北。十几岁的时候,总有无处发泄的精力和情绪,一开始他也用身体上的暴力释放情绪,直到后来接触了音乐,接触了摇滚,才平息了需要释放的精力。他认为摇滚和足球都有暴力倾向,解放了他要“破坏一切”的心绪,“就是一种不安分的因子,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喜欢看黑帮片。”他坚持认为,人要直面自己的人性弱点,“你不要避讳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因素,当然你要控制,不能把任何一个面发展到特别极端和犯罪的角度,但是摇滚乐跟足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出口,把你的天性释放出来,打碎好多东西。”
从这点来说,小乐认真表达了他对摇滚乐的感谢,“转移了好多精力,释放出来了。不管表达出来的是peace love还是violence。”
但是这种释放并没有伴随父母理解。尽管1990年代是国内摇滚的黄金时期,但对众多家长来说,玩乐队的不是好孩子像是某种共识,上一辈无法理解这种音乐形式和解放自己的人生态度。小乐也未能幸免。“严重的时候,跟我爸好几年没说话。”
但和解实际上也非常简单——出名了。父母的同事朋友听了他的歌,甚至有人成了盘尼西林歌迷,也知道他们拿了奖。他完全不责怪以结果为导向的和解,“他们这辈人某种意义上跟世界是脱轨的。”

在节目里,大张伟觉得没有听出盘尼西林新歌《群星闪耀时》里的黑暗,因而得到小乐的回呛。虽然不再是英文歌,但一样是用描述场景隐藏创作的真正意向。
孤独的世界他浪费所有的白天
诱人的黑暗比爱更难以拒绝
美丽调散每一个幻想的瞬间
闪耀的群星颠覆着黑夜
在小乐的作息中,夜晚比白天清醒的时间更多。下午两三点起床,吃饭听歌看书玩游戏,有想法了抱着吉他能一下子创作出整首,没有想法时也不强求,也不焦虑。
“我相信老天对我的眷顾,有一天没了,我就认命了,没了就没了,就别玩了,干点别的,我就可能去当足球教练。”
完全没有要一辈子死磕在音乐上。“为什么非要死磕,就我不明白,好多人说乐队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就没有呗,就解散呗,各奔东西呗。”
小乐认为自己身上从小就有完全不同的两面,“小时候也爱看书,但也容易冲动。”这种矛盾拧巴到了这个年纪,在身上依然很淋漓。
说自己不会在音乐上死磕,也不会让盘尼西林forever,但在英国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乐队的使命没有完成选择回来。爱谁谁愿意听他的歌,但被逼问急了,也会放松戒备,承认还是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影响更多人。
花了几分钟时间讲他的乐队观,“好多中国乐队老强调我们在一块几十年,但是我喜欢的乐队都解散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合久必分,大家在一块待时间长了肯定会烦,不想再跟你们玩了,特简单,解散各玩各的。”
有些国内乐队要一直在一起,和多年未解决的版权问题息息相关。“大家要靠演出挣钱,解散了之后没法靠版税拿到收益,但在英国(乐队)解散后每年有丰厚的版税收益,可以让我每年都是百万富翁。”除了这个有可能的无奈理由,非要绑在一起很多年,他语气强烈得不喜欢这个行为,因为“这是一个绝对不国际化的想法”。只有不被束缚,有新鲜感才有音乐,才能打动人,“音乐是自由的,这不是一个足球队。”
但是在舞台上讲到认识十年的吉他手刘家可能会离开盘尼西林,小乐声音哽咽,戴着的墨镜挡住后面的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