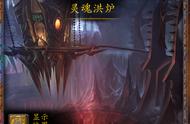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天,消息是晚间公布的。很多地方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而在它的出厂地——位于青海省一片辽阔草原上的第二机械工业部“221基地”,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原子弹产自身边。
根据不同人的回忆,这里也有过庆祝活动,但与外地一样,都是为那离自己很远的、沙漠深处升腾的蘑菇云。有人这样问同事:“我们国家还能制造这么厉害的武器?在哪儿生产的啊?”
221基地的装配钳工黄克骥属于少数知情者。他参加了核试验,原子弹由他和同事手工组装。当他们从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返回,很多人都不知情,包括他妻子在内。

221基地的一处车站。当初,第一颗原子弹从这里出发,运往核试验基地。张国/摄
“那时候保密。”年近九旬的黄克骥这样解释60年前的事情。

黄克骥老人接受采访时,爱人一直坐在客厅里旁听。郑萍萍/摄
直到原子弹爆炸后第二年,221基地的技术员刘智财去另一个工厂接收一款产品,还有人向他打听:“咱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是不是从苏联买的?”
刘智财不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他所在的车间就负责核材料加工,但由于隔离式的保密措施,他对别的工序并不了解,也从未见过原子弹,“我们只知道自己所*这一段、这一件”。
有过多支部队驻扎于此,包括附近山上的空军高射炮兵和探照灯兵。但许多士兵,直到服役期满都不知道,他们昼夜守卫的221基地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1958年开建,存续了36年多。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都诞生于此。
另一位技术员刘书鹤是1964年来到基地的大批毕业生之一。他这年9月拿着报到证到青海时,距离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只有一个月,他对此一无所知,连目的地在什么方位都不知道。
在省会西宁的报到点,他接受的入职第一课是保密教育,那节课的高潮环节是会场内800多人举起手臂,宣读保密誓词。他们的工作证盖着“国营综合机械厂”的钢印,这是个掩护名称,每个人在任何信件、任何场合,都不允许透露基地性质、规模、地理位置等信息。
来到221基地后,刘书鹤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同班同学朱鸿森失去了联系。
50年后,在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的一次活动上,退休的刘书鹤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新疆马兰基地原司令员马国惠询问,意外地找到了朱鸿森的电话。
这时他才知道:那些年,他们一个在221基地,一个在马兰。在像他这样的人手里,中国的核武器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然后送到他的同学那边去试验。他们互相去对方的基地出过差,但从未相遇。他在马兰打听过同学的下落,但由于保密限制,没有任何结果。
两个人,被同一个秘密隔开了半个世纪,刘书鹤说,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身处两地,却一直置身于中国西北的“同一战壕”中。
中国人的腰杆儿
2024年夏天,83岁的刘书鹤回了一次221基地。这是他离开后首次回来。30多年前,221基地撤销,人员分散安置,有一批人包括他在内,迁到河北廊坊,创建了另一个工厂。
他告诉记者,他本来没有回去的计划。他年轻时在基地受过腿伤,行动不便,但又抑制不住想念。解决之道是儿子推着轮椅,陪他“回家”。
很多老人都有这种矛盾的心情,他们担心自己的身体,又担心回去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回到这片叫金银滩的草原上。
他们怀念这里连绵起伏的山峦、山巅终年不化的白雪,以及丝带一样蜿蜒伸展的河流。
记忆并非全然美好。当地平均海拔约3200米,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二。初到者需要克服高原反应。
另一些记忆与寒冷有关:这里年均气温是零下0.4摄氏度,曾令他们苦不堪言。
84岁的退休工人蒋宗泰对此心有余悸。他说,那时他们冷天里吃馒头,前两口还热,咬到第三口,就能吃到冰了。

84岁的221基地亲历者蒋宗泰讲述“蘑菇云”背后的故事。胡春艳/摄
1958年,中国政府在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这片水草丰美的草原上划出1167平方公里的禁区,建设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实际建成区是573平方公里。
这片群山环抱的草原被选中为国家的核基地。为国家让路,1279户、6700余名牧民赶着大约15万头牲畜,仅用了10天,就迁到了外地。带头拆除帐篷的,是时任海北藏族自治州州长夏茸尕布的母亲和姐姐。
当时,原子弹问题不但是中国面临的科技领域最大“卡脖子”问题,并且直接影响国家的安危。
就在221基地建设过程中,在第一颗原子弹送去试验之前,一些技术人员一度转移到周边其他县城,因为有消息说,这个新生的基地可能会遭遇国外打击。
蒋宗泰记得,那次技术人员临时撤离后,他们留下“看家”。
中国抽调人力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该所的221基地建设也因此展开。
在北京,第九研究所盖起了一个样品库,以供存放苏联的原子弹样品。
但样品并没有等来——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1959年6月,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这就逼着我们自己干”,回顾这一经历时,“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说。
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63年7月,美国、苏联与英国签订了一份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但不禁止地下核试验。
据朱光亚回忆,美国代表当时称,之所以达成协议,是因为“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1963年,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有了突破性进展。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到221基地检查工作,当时,他们确定了“596”这个数字——把1959年6月这个特殊时刻,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黄克骥说,原子弹一直被视为“争气弹”。“大伙儿都憋着一股劲儿。早日试验成功,中国人腰杆儿就挺起来了。”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沙漠上空,“596”带来的那朵蘑菇云,标志着一面盾牌的升起。
中国政府关于第一次核试验的声明里提到了几个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威胁”。
这份文稿说,“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
紧迫感
晚年的黄克骥,家里挂着一幅字“汗浇血铸”,那是对他亲历的核弹研制过程的概括。
他的从业生涯里有过一次汗流浃背的半小时。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次发射导弹核武器,那是首次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
一个工人往核弹头试插雷管的时候,有一根雷管拔不出来。气氛立即凝重起来。领导说让黄克骥这位钳工去试试看。
“我脑瓜一片空白。”他对记者回忆。
尽管表示自己也“没干过”,他依然硬着头皮上去,操作了半个多小时,把雷管拔了出来。这时已大汗淋漓,内衣湿透。
那是中国的第四次核试验。他参与组装的那枚核弹头飞到894公里外爆炸,宣示中国拥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高塔上爆炸的,无法用于实战,因此,中国曾被认为“有弹无枪”。
刘书鹤也有过那种时间变得格外漫长的经历。一次武器退役试验,炸药变形后拆不下来,只能用锯去切割。两名工人操作,有人负责计数,提醒他们一分钟锯多少下。安全员在一旁浇水以防爆炸。每个人的心都揪着。工人的身上落满了炸药粉。
为这120分钟,刘书鹤给工人事先准备了两套换洗衣物。
60年后,弓着身子为国家“挺起腰杆儿”而流血流汗的那一代人已渐次老去,有的离开了人世。
221基地撤销时,这些人离开金银滩草原后的主要聚居点之一,是位于西宁市的“二二一小区”。为他们服务的中国核工业集团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西宁管理处管理科科长于大华熟练地对记者说,他们的服务对象是154人,年龄最大的97岁,最小的68岁,平均82岁。
她记得很清楚,2014年1月1日,这个数字是341人。
第一颗原子弹诞生前,于大华的父亲就在221基地工作。如今,她为父辈服务。
这位“核二代”说,父辈们的集体愿望,就是把“221”的故事讲下去,让更多人知道“两弹一星”精神。
2024年,一些老人跟刘书鹤一样,赶回221基地参加纪念原子弹爆炸60周年的活动。